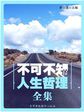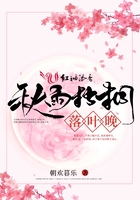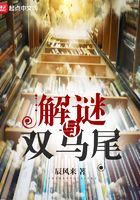那些往事的甜草芽,伏在记忆的斜坡上。
无论什么时候,你走过来,都是一副不用翻卷的画……
老油坊,就像一位看惯秋月春风的老人,端坐于西街,静观风云,不争不弃。老街的风致遗韵也在这一份坦然惬意中,无声地传承。
漫步老街,逝去已久的响声散落一地。那童稚目光里曾看到的一切,在岁月里一点点切割,砖瓦般垒砌起深刻的记忆。踏着凸起的鹅卵石,一块一块数着走过的童年,已经走得很深很远,那低低节奏分明的号子,犹在耳边轻轻拂过的轻风里悬挂。穿街而过,是上学的路,也是回家的路。暮霭晨光,慢慢过滤着一段段日子,骨子里飘出的醇香浓缩着时光的距离。打开一扇窗户,就打开了一扇通向昨日的门扉,我似乎看见西街幽深的巷子里有着历史的模样,那清亮透明的芝麻油,乌黑醇厚的菜籽油,一桶一桶,一缸一缸,如橙黄的玛瑙,如流光的乌金,滋润着老镇,滋养着居民平平凡凡的日子。
在那个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年代,人们饥饿的嗅觉对一种气味最为敏感——香!小家小户厨房里那点微不足道的香气,不足以在记忆深处打下深刻的烙印,只有一股香味儿,让老街居民终身难忘。这股香气自西街老油坊上空飘起,弥漫在叶集狭长窄旧的街巷深处,穿越几十年岁月,至今还依稀附着在我们的鼻孔里,潜藏在老街四邻的心坎里,伴着岁月起起伏伏。
传统,是不张口说话却最让人难忘的东西;传统,也是最不新潮时尚却最让人迷恋的东西。城区的繁华毫不犹豫地向东移去,几条老街的繁荣已经成为久远的过去,食品站消失了,糖果厂消失了,老茶馆消失了,豆汁厂消失了,九货联营消失了,但如果你怀旧的脚步向西街走去,走过张大妈家灰青的烟囱,走过李大爷家爬满野藤的瓦楞,走过算命老王的幌子,你会发现:它,还在老地方!也许它是你日日走过,却不经心不留意、只在炒香开榨的日子里才深吸鼻翼,赞不绝口的地方;也许它是你曾经迷恋,曾经热烈向往,曾经久久不肯离去的地方,因为那里真的好香!在我流连于此的童年时光,老油坊已经很老,但古旧的器具掩不住飘溢的香醇,在炒籽开榨的日子,一条街的嗅觉都鼓胀起干瘪的细胞,一条街的鼻子都疯狂地走神,因为那动人的气息是人们感官最愿意亲近的味道。
老油坊已经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岁月。50年,也许你的容颜已经老去,也许你爱的人早已远走,也许你的街坊四邻已经残缺不全;五十年,也许你的人生已经有了太多太多的改变。但,如果你走上熟悉的街道,蓦然发现已经遗忘了很久的老厂子、老房子还在,你的心或许会深情地动一下,搅起很多沉淀的过往,泛起很多旧时的记忆。脚下的鹅卵石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水泥路面,低矮的屋檐也有一些变成了楼房,但你仔细辨认还能找到曾经的影子,就像儿时的小伙伴,已久不见面,但逝去再长的岁月都能从斑驳的脸上找到熟悉的眉眼。你看,老门脸还在,陈旧的木板门还在,一排排高大的油桶一如从前。油坊,似乎把街道凝固在过去,把时间定格在过往。
那时,也许八九岁吧,家住在南街,那天和名字叫老定的邻家哥哥一道去西街玩。过了十字街往西一转,小桥头上就嗅到扑鼻而来的香。循着香味往前走,自然走到了油坊门口。醉人的气息诱惑着我们欲进还休的脚步。老定忽然记起他二伯在油坊干过活,我俩以找二伯为名溜进了后街的作坊。那房子好大呀!太阳从高高窗格子里照进来,穿过絮状的灰尘,照在灰白的墙上,照在几口大锅上。那锅真海,恐怕能够睡进去几个孩子。锅里正炒着油菜籽,几个人挥动着粗壮的胳膊翻炒,铁锹大小的铲子翻起的瞬间,可以看到籽粒在锅底跳舞,饱满的香味令人垂涎欲滴。我们流连在那里,久久舍不得离去。
开始榨油了,榨油房大梁垂下一根极长极粗的麻绳,尽头系着一根乌黑锃亮的长木锤,比和尚敲钟的大木鱼还粗还长,木锤正对着榨槽,几个粗胳膊粗腿的汉子,朝着榨槽荡起大锤,榨锤与吊绳磨擦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他们哼着整齐的号子,声音不高却节奏分明:“嗨哟荷呀!撞起来呀!榨出水呀!流出油呀!流满缸呀!装回家呀!烙油馍呀!好日子呀!过不完呀……”一下一下地撞,黄橙橙的油就慢慢溢出,汩汩流到下面的油缸里。好多西街的景物已经记不清了,但是那绳,那锤,那凌空飞起的情景,那节奏有力的号子在记忆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迹。
喷香的诱惑让我们渐渐成了这里的小老鼠,瘦小的身体趁工人们不备,溜进溜出,时或偷出小块小块的渣饼来。在那个缺乏零食的时代,香香的渣饼可算是难得的美味了:虽然硬硬的,干干的,口感算不得十分好,但啃一口在嘴里慢慢咀嚼回味,能品出幽幽的余香,有时分一点给同学尝尝,大家都很开心。过后嘴里悠长的回味,口齿间的余韵,就像阴天空气中袅袅的雾,长时间不会散去。
西街油坊生产的菜油芝麻油,香味浓郁,质优价廉,是远近闻名的好油。城乡居民,远远近近,拎着瓶的,拎着壶的,步行的,骑车的,都愿意来这里打油。人们不爱超市里那些花花绿绿、包装精美的货色,只相信这里的油最香最醇最实惠,吃着最放心,价格最公道。
“打油!”
“菜油还是麻油?”
“菜油!”
“打多少?”
“一斤。”
“好嘞!”
长长的油提溜伸进深深的油桶,稳稳提起来,顺着漏斗倒进油瓶,一瓶两提溜,不多不少整一斤!盖盖儿,收钱,转身走人。附近的居民,路近人熟,炒菜炒着炒着一看没油了,打发孩子去油坊打油,不用给钱,不用打条,不用记账,也无需打招呼,等哪天大人得闲了,欠了几次的帐一并结清,皆无口角,绝无纠纷。百姓的淳朴,经商的厚道,叶集古老的民风在深深的街巷间代代相传。
我想到了老陈(大家都这么叫他),从西街油坊建成开始到现在,他一直在油坊工作,今年已经70来岁,每天坐在店面里,细瘦的身姿就像铁杆细丝的油提溜,一直没有什么改变。我和他的儿媳相熟,于是有了探访他的机会。
为什么一个街道企业,能从计划经济年代一直坚守到现在?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今,几十年时代风云,几十年沧桑巨变,世界早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到市场主流理念的转型;从社会发展变革的大环境,到人民生活状况前所未有的改变;从人们思想的旮旮旯旯,到现实社会的角角落落。21世纪的今天,哪儿也摸不着六七十年代市场的皮毛了,但是一个小小的油坊处变不惊地走过了巨大的裂变,并且一直在走,一定有它雄壮的理由。
没想到老陈竟非常淡定,语气极其轻描淡写:“哪里有什么制胜之道?就是忠厚待人,本分经营,坚守传统,恪守质量。”简简单单,朴朴实实,细细揣摩却句句在理,句句切中要害。
经商之道,一在做人,二在为商。忠诚待人,诚信待客,决不以任何理由降低质量,决不克斤扣两,保证货真价实,这是民营企业长久存活的根本。
事实上,小油坊不可能不受社会大环境的冲击,生意不够景气是回避不掉的现实。现在,职工们收入不高,只能维持简单的生计,年轻人不愿干了,主动离开的也不少。像榨油中最核心的工艺“猴子爬山”,老油工干不动,需要培养年轻人,但活很累又不挣钱,后备乏人。老陈谈到油坊前景的时候,担忧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可喜的是目前他的儿子已经成为榨油技术的熟练工,如果叶集以及周边地区的油菜种植面积能够扩大,如果菜籽收购的质和量能够保证,他对油坊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
从油坊向西再往深处走100米,临街的几间房子就是陈老板的家。他的住房是叶集老街老房的标本,低矮的檐似乎伸手就可以摸到,让人顿生身体增高之感。门前窄窄的街道,曾经热闹而忙碌,在叶集只有南、北、西这三条街的时代,这里过年过节有秧歌队打着腰鼓,琅琅歌唱,热热闹闹;也有每年正月十五,孩子们拖着自家制作的兔子灯,满街游走;还有刻字的、画像的、炸爆米花的来来去去;还有补锅的、收牙膏皮的满街吆喝。现在,老街平静了、冷清了,似乎远离了喧嚣,淡出了尘世。
但西街老油坊还在,它依然精神,依然飘香,依然活在城乡居民的生活中,依然在叶集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老油坊,就像一位看惯秋月春风的老人,端坐于西街,静观风云,不争不弃,一切顺其自然,老街的风致遗韵就在这一份坦然惬意中,无声地传承。
容易成功和难于成功同样能刺激人的愿望。
——巴尔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