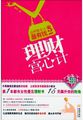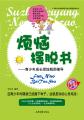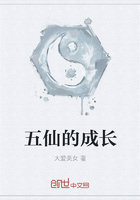童年的歌谣,你是,绽放在记忆里的璀璨;
童年的歌谣,你是,定格在瞬间的永远。
童年的歌谣是盛开在睡梦里的温暖,童年的歌谣是绽放在记忆里的璀璨,童年的歌谣是行走在岁月里的缠绵,童年的歌谣是定格在一瞬间的永远。
一个人从幼年到少年,或许总有那么几首童谣曾经伴随过你。当曾经读过的故事尘埃落满,当曾经看过的画面残缺不全,当曾经仰望的身影不再康健,但童年的歌谣,总会让我们在每天奔波忙碌的间隙,意犹未尽地想起。
我的童年是在七十年代那个物质生活极为困乏的时代,吃的零食是一分钱买十个的面糖豆,二分钱一个的麻花子,五分钱一杯的小毛栗,偶尔得到一块硬糖,也如获至宝,会含在嘴里甜半天;穿的是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旧鞋子,偶尔做一件新衣,买一双新鞋,大人也是舍不得给穿的,必定压在箱底等过年穿。现在的孩子,衣服是穿不尽的姹紫嫣红,零食是吃不完的林林总总,但据调查,当代的孩子们的快乐感觉,却没有同步提升,他们感觉更多的是约束和压力。我们的童年贫穷却快乐着,在回忆里有永远品尝不完的幸福,甚至还带着一些浪漫。就如童年的歌谣,平时根本没有闲暇去回忆,但偶尔静静地想起,便能勾起无数的回忆,以至于连自己都感觉有些诧异,虽然我们已经过了相信童话的年龄,虽然我们已经没有了做梦的心情,虽然我们的笑容已经不再单纯,但那些埋藏在记忆里的童年歌谣,却像种子一样深深地扎根,一旦提起还能够朗朗上口。
在夏季的夜晚,院子当中放一张竹床,一群小伙伴挤坐在上面听大人讲故事。头上是星光亮亮闪闪,月儿圆圆弯弯,一天又一天,当把万般变化的孙悟空,耍大刀的关云长,放牛的王二小等等故事听完,经常会把那些烂熟于心的歌谣,兴致勃勃地念唱一遍又一遍。
小板凳,摞摞,上面坐个大哥,大哥出去买卖,上面坐个奶奶,奶奶起来烧香,上面坐个姑娘,姑娘起来梳头,上面坐个马猴,马猴出来蹦蹦,上面坐个臭虫,臭虫出来爬爬,上面坐个娃娃,娃娃要吃面疙瘩,张着大嘴喊妈妈,妈妈过来,啪啦啪啦两耳刮。
几个小伙伴说到这里,就你指着我,我指着你:“你是那个娃娃!”“你是,你是!”“你是那个臭虫!”“你是马猴!”“是你,你是!”……指指点点,推推攘攘,争论不休,满院子的嘻嘻哈哈。
也许在大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在懵懂无知而又天真烂漫的孩子看来,却是乐趣无穷。为谁是臭虫,谁是马猴,谁是那个张着大嘴、流着鼻涕、要吃面疙瘩的娃娃而争得面红耳赤,吵闹成一团,并且乐此不疲。
有时候,在院子里玩,一会跳绳、一会抓子、一会踢毽子,那时候玩的花样很多,在地上画格子跳石,用烟盒子叠老包,男孩子滚铁环、打得锣(陀螺),女孩子跳橡皮筋,大家一起抓老羊、丢沙包、捉特务,玩累了就坐在廊檐台子上歇着,看见篱笆墙边的丛丛月季,密密麻麻的叶子,密密麻麻的花,几个小姑娘自然而然地念起了这样的儿歌:
刺麻台,叶子多,人家夸俺姊妹多,俺姊妹,也不多,两个推磨两个箩,两个厨房做馍馍,两个房里裹小脚,两个上山砍柴火,看见一只小花鸡,大姐逮,二姐杀,三姐烧水,四姐掀(褪毛),五姐剁,六姐煎,七姐开柜拿油盐,八姐盛,九姐端,端到十姐脸面前,十姐十姐你尝尝:家鸡没得野鸡鲜。
那时候不懂得什么是歌、什么是谣,只觉得念起来很好玩,兴致盎然,趣味无穷;那时候更不需要什么舞台,不需要谁来排练,大家自然而然,心有灵犀,出口成诵,你一句我一句,整齐流畅:“大姐逮,二姐杀……”,歌谣像流水一样从一个人口中流到另一个人口中,非常熟练,无需思考,张口就来,绝无迟疑。这些歌谣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念,也不知道是谁教会了谁,总之,小伙伴们在一起说着唱着,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
在夕阳西下的黄昏,一群小孩聚在一处,在街道边疯得忘记了回家,忘记了吃饭,直到暮色四合,直到家长们拖着长长得声音呼喊,才一个个带着那张又是灰又是汗的花脸,依依不舍地离开。
大月亮,小月亮,开开后门洗衣裳。
金盆洗,银盆浆,打扮哥哥上学堂。
学堂路,盖瓦屋,瓦屋高头一只鹅,扑棱膀子过江河。江河那边人又多,穿着花鞋来对歌。对歌还要对歌人,梳头还要红头绳,搽粉需要明镜子,坐官需要秀才人。
这首歌谣叙述的内容大概是父母把家里的男孩子穿得干净整洁,打发他去求学。然而上学的路上有热闹的对歌,那喜庆欢乐的场面对男儿是一种深深的吸引,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也想去看热闹。然后父母就教育自己的儿郎说:“想对歌那是要有条件的呀,你看人家多有钱呀,楼房瓦屋的。等你读好了书,学好了本事,做了秀才当了官,才能够给女孩子买明镜子,买红头绳,才可以和女孩子对歌呀!”这也许是那个时代最最朴素的教育经。当然,我们唱着这个儿歌的时候完全不懂得这些意思,也丝毫没必要去追求理解,也从来没有人要给我们解释。我们只是把它当歌唱、当经念而已。你唱我学,我唱他学,口口相传,像风吹麦苗一样,一波一波传过去,才不去理会它是什么意思呢!玩耍时自发的齐整的念白,是游戏,是娱乐,更是无限的欢乐。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从没有感觉到生活的穷和苦,留存在记忆中的只有快乐,快乐,再快乐,残缺的衣和食都淹没在一片快乐的海洋里。那快乐里是完整纯净的童心,是没有极限的幸福感觉。
《说反话》是童年时候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歌谣,一百遍地念起,会一百遍地笑弯了腰,笑疼了肚子,笑僵了腮帮子。
打开天,望望门,满天月亮一颗星。
我在屋里头梳手,听到外面人咬狗。
拿起狗头砸石头,石头一下咬了手。
幼小的心灵想象着怎么把天打开,去看那门。天上自然没有门,更没有满天的月亮。但多么希望真的看见“满天月亮一颗星”的奇观啊,那句子里有童年浪漫的遐想和幻觉。直到现在,有时我仍然会有观赏满天月亮的美丽幻想,希望哪怕是在梦中看见那种情景也好。那时候念到“听到外面人咬狗,拿起狗头砸砖头,砖头一下咬了手”的时候,语气和语调就更是张扬到摇头摆尾,东倒西歪的地步。
歌谣是童年的诗,童年的趣,童年的梦。我们在蹦蹦跳跳,唱唱叫叫,玩玩笑笑,快快乐乐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平常而又难忘的日子,这些难忘的日子串起了我们纯真而又幸福的烂漫岁月。
现在,那些儿时的伙伴早已分散,很少谋面,有的甚至了无消息,但每当想起这些童年歌谣,那些美好的往事就扑面而来,那一张张纯净的脸,那一串串童稚的声音,一个个欢蹦乱跳的身影,都生动鲜活地立起了清晰的形象,仿佛就在眼前。他们的身影伴着歌谣走来,童年如水般无邪的心境也会随着回忆走来。这里面有深刻的情感记忆,每当想起它,所有的烦恼压力全都烟消云散,心境会如山涧细流般清明澄澈。拥有一颗这样澄澈透明的心是多么令人欣慰啊!
也许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做梦的心情,也许我们的笑容已经不再单纯,也许我们的声音已经不再稚嫩,可是在我们奔波忙碌的间隙,仍然会想起这些歌谣,这是岁月弥留的味道。它会永远珍藏在我们心中,是生命过程中无形的宝藏。
让那些童年绽放的画面,一直开在我们的睡梦中;让那些无邪的童声,一直响在我们的笑声里;让那些无尽的幸福快乐,永远陪伴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
扯攮攮,拜小姐,小姐穿个破油鞋,油鞋破,两半个。大半个,换馍吃;小半个,打酒喝。馍呢,猫吃了;猫呢?上树了;树呢?水淹了;水呢?龙喝了;龙呢?上天了;天呢?那呗?(指天动作)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老鼠老鼠你别急,抱个狸猫来哄你。
天上星,亮晶晶,我站桥头望北京……
小红孩,上南山,割荆草,编小篮,筛大米,做干饭。小狗吃,小猫看,急得老鼠啃锅沿。
……
不会在失败中找出经验教训的人,他的通向成功的道路是遥远的。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