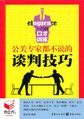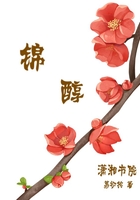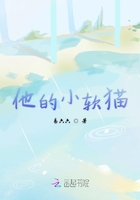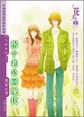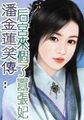生活语言的运用者虽然不必那么讲究修辞艺术,但他们却是语言的创造者,将粗糙的语言赋予了生活的情趣,特别是“任意代词”的普遍运用,使日常语言显得更为朴实而生动。
语言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都有其可以替代的词汇,语言专家早已研究透了。这里我想说的“任意代词”,是指日常语言中那些极其通俗、用途很广,又看似随意的替代性词语,尤其是某些方言土话被赋予替代功能,其含义更能让人回味。
在我们湖北,有个“霍”字在市井生活中运用得相当普遍:“霍他的人!”是说要揍他;“几口就霍了一碗,”形容吃饭速度快;“他们都霍上来了!”形容某种阵势与动态;“一座楼房几下就霍起来了,”是指干活效率高。“霍”字近似“搞”,但又有别于“搞”,并且带有一种气势,因而很多劳动阶层的人乐于使用。找不出准确的动词时,就用“霍”,有时撇开正规的语言不用而偏要用“霍”,因为在它流行的区域内,它比某些规范的字眼更贴切,更能传神。还如,形容某人食量大,不说他能吃而说他“能嗨”,这同样是一种“有意借代”,是为了增强语言效果。
我们这里很多地方还流行一个“噪”字,要想找出与它准确对应的词比较难,可它也能替代多种涵义。如“你噪什么噪!”意思是你凶什么,你别凶,你别狠,但又不完全与之等同;又如“只有老张能噪住他,”这里的“噪”,是指老张具有一种权威、能力或声势能够将对方驾驭,或压倒对方;还如“把他噪死,”意思是平时要将对方牢牢卡住。“噪”字,有点像南方非卷舌音读出的“罩”,但其意又大有区别,只有本地人能够听懂。
我们老家一带,某人与对方谈得不投机,就可能冒出一句:“你别给我尼格浪!”这个“尼格浪”纯粹是方言,没有谁考证过它的来历,我想它或许来自某个戏剧的唱词或细节。当地人用它时,甚至发音都不一致,更没人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但并没有影响它在日常对话中的作用。“尼格浪”是对对方不满的表示,含有糊弄、装聋作哑、答非所问等多方面的含义,同时也表示自己清醒,善于识破别人。并且,类似代词都具有两方面的功能,由说话的环境、时机、语气和表情决定它们的含义,听话者对其解意也不会发生误差。如果向对方表示某种好感,有时也使用“尼格浪”,对方听起来反倒感觉出一种温暖和亲热,这时它又演变成一句“亲近的骂语”。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生活语言中使用最多的代词是“那个”,它常常被当作语言交流中的“赖子”,搜寻不到适当词汇时,就用“那个”来替代。比如“你见到他,尽量那个一些,”这里指的是待人态度,或者是冷淡轻慢,或者不卑不亢,或者是主动大方,等等,被点拨者心领神会,自会准确地选取其一。很多情况下它也被用来表达不满,以它替代对方行为的失当、言辞的过分或态度的不妥等等。有时还被用来替代某些不便于明说或难以启齿的言语,比如“他和她那个了”。因为“那个”属于汉语中的通用词汇,所以被借用的频率很高。
有时需作含蓄表达,也离不开替代词汇。不知从何时起,女性称例假为“大姨妈”,例假本来就是一个代称,换上“大姨妈”或许更生活化一些。这个代称可能来自某个故事,其实称其为小姨妈或大姑妈、大奶妈、二姑奶、姑奶奶,别人也都能领会。这一点,更能证明生活语言中这类代词的“任意”性质。还有更简捷的,“她有了么?”这里的“有”,可以看成故意省略,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代词,用来代替“有喜”或“有孕”,这是日常语言在某种情况下的回避。
“任意代词”在生活语言中大量出现,是由大众层面日常语言交流的实用性、简便性、通俗性、生动性和某种程度的粗鄙化决定的。生活语言的运用者虽然不必那么讲究修辞艺术,但他们却是语言的创造者,将粗糙的语言赋予了生活的情趣,特别是“任意代词”的普遍运用,使日常语言显得更为朴实而生动。当然,无论多么巧妙的任意代词,都必须以规范语言作前提,必须用规范语言先做铺垫。
人为某事而诞生,并不是为无所事事而诞生。
——武者小路实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