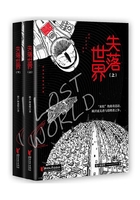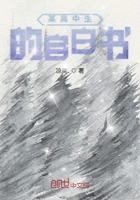倪文俊十万红巾打武昌,原本是可以稳操胜券的。
武昌守敌不足万人。湖广行省的官员们,一向是看威顺王爷的脸色行事,每遇战事,皆听从这位带金印独揽一方征伐大权的王爷调遣。前些日子,王爷遣参政阿鲁辉去招募湖湘溪洞的苗军前来助战,苗军首领杨完者倒是一员悍将,但尚在途中,不知何日可来。进攻中兴的四川元兵,仗打得很艰苦,城池得手后总是逗留不前,并无东援省城的意思。大都朝廷也急了,无奈何只得远调江浙行省平章卜颜帖木尔溯江而上,驰援武昌。但远水难救近火,宽彻普化只好带着王府的妃妾、儿女,在怯薛们的护卫下,夜开城门,逃之夭夭了。
倪文俊占了武昌。红巾将士皆大欢喜,省城花花世界,谁不想到这儿扬眉吐气逛一逛呵。倪文俊带亲兵住进了威顺王爷的府第,这儿依山傍水,飞檐翘角的殿堂与绮窗绣户的阁楼参差错落,掩映在重重绿荫之中。回廊曲径,入山,鸟鸣声声;绕水,荷叶田田。到处是花团锦簇,以及花团锦簇中的舞榭歌台。他甚至在几处阁楼的栏杆上还看见了金丝鸟笼,笼中的鹦鹉仍在学舌。但人呢,那些美姬与歌女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位渔家子出身的草莽大帅,生性喜欢水。一天,他弄了一只小舟,叫了几个亲兵随行,就到湖中荡水去。湖上白鸥点点,小舟逐鸥而去,不觉就到了湖心岛上。岛不大,但绿树成荫,绿荫深处有一佛寺小庵,一圈赭色的砖墙围着,佛堂庭园,甚是清雅。倪文俊信步直入堂奥,看门的老仆哪敢阻拦,只得跟随其后,垂手侍立。佛堂正殿遮着帷幕,倪文俊不耐烦地掀开帷帐,嗬,佛殿上供的是什么玩意?好一群光怪陆离的怪物,尽是些人首兽身,或兽头人身的牝牡两性,赤裸着作疯狂的交媾状。
“我操他奶奶的,这是什么佛?”倪文俊喝问。
“欢喜佛。”老仆不敢抬头,低眉答道。
“什么人在这儿拜佛?是男还是女?”倪文俊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的口气和缓下来。
“王妃月察孛儿。”老仆依然低着眉,低声回答。
“嗯,是她,果真是她。”这位草莽大帅是熟悉风骚女人德性的。转过佛殿,紧挨着的,就是修炼的禅室了。推开门,便有一股浓郁的异香扑鼻而来。倪文俊一个激灵,陡然兴奋起来:“安息香!这是那个女人身上的安息香。”
随行的亲兵问:“是哪个女人呀?丞相。”
“天下第一美人月察孛儿。”倪丞相不屑地白了亲兵一眼。转过头来,他问老仆:“人呢?她人在哪儿呢?”
老仆说,王妃早随王爷逃离武昌了。不过,他遵王妃所嘱,每日照例给她屋子里烧一炷安息香。倪文俊阴沉着脸,数年前的一幕不断在他脑海中闪现,那是省城例行的迎佛盛会,他挤在人流中有幸瞻望到黄鹤楼上那些王府妃妾,那时盛会散场,妃妾们的轿舆从他身边走过,刚巧,一个美艳得令人炫目的美姬掀开轿上窗帘观望市容,人们立即嚷道:“这就是王爷最宠的爱妃月察孛儿。”一会轿上窗帘放下了,一股浓郁的异香却从美人身上袭出,钻进他的鼻孔,钻进他的心里,再也挥之不去了。他当时在心里愤愤地骂了一句:“王妃,王妃,还不是从民间抢来的。有朝一日,我也能抢!”天遂人愿,他现在居然就抢到王府来了,绰号倪蛮子的他,现在是王府的新主子了。
禅室就是卧室,女人起居梳妆的陈设,一应俱全。那张沉香木的卧榻尤其宽大,雕花镂凤的床楣上,十分显眼地嵌着一对象牙琢成的戏水鸳鸯。
“丞相,你不是说打下武昌,让哥们儿滚一滚王府的象牙床吗?”几个年轻的亲兵嬉笑着,竟跃上牙床打起滚来。原本阴沉着脸的倪丞相这下真的动火了,他像鹰抓小鸡一样提起几个小兵,又是耳光,又是拳脚,叫他们一个个都滚,滚开,不准再上这个湖心小岛。
倪文俊身边的侍从换了人,他喜欢去那个湖心小岛,喜欢歇息在那间禅室的卧榻上。现在在他身边侍候得最殷勤的,是新近归顺红巾的一个王府虞候,倪丞相毕竟是草莽大帅,每日处理完军务,他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夜晚总不能叫他独守空床呀。这虞候对大帅可算体贴入微,每每能弄来市井中的歌伎、娼女,供他消遣良宵。不过,事后虞候也常听到大帅咕噜:“都是些俗物,贱货!”
而今这省城的新贵,天完丞相倪大帅究竟在想些什么呀,虞候琢磨着,不敢怠慢。一天,倪大帅忽然问他:“我说虞候,你看这湖广地界,什么官最大呀?”
“当然是大帅你,你做丞相的官最大。”虞候谄笑道。
“放屁!我问的是湖广官府中的官。”倪文俊喜欢单刀直入不拐弯。
“噢,噢,自然是平章,平章政事了。这是从一品的朝廷命官,亚相,亚相,就是朝廷副宰相了。”虞候见机转舵,顺着大帅的意思说。
“如果我归顺朝廷,皇上能给我一个平章当吗?”倪大帅的简单直率,令虞候大吃一惊。
“大帅在说笑话。”虞候不知对方虚实,想支吾着离去。
“你不要走。”倪文俊拉住虞候,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对方,仍然是草莽汉子的率直:“信,托你交给威顺王爷,王爷是当今皇上的叔祖,他在皇上面前说得起话。虞候你也知道,王爷的大公子在金刚台被我捉了,现在还在我手中。这事若成,放人;这事若不成,我可要杀人了。”
这虞候连夜出城,将倪文俊挟人质求招安的信带了出去,这信经威顺王爷之手,又传到了大都朝廷。
倪文俊的算盘打错了。求招安一事,不管是真是假,这对吃了败仗的元军来说,都是一个绝好的契机,他们托言皇上有意恩准,正交付大臣廷议,以此拖延时间。一面密令阿鲁辉招募的苗军,化装为乞丐、流民,窜入武昌潜伏起来,一面又催促江浙元兵昼夜兼程,溯江而上直扑过来。倪文俊尚在王府中做着美梦,突遭内外敌人的偷袭和夹攻,猝不及防,损兵折将,匆匆得来的城池,又匆匆丢失了。
元军攻占了武昌。愤怒的倪文俊手刃了威顺王的大公子别帖木尔,用长竿挑起人头,悬于王府大门前,让这颗血淋淋的头颅,去迎候他父王的归来。
继四川元兵之后,江浙元兵也进入了湖广,红巾军与元兵形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兴,安陆,黄州,蕲春……不少城池朝秦暮楚,几易其手。但沔阳因有明玉珍的多年经营,兵强马壮,百姓归附,元兵多次进犯,都被打了回去。倪文俊率溃兵退回沔阳后,元兵尾随而来,一场大战又在汉水边的汉川县打响了。
威顺王宽彻普化率数千怯薛为前导,亲督四十艘楼船巨舰进攻红巾水寨。倪文俊佯败,一连放弃好几个据点,沿途扔下不少辎重,一直退到一个叫鸡鸣汊的地方,方才与明玉珍的大军会合在了一起。
面对来犯之敌,如何收拾他们?
“宽彻普化那龟孙子已钻进了我的口袋,前几日我已遣一员裨将切断了他的退路,现在,是坛子里面抓乌龟了。哈哈哈哈!”倪文俊要雪武昌兵败之耻,又很欣赏他狡诈的诱敌战术。他那带有明显刀痕的眉毛耸动一下,接着转向明玉珍问道:“明将军,你我谁先下手呀?”
玉珍瞥了倪丞相一眼,并不计较他凌人的盛气,沉着气平缓地反问道:“丞相,你看这乌龟该怎么个抓法?”
“两军相逢勇者胜。用我的多桨快船,前后左右,四面围攻呀!”倪文俊是水上豪杰,他的多桨快船疾如旋风,曾多次令官军闻风丧胆。
“但眼下形势,天助丞相,不知丞相有无觉察?”玉珍不紧不慢,胸有成竹。
“啥?你说啥?天助丞相,天助我倪蛮子?”面对眼前这位常胜将军,倪文俊不敢小觑。
玉珍近前,微微俯下头来,附在身材矮壮的倪蛮子耳根下,如此这般细述一遍。
“妙计,妙计!”绰号倪蛮子的红巾大帅不由一巴掌拍在玉珍肩上。随即,便开始调兵遣将。
宽彻普化一路破敌,接连收复了好几座县城,开初,他还怕孤军深入,腹背受敌,但每次接战,这些裹红巾、着赭衫的草寇,皆是一触即溃,于是他便放胆穷追,扬言要活捉倪蛮子,活剐寇仇,以雪杀子之恨。
“父王,今已秋去冬来,北风寒冽,士卒们征衣单薄,是不是休整几日再战?”王爷的二公子报恩奴金盔金甲,此次破贼,屡立战功,他立于舰首,向父王献策。
王爷斜睨了他一眼,不屑答话,转头瞭望战舰前方。
“杀大哥的仇人就在前头,我们怎能放他逃脱!”随军作战的三公子接待奴、四公子佛家奴齐声嚷嚷,他们初上战场就遇上了连战连捷的好运,也想擒几个红巾草寇,好在众人面前表表功。
忽然,前方芦苇滩中,惊起几只水鸟,水鸟惊飞处,一条小小的渔舟荡了出来。一个簑衣渔父长声吆吆“啊嗬嗬,啊嗬嗬”地吼了几嗓,便一边荡桨,一边唱起了水上渔歌——
老子本姓天,生在江湖间。
杀人又越货,阎王也不管。
战火横飞之地,谁敢在水上撒野?怯薛们喝令渔舟近前。那渔父并不理睬,各自荡桨。当战舰前行,靠近渔舟之际,那渔父陡然揭去斗笠,从笠中抽出短弓,嗖嗖嗖,连发数箭,舰首几个怯薛,立时中箭落水。
“倪蛮子!他是倪蛮子。追,快追!”王爷看清了渔父面目,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四十艘巨舰尾随倪蛮子,报仇心切的王爷父子,只顾催桨手快划桨,没想到前面滩多水浅,前后有几只战舰搁了浅,整个舰队便瘫痪在芦苇滩中了。
未待元军反应过来,芦苇荡里一声呼哨,潜伏滩中的芦苇筏子顿时着火,火筏铺天盖地扑向楼船战舰,茫茫水天之间,霎时一片焰烟火海。
喊杀连天,元军大乱。王爷的三个公子慌忙换乘快船,掉头逃窜,但迎头却碰上了红巾水上英雄——当年杀渔霸的万三奴,而今明玉珍的义弟明二将军。明二将军挥舞一杆大刀,不到三二回合,手起刀落,接待奴、佛家奴便成了刀下之鬼。另一条船上的报恩奴陷入重围,无计自救,也只得长叹一声,挥剑自刎了。
在怯薛的护卫下,王爷宽彻普化逃到了岸上。王爷身后,还跟随着一个眉目清秀的青年将佐。他们刚转上一个岔路口,只听得前头猛喝一声,一彪人马挡住去路,为首一人,正是左眉上有明显刀疤的草寇大帅倪蛮子。
怯薛连忙挥刀迎战,倪大帅左右骑将一齐上前厮杀。“宽彻普化龟孙子,今日看你往哪里逃!”倪大帅驱马直前,本来是要生擒王爷的,但忽地山风骤起,一股异香扑鼻而来,直入他的肺腑。倪蛮子一个激灵,愣怔一下,不由打量起王爷身后那位骑白马的将佐。“噢,好清秀的面目,我在哪里见过?”倪大帅在心下嘀咕着,迅速搜索脑海深处的记忆,陡然,他不禁一阵暗喜:“莫非是她?嗯,是她,是她!”草莽大帅放过王爷,策动胯下乌骓马,径直前来擒她。这白马将见事不妙,掉头就跑。倪蛮子岂肯放过,盯住她紧追不舍,白马在前,黑马在后,二马一前一后在山道上狂奔着,不一会,便转过山口消失了踪影。
白马将确是军帐中随侍王爷的王妃娘娘,王府中湖心岛上那间禅室的主人月察孛儿。月察孛儿毕竟是女流之辈,跑了几个山峦后,她慌不择路,钻进树林,左寻右觅,失了路径。倪蛮子却是惯于钻山林的草寇,他轻而易举就绕到她身后,悄无声息,一把便将她扯下马来,掀掉她的头盔,那青丝云髻顿时露了出来。“啊哟,我的王妃娘娘,你让我想得好苦!”倪蛮子耸着鼻子,猛吸了一口她身上袭来的异香,欲火早撩得他十分难捺,不容分说,三下五除二,顷刻间他就褪去了她的戎装,把她赤裸裸地横陈在这个僻静的林下,疯狂地颠鸾倒凤,兴云作雨……好一阵子,他才疲惫地从她身上爬起来。月察孛儿并不挣扎,也不反抗,只是用手梳理一下纷乱的鬓发,反而故作媚态,娇嗔道:“大帅太性急了!你军帐中恐怕还没有压寨夫人吧。妾谢大帅不杀之恩,走!我跟你走。”
就这样,王妃娘娘摇身一变,竟成了倪大帅军帐中新一轮压寨夫人。
美人的诱敌,使王爷得以逃脱生死劫。几骑怯薛护卫着威顺王宽彻普化远逃到了陕西,一个败军之将,他无颜回大都见皇上,羞愧难当的落魄王爷,后来只好绕道四川去了云南,依附在那儿做梁王的堂兄弟车力帖木尔,远避烽火连天的中原,去度他的残年日子去了。
江浙平章卜颜帖木尔就没有王爷那般颟顸、愚蠢,他是一个善于掩藏自己锐气的老狐狸,在同僚中表面上卑言谦辞,暗中他却盘算好了一着擒贼擒王,以邀头功的险棋。他的妙招得到大都朝廷的首肯,于是,淮西元兵从东线,四川元将哈林秃从西线,河南元兵从北线,占领武昌的江浙元兵从南线,步步紧逼,很快合围,团团包围了天完红巾的莲台省蕲都。
徐寿辉原本是光杆皇帝,兵权尽在部下将帅手里。天完朝廷的太师邹普胜,探知卜颜帖木尔已打造好了槛车,随时准备擒住天完皇帝,献俘阙下,他一时吓破了胆,托言出城搬救兵,扔下徐寿辉,匹马单身跑到黄州,投靠陈友谅去了。
“徐主首义,功盖天下。而今勤王护驾,我陈友谅绝不落在人后。”陈友谅一双鹰眼闪闪烁烁,平日狡黠的目光,更增添了几分令人捉摸不透的神色。部将们都知道,主帅言辞字面上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言辞背后的深意。果然,他接下来就不忘笼络手下的将佐了:“不过,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只有天晓得。弟兄们随我出生入死图个啥?还不是为了吃香的,喝辣的,将来图个封妻荫子。让将士们白白送死,这蚀本的买卖我不干。”言罢,他目光凝住了,阴鸷而凶悍,盯住谁,谁都觉得有如芒刺在背。
陈友谅将主力留在黄州自保,只遣一支老弱偏师前去送死。蕲都陷落了,数百名莲台省职官僚属尽落敌手,惨遭腰斩灭族。天完皇帝徐寿辉侥幸逃脱,潜入沔阳湖黄梅山中,生死不知。陈友谅有忧有喜,忧的是元军已兵临黄州城下,喜的是天完皇帝用不着他动手弑君,自可借他人之手,取而代之。
天完政权岌岌可危,天完丞相倪文俊又在干什么呢?这位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的所谓丞相,原本是一路草莽大帅,那时他正带着月察孛儿在山中狩猎,他得到这个消息时是在一条山沟的军帐外,这一对自诩为英雄美人的狩猎者正就着篝火在烤野兔肉,随行的军校劝他出山,领兵前去救驾,他执意不允。军校苦劝不止,惹恼了他,野兔肉在他口中还未咽下,他呸的一声,将满口的唾沫和肉渣吐了那军校一脸,愤愤地骂道:“老子就是不出山!徐寿辉不过是一个木讷的偶像,庙子里木雕泥塑的菩萨一尊,也值得哥们儿去为他玩命?”倪文俊不怕死,但他贪恋山中的艳福,他一直踌躇观望,按兵不动。
明玉珍奈何不得倪、陈二帅,他深为倪文俊的草莽习气担忧,更深恶痛绝陈友谅暗藏狼子野心的阴谋伎俩,天完红巾三大帅,现在只有他一支孤军前去解围了,他心中不由有些伤感:“自青山聚义以来,我明玉珍追随徐主,志在驱逐鞑虏,以靖中夏,天完红巾大业,岂可中途而废!成败悬于天,初志不可移。”天地间赖有玉珍这颗赤子之心,沔阳红巾在“明”字帅旗的率领下,全军开拔,星夜兼程,直奔黄梅山,直扑沔阳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