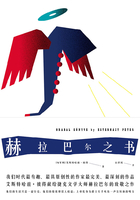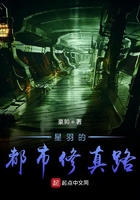挂职的梅干部听说乡上的农田基建点要往古塬村放,又听说包乡的王副县长对此事特别重视,要亲自检查的,并把这当作一项考察干部的政绩哩,心里就憋了一口气,要暗暗地露一手。
往年,麦子堆上场,农田基建搞的忙,今年开春时全乡的麦田遭了虫灾,绿油油的麦苗儿被虫子咬掉了根,全死掉了,人们就将麦田翻掉了改种了秋,没了麦子,乡政府就将农田基建提前了几天。梅开园在乡上开了会,就劲头十足地连夜在古塬村开了动员会,又和村支书全子、村主任发财、民兵连长铁军、会计小王等几人在野鸡畔规划了二百多亩的农田基建点,又一方一绺给家家户户把任务划死了,这样,所差的就是上劳了。
这天,小梅就在代销店拿了几张红纸写标语,自个低头想了半天,硬是没个合适的,就打发个学生娃去找村会计小王来商量。
不一会,留着中分头的小王就来了,见梅开园说起此茬,就说:“不是县长要来的么,咱就弄个‘欢迎领导来检查工作’,要不写上”天大旱,人大干什么的。
梅开园说:“早多少年的陈词烂调了,如今要弄新的。”又说,“如今的标语我考虑要和奔小康往一块连呢!”
小王坐着,将头伸进裤裆里,放了一颗长长的屁,憋了半天说:“你看‘农田农田小康关键,基建基建保证双千’咋响?”
梅开园觉得好,又嫌烦,就说:“干脆写农田基建小康关键”。
小王茅开顿塞地说:“好好好,这八个字简单明了热情坦荡。”
梅开园挥笔写了这八个字,小王一边端着字往太阳下晒,一边问小梅:“你说小康是个啥样子?”
梅开园说:“说是钱粮双过千,其实有个好队部、好学校就差不多了,真要按标准,县里这几年树的小康村没一个合格的。我就亲眼见过小康村的人到处借粮吃哩!至于靠贷款买化肥种地的人多的是。”又顺口问道:“小王,生产队时的红旗还在不?”
小王说:“红旗还在,只是被老鼠咬了几个窟窿,横幅却没有的。”
小梅说:“你先把红旗找出来给风珍子让洗干净了,破了的地方再想法补补。这回咱一定要把声势造大。”
俩人正说着,全子就从门里进来了,小王就又说起横幅来,全子说:“我家倒有两块被面,不知能不能当横幅?”
小王说:“能,外咋不能,多用上两块,折成窄条用针纳在一起就行了。”两人说着就忙去了。
一切匆匆忙忙准备好,就到了真正上劳的日子了,好在今年没麦子,人都不忙,烟栽上了,正疯了般地往大长。另外人们见小梅在会上咬牙切齿的,情知他是非要完成不可的,大家都有了思想准备,农田基建就该上的劳力就都上了,三天下来任务就完成了不少,可小梅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县长来检查,这可真把他急坏了。
到得第四天,早饭一吃,乡上的文书小玉就骑着摩托来到工地上,说王县长听说这儿农田基建搞得好,要亲自来检查哩,叫村里及早作准备。
全子小梅说:“家家户户都有人哩!”
小玉说:“李乡长特意安妥的,说这王县长是农业学大寨时当的支书后来又当乡长县长的,他特爱的是红火场面。像这样战线拉的太长没看头的,要把人集中起来,再说牲畜也要闹到地里,要有驴欢马叫的味。”
小王开玩笑地说:“这村里别的东西都没有,叫驴倒是挺多的。”一干人就都瞅着全子笑了起来。
小梅听了这话,就动了心眼,说:“我就觉得缺点什么,全子,你将村里人都集中到这一块地里,全子和小王把各家婆姨、老汉都集中来,学生娃今天也放假,也集中来,村里的所有拖拉机、三轮多弄些来,没有铁家俱的,就把牛驴马什么的都牵了来,要闹得驴踢狗咬的。”
全子和小王就走了,俩人也真有办法,不一会,婆姨、碎娃、老汉约摸集中了五六十个,又牵来了几匹牲口、架子车,还来了四辆三轮车,地里一下子就热闹非凡了。
小梅开全子的玩笑,说,“你日鬼的美,这些婆媳倒蛮听你的。”
小王说:“全子是咱村的镇海宝,缺了他谁也闹不动的。”
小梅说:“应该说是金箍棒更合适些。”一干人就都笑了。
全子说:“我这下反正把这些婆媳都交给你了。”又说:“村中除了这几个,再就剩拦羊的了。”
这时,就中午十二点了,王县长仍不见来,人们起先的劲头就都松懈了下来,三个一堆,两个一摊,躲在三轮车、架子车后的荫凉处搁方、搁顶的,聊起天来。
刚平婆姨坐在车辕上给孩子喂奶,两个乳白色的奶子就宛如一团馍似的白晃晃地裸露着,乡政府的小玉还没有结婚,看到这情景就馋眼了,不料,一滴涎水滴了下来,恰被全子看了个正着,就说:“看,公家人都想吃你的白奶馍哩!”小玉通红了脸,到是刚平婆媳说:“吃就吃,能养了一个就能养两个。”说忘了,那捏奶子的手一松,可就淌出了孩子的嘴,吃——一一股奶溅到了小梅的裤腿上,一时间,工地上的人就都凑来开小梅的玩笑。
小梅红了脸,将裤上奶汁擦干净了,为转移视钱,就对全子说:“我琢磨着要几个白发老婆和白胡子老头才更有形象意义哩!”说完就和小王一块去村里招呼。
小玉大声喊叫着说:“快去快回,估计检查团快来了。”
两人进了村,一眼就看见村中央的场里堆着些麦秸杆,旁边铺了一大摊麦穗,老莫老婆正用棒槌棒棒棒棒打。小梅见了,先自惊奇起来说:“这倒怪了,今年全乡麦子全遭了殃,她到收了麦子。”小王说:“这老婆能哩,前几天到女子家里住了几天,就拾了这一堆麦子,足够打两斗的。”
梅干部听了这话,心头就涌起一阵怜悯,心想:人他妈活着真不容易,都得总是想着法儿往下活。但只是一忽儿想了,到得老婆跟前就督促她到工地去,说今个家里谁也不留的,拦羊的都要往回叫哩!
老莫老婆听了,见是半地里,就斯文着不想去,说他老汉已经走了。小王就说:“你快去,要不就要罚麦哩!”老婆听得罚麦二字犹如惊弓之鸟,将棒槌扔了,颠着一双小脚跑了。
两人跑了一圈,又拾掇得两个白胡子老汉和两个老婆婆,就急急忙忙往回赶,离得老远,就照见南山里往上冒黑云团。小王说:“这天要下暴雨哩!”梅干部说:“下刀子也得在地里给我守着。”两人正闲聊,就眼见得北边的山路上尘土翻滚,有两辆小车向村里驰来。两人慌了神,奔跑着呐喊道“来了!来了!”“快点!快点!”果然这声音仿佛一针强心剂,众人都忙碌起来。
两辆小车在地畔停了,却正是王县长和乡上的赵书记及其他一干人。王县长站在地畔上一照,但见尘土翻滚,红旗飘扬,架子车、拖拉机、三轮来来往往,当此之时,人声、马叫声、机器声混响成一片,“农田基建,小康关键”八个大字耀耀闪光,地里有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有弓着背的老太爷,有柱拐杖的老太婆,地畔上还睡着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那些脱光了上衣的男人们和那些风风火火的婆姨们此时越干越欢,这种场面一下子感染了王县长,他二话不说,西服一脱,下到地里拿起锨就干。这可忙坏了县委通迅组组长强子,他忙启动照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乡上赵书记、水利局的赵局长见县长干开了活,也都操起了家具,一个个动起手来。此时,群众劲头愈大,一个赛一个的欢。
梅开园本是清闲惯了的,这阵不好意思了,就拿了锨装模作样地到全子身旁说:“这天恐怕有雨哩!”
全子抬头张望,见黑云团在烈日下翻滚着往上涌,就说“再等等看。”等了一忽儿,见一干检查人都没停的意思,全子便凑近县长说:“天不照好,恐怕有雨哩!”田县长停下手中的锨,抬头看了看,见南边的天空黑云疙瘩往上冒,又起了风,就说:“也该下场透雨了。”又说:“把人召集起来,我讲两句话。”
过了七八分钟,人们就都停了手中的活,一群满面尘土的老百姓就都被召集过来,有坐的,站的。田县长见众人都静下来,就在近处一高土台站了,说:“同志们,今天我见到这场面确实被感动了,确实和过去学大寨一个样,红旗飘飘,人欢马叫,这才真正是要大干不要苦熬,靠大干改地换天,咱这参加的有老汉、老婆、大人、娃娃,可谓男女老幼齐上阵,干劲冲天……”他的话刚讲到此,空中就炸开了雷,接着就劈哩吧啦下起雨来。平整的地里被雨点砸得虚土直冒,众人先自乱了,都纷纷操起家具往家跑。王县长也着了急,只好把长篇演讲全吞到肚里去了,只说了句“谢谢大家”,就草草收了场,向车跑去。
全子和小梅还等着王县长表扬自己哩,见下起了雨。情知没了指望,也簇拥着向车跑去。
轰隆隆隆,哗啦啦啦。
下雨啦。
车行到村里,地上已有了水淤,车从全子住的坡上下不来,只能停到塬里,一干人下了车,就往全子家跑。等得到家,衣服就全淋湿了。全子婆姨张罗着寻了几件衣服给大家换,梅干部换了一件衫,别的人都不愿换,都将衣服扭干了,又穿到了身上,全子就找了个脸盆,从灶里煨些火放到炕上。一大群人就背转了身子烤衣服。
一面再看那雨,端的是好雨,雨如一道帘幕似的扑天盖地的下,院子里只一眨眼功夫就积满了水,又倒流进全子家里来,全子着了急,就从灶火中铲了些灰土拍在门口,堆起一个高棱来挡住了。
“真是场好雨。”小梅感叹地说。
谁也没接他的话茬,因为这时,院子里传来了乒乒乓乓的响声,雨中夹杂着杏儿大小的冰雹在院子里蹦蹦跳跳的,宛如小孩在做着游戏。有几颗就蹦呀蹦蹦到了窑里,蹦到了炕边。一通人都吊着脸,不再说话。
全子的小儿子今年上一年级,此时兴致特高,从门口捡了几粒冰雹蛋,说:“咦,这么大!”就往嘴里放,全子婆媳着了急,一手给打掉了,说“吃屎的嘴,再就没得说了。”孩子吃了疼,“哇”的一声就哭,全子媳妇心里就怯了,搭讪着说:“农村讲究下冰雹就不敢说大哩,越说下得越猛。”一边拉了孩子到窑后面来,悄悄塞给几毛钱。
孩子总算哄住了,可冰雹依旧没有停的意思,稀里哗拉的。下了白花花一层,众人没话说,全子媳妇却沉不住气了,说:“今年麦子遭了虫灾,全死光了,玉米地里净是些灰包,只盘算着收一料好烟,老天偏又下起了雹子。这老天实实该杀了。”她骂着,就从案架上操起一把菜刀,“当”的一声,扔到了当院。“我一下把你这死老天给杀了”。
话一出,冰雹果然下得小了,渐渐地停了,于是众人都舒了一口气。
全子见暴雨仍下着,众人都已沉默,就提议大伙来喝几盅。政府办的小李挤了一下眼,示意着躺在炕上打盹的王县长。
梅干部说:“只喝两盅,天凉也好暖暖身子。”全子婆娘就忙张着弄起菜来。
王县长睁开了眼,说:“别忙乎了,抄点酸菜就行。”
全子说:“只炒一个鸡蛋。”就先抄了酸菜、提了酒瓶来喝。又说,“这喝酒,就象发动机器,机器发动着了,就停不下来,非喝倒不可。”
大伙笑了一通。
王县长说:“这也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呵!”
大伙又笑了一通。
酒过三旬之后,雨就小了起来,酒场可就逐渐热闹了,大伙儿你来我往,倒酒碰杯,不亦乐乎。全子提议和县长划几拳。王县长起初不应称,乡里的赵书记说愿代县长喝一半酒,县长才勉强同意了,可一伸手,果然不凡,连赢了全子三个。全子偏又不服气,吹嘘自己是西北高手,今个可就栽了,非要再来不可。
此时,小梅也正在凑哄热闹,全子婆姨用手指戳戳他,用嘴努努外边,小梅情知有事,就悄悄走了出来。
外边雨停了,只有浓云还没有退尽,遥远的村子对面的黑疙瘩峁上有一方灿烂的阳光。大门口铁军和小王招手叫梅干部。
小王说:“可不得了了,老莫老婆子拾的麦子全让水给冲走了,这阵正在场里哭着骂哩!”
“真有这事?”小梅吃了一惊。
“可不是哩,你说这事可该咋办哩么?”民兵连长铁军搓着胖乎乎的双手。
三人出得门,走得几步,梅干部静下耳朵,果然听到了老婆婆的哭诉声:
老天爷呀——开开眼呀,
麦子地里——净虫子呀,
玉米地里——灰包多呀
烤烟地里——雹子打啦。
一点麦子——叫水推(淹没)啦。
……
那哭声,似唱歌一般,一咏一叹,如泣如诉,声调悠长而凄凉。在这种生机勃勃的世界里猛地听到这种哭声,倒平添了几份恐怖,梅干部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身子。
小梅说:“你们俩上去让她别哭了。”
小王说:“刚才劝她她不听,拉她她也不走。”
“要不,强行把她架走算了。”铁军说。
“这——”梅开园迟疑了一下“恐怕事情弄反遭了不好收场。”
三人相跟着一同上得塬,就照见场里干干净净的,有几处水淤中隐约漂浮着一些麦壳,场边地有一些麦杆和杂草搅和在一起。场中央老莫老婆全身都是泥和水,跪在场中央哭诉着。见他们来了,情知没好事,就心虚地住了嘴,嘴里嘟囔着不出声。但还是没有起身的意思。
三人包围着站了一圈。小梅训斥道:“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老婆婆听得这话就停住了,哽咽着不敢吭声。
见她还没有走的意思,小梅沉下脸说:“再不走,就把你抓起来让你坐牢。大白天的你搞什么封建迷信!”
“迷信?”铁军不解地问小王。
小王没有回答铁军,而是声俱厉下地说:“你刚才哭老天爷瞎了眼,那来的老天爷,这不是宣传封建迷信是什么!”。
老婆婆大约害怕被抓起来坐牢,十分不情愿地起了身,走了。
等走远了,铁军“噗嗤”一声笑出了声,伸出大拇指说:“高!高!”
梅开园回到屋里,窑里已收了酒场,全子酣睡着,县长打蒙着眼,问:“天晴了?”
“天晴了。”
“该能动身回了。”县长话说是说了,却并未动身,而是更舒服地将身体往被子上倚了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