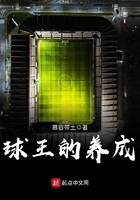四月十一日,星期一,下午三点。
“坐,派恩,”万斯友善地说,“狄勒教授已经同意让我们问你几个问题;而我们希望,每个问题你都如实回答。”
“一定,先生,”管家回答道,“我相信,狄勒教授没什么好隐瞒的。”
“太好了,”万斯懒洋洋地靠椅背上说,“那我们就开始吧。今早,这里几点钟吃早餐?”
“八点半,先生,跟往常一样。”
“家中所有人都一起吃吗?”
“是的,先生。”
“是谁叫大家起来吃早餐的?在几点钟?”
“是我叫的,在七点半,我敲门……”
“然后等他们回应?”
“是的,先生,一向如此。”
“你再想想,派恩,今早是否每个人都有应门?”
管家点点头:“有的,先生。”
“没有人下来比较晚吃早餐?”
“每个人都很准时下来,跟平常一样,先生。”
万斯坐直身,把烟按熄在烟灰缸里。
“今早吃早餐前,你有没有看到谁曾经出去再回来?”
虽然这问题问得轻描淡写,但我看到管家深陷的眼睛里,掠过一阵惊讶。
“没有,先生。”
“虽然你没看到,”万斯追问,“可不可能,有人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进出这房子?”
这是派恩在这次问话中第一次迟疑。
“这个嘛,先生,其实,”他有点紧张地说,“确实有人可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从前面大门进出,也可能从射箭室的门离开,因为当时我在餐厅里布置餐桌。我女儿在准备早餐时,通常会关上厨房的门。”
万斯若有所思地抽了一会儿烟,用平稳的语调说:“这屋子里有没有人持有枪支?”
管家睁大了眼。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先生。”他结结巴巴地回答。
“派恩,你听过‘主教’这个人吗?”
“我没听过,先生,”他的脸色惨白,“你是说,那个写信给报社的人吗?”
“我只是说‘主教’,”万斯不经意地说,“告诉我,你有没有听说,今早有人在河滨公园被杀了?”
“有的,先生,隔壁的工友刚告诉我这件事。”
“你也认识年轻的史普立克先生,对吗?”
“我见过他到这儿来过一两次,先生。”
“他最近来过吗?”
“上周来过,先生,我记得是周四。”
“当时还有谁在?”
派恩皱着眉头,似乎正努力回想。
“还有杜瑞克先生,”过了一会儿,他说,“帕帝先生也在,他们都在安纳生先生房里一直聊到很晚。”
“在安纳生先生的房里?安纳生常带客人到他房里去吗?”
“不是的,先生,”派恩解释道,“那是因为教授当时正在图书室里,而狄勒小姐跟杜瑞克夫人正在会客厅。”
万斯沉默了一会儿。
“派恩,我的问题问完了,”他缓缓地说,“请你替我们把毕朵叫过来。”
毕朵急切地朝我们走来,站在我们面前。万斯问了一些跟之前一样的问题,她的回答对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但就在访谈结束时,万斯问她,在今天吃早餐前有没有朝窗外看过。
“我往外看过一两次,”她回答说,“难道我连看看外头都不可以吗?”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出现在射箭场上或是后院?”
“除了教授跟杜瑞克夫人,没有别人。”
“没有陌生人?”万斯的样子让人觉得狄勒教授跟杜瑞克夫人这天早上出现在后院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从他缓缓把手伸进口袋掏烟的动作,我知道,他已被这消息深深震撼了。
“没有。”女厨答道。
“你是几点看到教授跟杜瑞克夫人的?”
“大概八点钟吧。”
“他们在谈话?”
“是啊——反正,”她补充,“他们就在花圃边走上走下的。”
“他们时常这样,早餐前到后院散散步吗?”
“杜瑞克夫人经常很早就下来,在花圃边散步;我想教授也有权利,在任何他高兴的时候,到自己家的院子里散散步。”
“我没有怀疑他散步的权利,毕朵,”万斯温和地说,“我只是好奇,他平常也会这么早到后院履行这项散步的权利?”
“今早他不就履行了吗?”
万斯让女厨离开后,站起来走到面前的窗边。显然,他脑中塞满了难解的问题,好一阵子,他站着看向窗外的河畔跟街道。
“嗯……”他低声自言自语道,“今天是个跟大自然接触的好天气;早上八点钟,百灵鸟正展翅翱翔,搞不好嘴里还叼着一只小蜗牛。但是,老天,这一切都出问题了。”
马克汉看出了万斯的困惑。
“你有什么想法?”马克汉问,“我倒是觉得不必理会毕朵的话。”
“问题是,马克汉,对于这件案子,我们没法‘不理会’任何信息,”万斯并没有转头,他面对着窗外静静地说,“我也同意,截至目前,毕朵的供词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只是知道,这出戏当中的两个主角,今早在史普立克被害之后不久,在后院中散步。教授跟杜瑞克夫人之间的这场谈话,当然很可能只是巧合;但是,老教授对这夫人这么感性的态度,很可能和那次谈话直接有关……我想,也许我们得再私下找他好好谈谈这事……咦?”
他的身体前倾,贴近窗边说:“啊哈,安纳生回来了,看起来他挺兴奋的。”
过了一会儿,就传来钥匙打开前门的声音。穿过大厅的安纳生看到我们之后,快速冲进会客厅里,连招呼都没打,就冲口而出:
“我听到史普立克被枪杀的消息,到底怎么回事?”急切想知道答案的眼睛,扫过现场每个人的脸,“我猜,你们来这里是问我关于他的事情吧?好啊,那就问吧。”
说完,他把那厚厚的公事包往茶几上一丢,然后把自己抛到一把椅子上:“今早有个警察来学校,像闹剧中跳梁小丑似的问了一些蠢问题。说了一堆什么神秘啦、谋杀啦……还问我们对这位约翰·E·史普立克了解多少等这类问题,把几个大三学生吓坏了,看来他们接下来整个学期的心情都会受到影响,而且还害得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英语讲师精神差点崩溃。当时我自己正在上课,倒是没见到这小丑。听说他竟然还问他们,史普立克平常爱跟什么样的女人交往。拜托,史普立克和女人?那孩子的脑子里,除了功课什么也装不下。他是我们数学资优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从来不缺课。今早点名没到,我就知道一定有事。中午吃饭时,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这桩谋杀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也不知道,安纳生先生,”万斯一直仔细地观察他,“不过,关于你那破案方程式,我们有新的因数提供给你。今早,约翰·史普立克被一把短枪射穿头部毙命。”
安纳生一动不动地瞪着万斯好一会儿。接着,却仰头大笑起来:
“又来了,就像公鸡罗宾之死一样……来来,简单说明一下案子。”
万斯简单叙述了一遍案情。
“这是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他说,“安纳生先生——你有什么看法吗?”
“拜托,当然没有——”他十分吃惊,“一点也没有。史普立克……我教过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十分有天分。可惜,为什么他父母要给他取约翰这名字呢?还有很多别的名字啊,因为这样害他被个疯子一枪毙命。显然罗宾被箭射死,跟这是同一个人干的。”
他搓搓双手——此时他已经变成一个理论性的哲学家,“这是很好的问题,你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吗?我必须掌握每一个因数。也许在解答的过程中,我会发现一套新的数学理论也说不定——就像凯普勒,”他咯咯笑了起来,“还记得凯普勒的‘宇宙和谐论’”吗?后来它成了微积分的重要理论基础。凯普勒是在制作葡萄酒架时想出这套理论的,他当时想,要怎样才能用最少的木头构建出最大的贮放空间。搞不好,我这破案公式,也会为科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的领域呢,哈!那罗宾跟史普立克也会名垂不朽。”
尽管我知道,这人一辈子都跟抽象的理论为伍,但他这种幽默实在让我倒胃口。不过,万斯似乎不以为意。
“有一件事,”万斯说,“我忘了提。”他转身向马克汉要那张写着数学公式的纸条,递给安纳生,说,“我们在史普立克的尸体下,发现这个。”
安纳生不屑地看了看那纸条。
“原来,主教跟这案子也有关。纸张字体跟主教的字条是一样的……但是,他打哪儿弄来这雷曼—克瑞斯托弗尔张量公式?为什么不是其他张量,像G、∑、τ之类的,几乎每个对应用物理有兴趣的人,都会迷上这些公式,但这一个实在太冷门了。而且,我觉得怪怪的,好像……哦,老天爷!那晚我才跟史普立克在讨论这公式呢!他还把它记了下来。”
“派恩说,史普立克是在周四晚上来过这。”万斯说。
“哦,他说的?他是这么说的吗……周四,是了,帕帝也在这,还有杜瑞克,我们在讨论高斯的理论,然后提到这个公式。是杜瑞克先提起的,之后帕帝还提到,要把什么高深数学理论用到西洋棋上……”
“对了,你也下西洋棋吗?”万斯问。
“以前下,现在不下了。不过,那是很棒的游戏。”
“你有没有研究过帕帝布局法?”
“可怜的老帕帝,”安纳生微微笑道,“他倒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基础数学家,应该去当高中数学老师的,可惜太有钱了,把时间都花在西洋棋上。我告诉过他,那套布局是不科学的,甚至向他解释过缺点在哪里,可他就是不听。后来,卡帕布兰加、维德玛和塔塔科瓦那些人出现,把他打得落花流水,完全跟我之前预料得一模一样。从此,他一生也毁了。接下来的好多年,他还在想另一套布局法,但始终不能成功。他还不断读威尔、西伯斯坦、艾廷顿和马赫的作品,希望能从里面得到灵感。”
“实在有意思,”万斯将火柴盒递给安纳生时说道,“帕帝跟史普立克很熟吗?”
“噢,不,只在这儿见过两次。不过,帕帝倒是跟杜瑞克很熟,常问他一些数学上的问题,希望可以借此找出一些突破性的棋术。”
“对于你们那晚讨论的雷曼—克瑞斯托弗尔张量公式,他也很有兴趣吗?”
“应该不会有兴趣,离他熟悉的领域实在太远了。那些关于时空概念的理论,很难跟棋盘搭上边的。”
“对于在史普立克身上找到这个公式,你有什么看法?”
“我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要是上头有史普立克的笔迹,我会说,这可能是从他口袋里掉出来的。但像这样,我实在不懂,谁会这么大费周章用打字机打出这个公式?”
“很显然,是主教。”
安纳生将烟斗移开嘴边,笑了起来,说:
“是主教X,我们必须把他找出来。他实在令人难以捉摸,也太离经叛道。”
“显然正是这样,”万斯说,“还有,我差点忘了问你:狄勒家里有没有手枪?”
“哈哈哈!”安纳生放声大笑,“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抱歉,让你失望了,答案是:没有。没有手枪、没有玄关、没有密道,一切都非常透明。”
万斯叹了口气,说:
“真是太可惜了,我本来有个想法……”
这时,贝莉儿·狄勒悄悄从大厅走来,正站在走道上,显然刚听到万斯的问题以及安纳生的回答。
“西古德,我们家有两支短枪,”她说,“难道你忘了那把老手枪,我在乡下打靶的那支……”
“我以为你很久前就把它丢了,”安纳生站起来,为她拉了把椅子,“那年夏天我们从霍帕空回来后,我就告诉你,在这个国家里只有强盗跟坏蛋才能拥有枪……”
“但那时我不相信你说的话,”女孩说,“我向来搞不清楚你什么时候是在开玩笑,什么时候是在认真说话。”
“你把它留了下来?”万斯问。
“哦,是的,”她望向希兹求助,“难道不行吗?”
“我想,就技术层面来说,这是不合法的,但是,”万斯露出令她安心的微笑,“我想,警官应该不会动用苏利文法案来找你麻烦的。这两把枪现在在哪?”
“在楼下射箭室,置物柜的一个抽屉里。”
万斯站起来说:
“狄勒小姐,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带我们去看你放枪的地方?我很想看看这两把枪。”
女孩显得有些犹豫,望着安纳生求助。
安纳生点头,她二话不说便转身走向射箭室。
“枪就在靠窗的抽屉里。”她说。
她走上前,拉出一个靠边的小抽屉。抽屉的后方,一堆杂物之下,有一把点三八自动手枪。
“咦?”她尖叫,“怎么只有一把,另一把怎么不见了。”
“那是把小枪,是吗?”万斯问。
“是的……”
“一把点三二?”
女孩点点头,然后一脸狐疑地望着安纳生。
“枪不见了,贝莉儿,”安纳生耸了耸肩,对她说,“我也帮不上忙,可能是其中一位年轻射手厌倦了在射箭场射箭,决定拿把枪把自己干掉……”
“拜托别闹了,西古德,”她央求,带着一点恐慌,“是谁拿去了呢?”
“哈,又一个黑色悬案,”安纳生说,“一把点三二离奇失踪。”
见到女孩的惊恐,万斯换个话题:
“狄勒小姐,能不能请你带我们去找杜瑞克夫人?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跟她谈谈。我猜,你既然人还在这里,你们之前计划的骑马之行,应是取消了吧?”
女孩脸庞闪过一阵哀伤的阴影。
“哦,你今天可不能去打扰她,”她的语气听了都会让人难过,“玛意夫人病得很严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带她上楼时她还好好的,但当她看到你跟马克汉先生出现,她整个人都变了,变得好虚弱……她心里一定有些很难过的事情,我扶她上床时,她口中不断念着‘约尼·史普立克,约尼·史普立克’……我给她的医生打电话,医生也立刻赶来,说她需要安静休息……”
“当然,没什么重要的事,”万斯说,“我们可以等改天。狄勒小姐,请问她的医生是谁?”
“是惠特尼·巴斯迪。据我所知,一直都是他给她看的病。”
“是个好医生,”万斯点点头,说,“全国现在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医生了。没有他的允许,我们绝不可以找她。”
狄勒小姐满怀感激地看着万斯,接着就告辞离去。
当会客厅里再度只剩下我们几人,安纳生走到壁炉前,别有深意地看着万斯说:
“‘约尼·史普立克,约尼·史普立克,’哈!玛意夫人原来早知道这件事。虽然她行动不便,但脑筋倒是清楚得很。人的脑袋,实在是高深莫测,欧洲有些智力胜过电脑的人,在生活上其实是个大白痴,我认识几位西洋棋大师,还需要护士来照顾他们饮食起居呢。”
万斯似乎没听到他的话,径自走到靠近射箭场的一个小柜子边停下,被一组中国古玉雕吸引住了。
“这大象不应该摆在这里的,”他指着柜子里其中一个小东西说,“那是赝品——假的。仿得非常好,却是假的,可能是仿清朝赝品。”他转过身去对马克汉说:“马克汉,我们也只能查到这里了,还是走吧。不过,在离开前我还想跟教授再说几句话……安纳生先生,能在这儿等我们一下吗?”
安纳生挑挑眉毛,显得有些惊讶,但随即换了一副无所谓的微笑。
“噢,没问题,你们去吧。”说完,就开始为烟斗添加烟草。
狄勒教授对于我们二度造访,显得十分不悦。
“我们听说,”马克汉表示,“今天上午用早餐前,你和杜瑞克夫人曾经谈过话……”
狄勒教授脸部肌肉愤怒地鼓起。
“我在自己花园里跟邻居聊天,难道也要劳驾检察官大人关心吗?”
“当然不敢,教授。只是,我正在进行一件案子的调查,而这件案子跟你家有密切关系,所以我想应该能得到你的协助。”
老先生依然不满地抱怨了好一会儿。
“行啦行啦,”他不耐烦地说,“除了杜瑞克夫人,我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人——这是你想知道的吧?”
万斯介入两人的对话:
“狄勒教授,那不是我们来找你的目的,我们只是想知道,杜瑞克夫人今早是不是对你说起河滨公园发生的事?”
老教授本来又想发飙,但克制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
“没有,她没有提起那事。”
“她看起来有没有不自在,或情绪激动?”
“没有!”狄勒教授站起来,对着马克汉说,“你们想干吗我非常清楚,但我帮不上忙。我已经告诉过你,马克汉,我不会替你们当间谍,或是给这不快乐的女人增加困扰。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些了,”他回到自己的书桌旁,“很抱歉,今天我很忙。”
我们退到大厅,向安纳生道别。他挥手向我们示意,但他的微笑中透露着一丝诡异,似乎亲眼见到了我们刚碰的一鼻子灰。
在走廊上,万斯停下来点了根烟。
“现在,我们去跟可怜的帕帝先生聊聊,我不知道他能告诉我们些什么,但我很想跟他谈谈。”
帕帝不在家。他的日籍佣人告诉我们,他主人很可能正在曼哈顿西洋棋俱乐部那里。
“没关系,明天会有足够的时间,”离开那房子时,万斯对马克汉说,“我明早会跟巴斯迪医生联络,看看是否能安排跟杜瑞克夫人见见面,同时也顺带找帕帝谈谈。”
“希望——”希兹咕哝着说,“明天的收获会比今天多。”
“警官,你可能没发现,我们已经有一些重要发现了,”万斯回答说,“我们已经知道,每一个跟狄勒家有关系的人,都认识史普立克,也都知道他早上有到公园散步的习惯。我们也发现,今天早上八点钟,狄勒教授跟杜瑞克夫人一起在花园内散步。我们还发现,射箭室里一把点三二手枪不见了。虽然不能说是收获丰盈,但也不是空手而归,绝不是空手。”
在我们开车回来的路上,马克汉在一阵若有所思之后,望着万斯说:
“我有点害怕继续追查这件案子了,它让人觉得邪恶。一旦报社知道了约尼·史普立克的童谣,把两桩谋杀案联想起来,真不敢想象后果会怎样。”
“我想你是无计可施了,马克汉,”万斯叹了口气,说,“我是一点也不迷信——从来没遇过什么梦境成真,也不知道第六感究竟是什么感觉——但我总觉得,主教一定会让媒体知道那首《鹅妈妈》童谣。和‘公鸡罗宾’比起来,这次史普立克的故事是鲜为人知的,他一定会想办法让大家都能联想起来。这是他的弱点,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马克汉。”
“我会打个电话给崔南,”希兹说,“看看他们有没有得到什么信息。”
不过,希兹显然不用多此一举了。当我们到达地检处,《世界报》那位记者已经在那儿等候我们,史怀克正陪着他。
“你好吗,马克汉,”崔南的态度有些无礼,但也透露出紧张,“我有些问题想问希兹警官,总局的人告诉我,他正负责史普立克的案子,而且一直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就来了。”他伸进口袋,掏出一张纸条交给希兹,说:“我对你可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警官,希望你也给我些内幕……看看那张东西,是我们刚收到的。”
那是一张打字纸,用埃力特活字、淡蓝色带,打着《鹅妈妈》那首约尼·史普立克的童谣,左下角用大写字打着:主教。
“这是信封,警官。”崔南再度把手伸进口袋。
邮戳上的时间是上午九点钟。跟上一张纸条一样,寄自N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