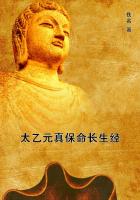虎啸军的新兵们吃过午饭,休息一个时辰后,在伍长的指挥下,开始练习站军姿。
烈日当头,汗如雨下。眼睛可以眨,但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是绝对不允许移动丝毫,擦汗更是一种奢侈的妄想。
一天三操三讲,杨烈至少参与一讲。从石敬瑭割地求荣,辽狗最凶残的一部分——“金狗”,南下河北肆意屠杀掳掠,烧杀*,一直讲到“澶渊之耻”。总之,汉人们一直过着屈辱的生活。
军官们轮番上阵演讲,不过,讲得最好的还是朱武。在他嘴里的金狗,简直禽兽不如,野蛮愚昧透顶。惹得一众官兵在班长的带领下,纷纷振臂高呼:“杀金狗。”
“蹲下。”随着班长一声令下,全班士兵整齐划一地蹲了下去,如同一头头卧虎。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在皮鞭、棍棒及思想动员之下,虎啸军士兵们熟练地掌握了队列要领。
“起立!”士兵们同时站起身子,“啪”脚跟只一碰,所有人几乎同时起身立正。
“向右看齐!”一阵细碎移动的脚步声,所有士兵的眼神都盯在最右侧的副班长身上。
牛皋一直静静地立在一侧,撇着嘴角欣赏着士兵们操练队列。这是他呕心沥血训练出来的一支铁军,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主公手里的一把锋利的钢刀才对。
牛皋仔细地看了一会,忽然走到队列前,大声下令道:“全体立正……向……右……半面……转!”
“哗。”又只一声,士兵们侧过了半边身子,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如果有人从队列右侧仔细纵向观察的话,一定会惊奇地发现,所有士兵的两只脚,竟然组成了两条绝不会交叉的平行线。
牛皋不禁有些得意,咧开大嘴巴,憨厚地笑了笑。这样一支军纪严明,训练有素的铁军,懦弱无能的宋军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收拾起心中的杂念,牛皋忽然大声命令道:“全体集合!”
“滴……”伴随着铜哨的长鸣声,几百个以伍为单位的小队列,在“一二一”的口令声中,纷纷向点将台前集中。
牛皋没有丝毫废话,大声命令:“从左至右,以班为顺序,依次到海边集合。”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向海边。
牛皋神色凛然地站在悬崖峭壁之上,冲着站在最前面的一班士兵,猛地挥下高高举起的右手:“跳!”
悬崖巍然耸立,高达三丈。从这么高跳下去,不死也得脱层皮,士兵们开始犹豫了。
牛皋二话不说,上前就是一脚,踹在一名士兵的屁股上,促不及防之下,第一个人掉了下去。紧接着军法官们有样学样,将立于第一排的士兵们统统踢下了海。
牛皋发现第二排上前的士兵们,个个面有惧色,有些家伙的身子已经开始发抖。
“奶奶的,一群胆小鬼。老子跳给你们!军法官都给我听好了,凡是不跟着我跳的,一律斩首!”牛皋起跑数步,纵身跃下了绝壁。
得,啥也别说了,总教官亲自带头跳了下去,死命令也下了,横竖是个死,跳下去还有可能活。不跳,就等着挨刀吧!
每组间隔大约几分钟,几个时辰内,所有的虎啸军官兵,连同军法官、护军使们一个不少,都跳下了海中。
尽管事先安排了周密的救援计划,悬崖四周大小船只齐备,但还是出现了超过十人的非战状态下的重大伤亡,其中大部分是溺水而亡。
紧紧地将伤亡报告攥在手里,杨烈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神色,几乎是从牙缝中迸出:“厚……厚恤……”然后别过头去。
牛皋分明发现主公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他默默地行了个军礼,然后悄然退到中军大帐口。
“伯远,”听见杨烈的吩咐,牛皋转过身子,立正站好。
“部队训练不能有丝毫松懈,今晚半夜把部队拉出去搞夜袭训练。”杨烈抬起头望想帐顶,语气之坚决丝毫不容怀疑。
熄灯号吹响,军营里顿时陷入了一片宁静之中。劳累一天的士兵们,倒头就睡,军帐里很快就传来了雷鸣般的酣声。
“噹噹噹……”好梦正香之时,忽然警锣声大作,和衣而卧的伍长们,第一时间就从梦中惊醒,顺手抓过枕边的武器,一跃下地。
睡在士兵帐内的军官们低沉地吆喝着,命令着,不时挥舞着手里的棍棒,拳打脚踢地驱赶着士兵们冲出帐外。
很短的时间内,虎啸军已经整齐地列队于操场之上。
牛皋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士兵们的手里全都拿着武器,弓手们也肩背长弓,腰挎箭囊。虽然没有睡好,一个个脸上都还带着疲倦之色,但精神头却十足。
牛皋也懒得废话,命令道:“全体向右转,跑步前进。”一马当先顶跑步冲出了军营。
杨烈负手立于路旁的小山头上,观察着他的子弟们演练也袭的章法。几百名近卫队官兵,刀出鞘,弓上弦,极为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的一切情况。一旦发现可疑迹象,就会象猛虎下山一般扑上去,将敌人撕成碎片。
嗯,不错,即使没点火把,官兵们的行军速度也并不比大白天慢多少。杨烈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一日四餐,餐餐有鱼有肉,荤素搭配。连值夜班士兵的宵夜也都好是肉丸面,官兵的营养不良问题终于获得了初步的解决。
杨烈始终记得当初带着龙威军展开夜袭的时候,因为没点火把,官兵们全都变成了睁眼瞎。根本不用提夜间发起攻击这回事,行军时掉进路边的夜沟里的士兵不计其数,因为惊慌失措,互相践踏受伤的也不在少数。
事后,找来当事的官兵仔细一问,杨烈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十二世纪初期这个年代,老百姓的营养普遍不良,有夜盲症状的人占了官兵里面的绝大多数。
从那以后,杨烈强制性的颁布了每日四餐的规定,而且必须餐餐见荤,否则军需官全部斩首示众。
杨烈满意地点点头,随口道:“此军可堪一战?”卫队长花荣挺胸收腹,猛吸了一口,朗声答道:“威武之师,无敌之师。”
“虎啸必胜,杀金狗……”顺利完成夜袭演练任务的虎啸军官兵们冲上了一座山头,大声欢呼起来。
吕颐浩仔细地观察着北港城的各个角落。宽大的街道上行人并不多,来来往往的多是运送物资的牛车队。大街两旁的房屋几乎都是两层小木楼,建筑形式完全一模一样。
吕颐浩觉察到,路上的行人衣着都还干净整洁,走路的步伐却比汴京快上许多。
即使是抗着锄头的老农,脚上也没有丝毫的泥土迹象。要知道,即使是首善之地的开封府,也不远远达不到此种程度。
吕颐浩观察到城内的商业情况并不算良好,大小店铺的生意明显不好,门前冷落,车马稀。
有趣的是,沿途众多的酒楼里面已经人满为患。吕颐浩的脚步停在一处酒楼门前,招牌上尽是两浙路风行一时的菜肴。略微一想,他马上明白过来,敢情恩师在两浙路运走的那些灾民,都送到流求来了。
拱手谢过店小二的殷勤招呼,刚走出数丈,吕颐浩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十分独特的情况,北港竟然没有一家米铺。
“没有米商大家吃什么?”吕颐浩带着疑问,步入了一家杂货店。店面长约四丈,宽二丈,货架上东西不多,甚至连最常见的农具都没有。
吕颐浩拱手道:“这位老丈,请问可有斗笠?”
店主见吕颐浩举止文雅,谈吐不凡,后面还跟了一大群书生,心知来了位贵客。赶紧一揖,笑道:“客官有所不知,鄙城所有的农具都由官府赠送,不须花钱另购,所以鄙店不敢做那亏本的买卖。”
“这是哪家的官府?居然给农民免费送农具?”吕颐浩的好奇心马上被勾了起来。
吕颐浩故意逗店主说话,客气地说:“老丈经营的货品不多,收入一定不太好吧……”
店主闻言马上笑了,问道:“贵客可是刚来鄙城?”吕颐浩点头称是。
店主笑眯眯地说:“那就难怪了。贵客有所不知,小老儿经营此店不过是打发时日罢了,并不以之为生。老朽劳碌了一辈子,闲着也闲是,不如给自己找点事做。”
吕颐浩越发不解,惊讶地问道:“那老丈以何为生?”
店主突然面向北方,深深一揖,然后转身冲吕颐浩拱手道:“拜主公他老人家的厚赐,小老儿一家六口,共分得一百二十亩荒地,三头耕牛,一石种子。不仅如此,官府每月还按时发放口粮二石。二个儿子参与修城每月可得二贯钱。老婆子和闺女替官府做针线活,每月也可得钱三贯……”
吕颐浩震惊异常,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官府,这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不禁讶异地问道:“请问老丈,这每年的税赋可重?”
店主反问道:“贵客以为该有多少税赋?”吕颐浩按照大宋国的经验,竖起一指,笑道:“怎么着也得十税抽一吧?”
店主哈哈一笑,竖起两指,眉飞色舞地说:“二十税一,而且五年内不须缴纳一文税金。我说贵客,您见过这样的官府么?老朽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这还是头一遭呢。”
“官府的公人靠什么为生?”吕颐浩不死心地追问道。他从没见过这种分田地,不征税,不摊徭役,做事发工钱,还免费发粮食的官府。
店主指了指海上,感慨道:“我家主公靠着海上贸易发家,当年若不是他老人家千里奔赴两浙赈灾,小老儿全家早已经饿死了。”
听到这里,吕颐浩马上想起一件举世皆知的大善举,急切地问道:“这主公可是姓杨?”
那位店主听吕颐浩提及主公的名讳,慌忙转身,冲着八仙桌上的一块生主牌,跪了下去,重重地叩了三个响头。然后站起身子,大声回答吕颐浩的问题:“我家主公正是姓杨!”言语间十分自豪,饱含着崇敬之情。
吕颐浩暗暗叹息一声,微笑着问店主:“主公可是名烈?”明明已经猜中了,但他还是忍不住要确认一下,心下既有些期待,又揣着莫大的恐惧,真有些难以自处。
可是,店主却摇了摇头,纠正道:“我家主公的名讳乃是平夷二字。”说罢,再次冲着生主牌行礼如仪。
吕颐浩看得很清楚,那店主的脸上满是虔诚之色,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尊崇。
吕颐浩既有些失望,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感觉心下轻松了许多。
朱武一直静静地立在吕颐浩的身旁,对于他的神态变化,完全了然于胸。
当初,朱武也对杨烈刻意要隐瞒自己的名讳,感到十分不解。后来,发现流求开始建军时,这才恍然大悟。计划造反的人如果不隐姓埋名,莫非傻傻地让朝廷灭其九族不成?
吕颐浩步出杂货店,身后却传来学子们的议论声:“我觉得这里大有可为,难怪恩师大人让我们来呢。”
“这里毕竟是化外之地,咱们不可久留……”
“我看啊,这里简直是理想中的国度,前途似锦……”
吕颐浩不由得暗暗苦笑,心情不禁越发沉重起来,究竟该怎么办,他亦迷惑不解。
吕颐浩犹豫了很久,冷不丁地说:“广达,咱们到书院去看看。”朱武促不及防,脚下一崴,差点跌倒在地上。
朱武千算万算,啥都算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书院上面去。也难怪,他也没有读过几天书,对于传道授业解惑这档子事并不熟悉,所以让吕颐浩抓住了一个大把柄。
吕颐浩眼疾手快,一把扶住朱武,安慰道:“广达兄,小心能驶万年船啊。这里跌到了还可能爬起来,若是在悬崖绝壁上面,那可就要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朱武自然听得懂吕颐浩的潜台词,他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笑道:“大路太滑了,很不好走。若是那田间的小路,有时候反而好走些,都怪我太不小心了。”
吕颐浩见此人颇有些急智,脸色也和缓了许多,笑道:“就怕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广达兄务必慎之。”
朱武就算是天神,这么短的时间内,也无法变出一座书院来,他只得转移话题:“大家一路舟车劳顿,实在是辛苦。在下先带诸位去下榻的地方,休息一下。晚上,在聚宾楼替各位接风洗尘。”
众人从开封出发,走走停停已经一月有余,身心俱疲,于是纷纷颔首道谢。
吕颐浩因着杨烈的关系,也不太好当众让朱武下不来台面,于是一行人转过街道,朝住处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