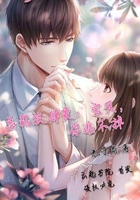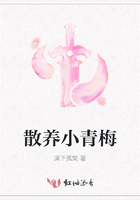四处灭火
1864年的下半年,民间传说,从长江至湘江,再从湘江至涟水,这条水路上,络绎不绝的民船,运载着湘军的私金财物,以及美女。
这年10月,随曾国荃一同回乡,先批裁减的两万多人,连同被这些将士抢夺的女人,浩浩荡荡,十里联帜,帆船相接,前往湖南。
多半往湘乡。
沿途两岸,无数人看热闹,都议论纷纷,说金银财宝如何多,女人如何漂亮。
特别是湘乡,成了这笔财富的最大占有者。
打开天京发洋财,是当时湘乡流传的一句俗语。那些湘军将领,回家之后忙着建豪宅,买田土;那些下层官兵,也或多或少捞了一点,他们不事生意,肆意挥霍,很快手头空空。特别是他们因战功而得到的空头支票,比如赏的什么千总、总兵、镇使等等顶子,因为得赏的人太多,几乎就是一个空名,堂堂四品、五品,原来干什么,回去还是干什么,至于六品七品就更没人管了。
这支庞大的队伍回到湖南,成了另一个火药桶,史称“会党”。
他们结成哥老会,酝酿起事。
他们流落和聚散在码头这些交通枢纽,慢慢发展成不同的帮派,不过,内部之间,非常看重加入湘军的时间先后。下面是他们的接头暗号:
一人问:碗米条条担担花,大哥什么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可谓五花八门:香香花(证明在湘乡弄团练他就入了伍)、沙棠花(长沙入伍)、周杏花(在衡州入伍)、周岳花(岳州入伍)、昌武花(攻打武昌时入伍)、安吉花、庆安花、银金花……
中下层官兵组成了各式各样的会党。一场生死之战,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他们打砸抢杀惯了,头脑早就挂在腰带上,于是,会党借机生事,强抢明要,或者干脆呼啸山林。
一封封密报,飞往曾国藩的案头。其中有湘乡县令密报的,有在家休养的阿弟曾国荃报告的,有一直在家主持家政的大弟曾国潢报告的。
曾国藩头皮都麻了。
朝廷开了这么多空头支票兑不了现,曾家成了最大的冤大头。曾国荃在家建起的豪宅大夫第那么光鲜,那么气派,以及大大小小将军的豪宅,成了刺激会党的靶子。但若是用镇压的手段,则事情就会越闹越大,说不定第二支洪秀全队伍,就会在湘乡冒出来。
曾国藩密令湘乡县令,以及在家的两个老弟,对于会党采取一条原则和十二字方针。一条原则就是:不上升到“造反”这个高度,免得朝廷借口他遣散不力,以此治他的罪。十二字方针就是:极力安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身在南京,他只能用书信来指导在家主政的曾国潢如何处理这些棘手的事。
曾国潢领会了阿兄的意旨,凡是哥老会头领被抓,他就当灭火队长,前往长沙、湘乡营救。所有的起事,他总说成纠纷,绝不会说他们想起义。
但这种事总是十天一小闹,一月一大闹。此起彼伏,让曾国藩夜不能寐。
一面是跟随他征战十多年的湘乡兄弟,他们用血汗换来的是曾家与大小将领的顶子名誉,若是杀戮或者打入大牢,一则他于心不忍,二则会激起更大的事变。一面是对他疑心重重的朝廷,只怕没有把柄,一有把柄就要打压和治罪他,还有曾家荷叶的大院、祖坟、家产,只要起事,就会被会党荡平无疑。
闹事日甚一日,连曾国潢也不耐烦了,写信来,不如抓几个杀头示众,以儆效尤。曾国藩收到此信,大惊失色,严令阿弟:万万不可,只能极力安抚。他甚至强令在家的两位兄弟割肉,吐一些出来。大家应该联络湘中有影响的人物,出资修桥修路,大办学堂,设立义仓,捐赠义谷,拯济贫苦,安宁地方。
一面在南京办公,一面时时关注老家动态,曾国藩没睡几个好觉,给弟弟的信中说:常常夜半惊醒,几难成眠。
会党难以扑灭,后来成为了一支庞大的力量,六十多年后爆发的那次革命,会党成了一支中坚力量,这是后话。
剿捻无功
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失败了,但捻军在北方却日益壮大。这年10月,朝廷令曾国藩北上督兵剿捻。
他推辞了,不是他惧怕艰难,而是他觉得自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一介文弱书生,十年征战,精血耗尽,身体还患奇痒症怪病。
痒病,这病看起来不是什么致命的重症,但是,它有两个特点:一是难治好;二是耗精神。通夜难眠,长此以往,比生一场大病还损精血。
曾国藩的痒病严重到了连说话也“舌蹇”的地步。
此外,还有若干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湘军撤了,要指挥的是一支非嫡系部队。僧格林沁、官文,再加上自己,三个钦差大臣共同指挥一支军队,难于协调。(特别是僧格林沁,历来看不起汉人,也不是一个读书人,难于共事。)
朝廷觉得曾国藩说得在理,于是,应允了他的要求。
可刚过了几个月,僧格林沁大败,全军覆灭。
清廷不得不再次调任曾国藩。
慈禧觉得曾国藩的湘军已基本撤散,才稍稍安心一点,但曾国藩的人望威信还在,必须借他来剿灭捻军。
这时,清廷不仅调曾国藩出山,也数次调曾国荃出来效力。
曾国荃确实身体不好,对朝廷也是一肚子意见,所以,他屡屡以身体正在调养为由,偏不赴任。
当初攻下南京,我说身体不好,你朝廷虚情假意挽留了一次,第二回就准予奏请,这回有难了,就数次催促,我九爷不是你的叭儿狗,你丢块骨头我就来咬。
1866年,捻军锋镝直指湖北,武昌危矣。慈禧顾不得你曾国荃托病了。严令曾国荃速赴武昌,任湖北巡抚。
曾国荃终于来上任了。他城府太浅,做事直来直去,与胞兄形成鲜明对比。刚上任,他就与总督官文闹僵了。官文是满人,没什么本事,是个混蛋、王八,你还再怎么形容都不冤枉这位老兄,但人家出身好,皇二代,一直以来,就是朝廷派在南方监视湘军集团的暗哨。连曾国藩都要迁就联络的对象,你曾国荃,他当然没放在眼里。
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不把你当人看。于是,曾国荃做事,官文处处掣肘,处处排挤,曾国荃也偏偏你官文说东,他就偏说西。
官文决定把曾国荃调到剿捻前线去,当然,也不忘恶心一下他。于是,他向朝廷保奏曾国荃去剿捻,要朝廷授予曾国荃“帮办军务”一职。
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所谓“帮办军务”是个虚职,就是个调研员的味道。一个攻打天京的主将,去当个军队调研员,不明摆着调戏曾国荃吗?
朝廷竟然批了。
朝廷能够戏弄一下汉人的时候就戏弄一下。
曾国荃弄不清这官衔是个什么意思,于是,写信给大哥曾国藩请教,应不应该向朝廷回个谢折。曾国藩告诉胞弟,不必专门回折感谢朝廷,因为,太平天国投降过来的将领,朝廷不放心,也是封这样的官衔。
曾国荃弄清是这么回事后,怒火中烧。
这让一个人看到了机会,这人姓丁,早就对官文恨死了,于是,他提供了官文索贿的证据。铁证在手,这时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正好来湖北叔父这儿玩耍,于是,由曾纪泽捉刀,曾国荃密折弹劾官文。
他列了七条官文罪状:贪庸骄蹇、贻误军情、欺罔徇私、滥支军饷、宠任家丁、冒保私人、结党营私。
以上七条,随便哪一条都可以治罪,削职弃军一枪毙了,可轻可重,这就看朝廷的态度了。
曾国荃是老大粗,曾纪泽没从政经验,奏折事先又没寄给曾国藩把关,这下就闯大祸了。
好在曾国藩耳目众多,京城马上就有人给他传话,说曾国荃已向朝廷弹劾官文。
曾国藩急出一身大汗,立即派快马急驰湖北,向曾国荃要来密折底稿。
看过底稿之后,曾国藩摇头不已,连说:胡扯,胡扯!
慈禧收到密折,召军机处各员商议如何处置。
折子虽然大部分事实证据齐全,确实值得纪委查一查,不过,这是一篇非常蹩脚的折子。
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叔侄俩,把当政的军机处部分人都扯进去了,这就是最后一条“结党营私”,说官文不仅与肃顺勾结,还与军机处大员暗中拉帮结派。
捏了半个七寸,因为慈禧只要别人与肃顺有牵扯,一定除之而后快。另半个七寸捏错了,说官文与军机处大员暗中勾结,这就引起了军机处集体反弹,说曾国荃血口喷人,造谣诬告,应严加处罚。
慈禧说:先不下结论,着军机处派人调查清楚。
于是,派了一满一汉两名大员赴湖北办案。
事实很快就查清,官文确有贪污索贿实据。
慈禧说:开缺官文的湖广总督缺,让他回京。
按常理,官文这种人枪毙一万次都够格。但他是爱新觉罗氏自家人,明眼人都知道慈禧此举不过是奶奶打孙子,扬起巴掌做做样子。
曾国藩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一篇力保官文的奏折早就飞向了京城。为官文说尽好话。
慈禧有了台阶,就驴下坡,让官文回京之后,又以大学士身份掌管刑部。这根本不算什么处分。
得此消息,曾国藩私下给家人写信时感叹:“公道全泯,亦殊可惧!”
慈禧很精明,她知道湘军虽已撤散,但曾氏兄弟统率着剿捻各部,李鸿章、左宗棠各部的骨干仍然是湘军旧部。曾氏像一条斩断的蚂蟥,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必须再度打压!
她在等待时机。如果时机不成熟,反令剿捻大局陷入被动。
曾国藩从来没有相信过慈禧可以成为朋友。
他唯有卖力,让慈禧认为他是一个忠臣。
捻军给曾国藩出了一个难题。这支铁骑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他们只攻城掠地,不占山为王,日行千里的马队让曾国藩的部队成了一只气喘吁吁的赴山狗。
曾国藩终于醒悟过来,挖壕,让马队成为困马。到处挖壕,各寨各垒,深沟大壕。
按这个办法,捻军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一支困师。
曾国藩相信,剿灭捻军指日可待。他没来得及高兴,这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京城御史弹劾他剿捻不力:督师日久,诸量加谴责。
一个御史敢弹劾如日中天的重臣,毫无疑问,后面一定有主使。
这个主使就是官文。
慈禧觉得时机终于来了。军机处那些生怕曾国藩功高盖主危及他们地位的大臣们,也立马抓到一根救命草似的,上朝时趁机攻击曾国藩,说他“办理不善”,也有人说他“骄妄”。甚至说“大局糜烂至此,不知该督何颜以对朝廷”。
面对正在对捻军收网、指日可以见效的曾国藩,军机处掀起了一场围攻。
也并非军机处的所有大员都是糊涂虫,老实说,他们是领悟了慈禧的意图。于是,部分军机发难,剩下的人,不得不同流合污,基本同意了弹劾曾国藩。
会后,圣旨下达:着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即刻接手剿捻。
曾国藩又羞又恼,干脆提出:两江总督我也不当了,我到营中以散员效力。
散员就是调研调研,参谋参谋,帮办帮办的意思。给学生李鸿章当个参谋。把皮球踢给朝廷。这让朝廷为难了,在李鸿章面前,你既是他的老师,你的官阶、资历、声望,都比李鸿章强,怎么能当“散员”呢?
朝廷说:你还是当两江总督。军草粮饷非常重要,这全靠你供应,李鸿章有什么事,要他多咨询你,向你报告吧。
曾国藩一度想退休,但他考虑那也不是个办法。在给他弟弟的信中,他说:回老家住,若是与地方官吏稍有隔阂,则步步都成荆棘,若是住到北京养病,很容易招惹怨谤。
退休不成,就只好再任两江总督。
然而,令曾国藩更为可惧的还在后面。1866年12月,清廷让曾国藩交出军权后,还不放心湘军集团,朝廷找了几个理由来打压,至于理由成不成立,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三个字——莫须有。不久之后,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等一批湘军官员被全部开缺回籍。
面对这一沉重打击,曾国藩十分惊惧。一方面,剿捻无功,已为清廷留下把柄,另一方面,曾国荃惹下祸端,为满朝权贵打击湘军势力提供了机会。更为担心的是,他怀疑清政府决定藏弓烹狗了。
手中再无一支可以与朝廷叫板的湘军,一介书生,他知道,此时的慈禧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深谙政治不过一场反复无常的游戏,于是,他作了最后的,也就是最坏的打算——负荆请罪。于是,他多次上奏朝廷,请开缺各职,入都陛见,自请办捻不善之罪。
收到奏折,慈禧笑了。
慈禧阴冷地笑过之后,拿御史开刀了。她一一驳回了御史的参劾,称曾国藩素来忠贞体国,是非常难得的,弹劾内容均是夸大其词。下令军机处加授曾国藩大学士衔、加赏一云骑尉世职。
面对慈禧的又打又拉,曾国藩对这个朝廷仍然没有失望。
他幻想着这个朝廷,不,是这个国家能振兴起来。青年时代,就怀着辅佐帝业的梦想,回到南京,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同样怀着救国梦的知识分子身上。
这就是他晚年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不遗余力地推动“师夷长技以制夷”。
咸丰十一年,他缔造了安庆军械所。上书朝廷造外洋船炮。与李鸿章、丁日昌倡议筹办江南制造局,设立同文馆。他的总督府内,过去是军事人才多,现在是科技人才多,据容闳记载:“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学、天文、机械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
他还提出在江南制造局设立学馆,“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于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书。”
同治十年,他干脆与李鸿章联名上折,选派留学生出国。
这件事,是容闳提出来的,由丁日昌向曾国藩建议。
在一个自大与固步自封的气氛中,唯有曾国藩来提这个事,才会减少阻力,引起朝廷的重视。
魏源提了多少年?朝廷几乎没有半点举动。
终于,又一艘轮船制造出来了,汽炉、船壳全系国产,曾国藩亲自登上这艘取名“恬吉”号的轮船,在吴淞口外试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