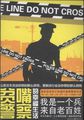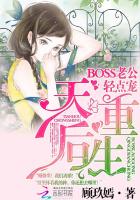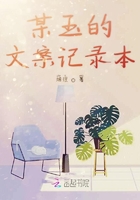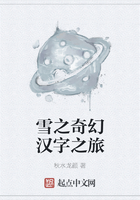双峰境内,有测水、涟水两条河交汇,所以叫两派交流,在这风云激荡的岁月,这儿是一股活水,养育出这么多的人物。双峰对峙,这种奇特的现象,哪儿去找?这么多侯伯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大大小小的人物,哪个县有这么多呢?所以,应该是“高山仰止”了。
朱尧阶为双峰书院题的对联,其口气之大与岳麓书院的两副对联有得一比。
其中一副是: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口气不可谓不大。口气更大的一一副在正门:
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朱尧阶笔落惊风雨,联成泣鬼神,一时成为佳话。
这对联一出,中里全体兴奋、自豪。此后这地方,出过很多人物,如蔡和森、蔡畅兄妹。娶的几个媳妇也赫赫有名,比如王廷钧之妻秋瑾、蔡和森之妻向警予等等。
总之,耕读天下,成了这地方普遍的民间风尚。
这是湘军意外的收获?
硬挺
天京攻克,湘军集体狂欢。
曾国藩是六天之后,才得到天京内城已全部占领这个消息。于是,他从安庆坐船前往金陵。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早晨到达棉花堤,又走了二十里,才到达曾国荃的营中。
这一天,来拜访他的客人非常多。
吃了晚饭后,曾国藩与曾国荃两兄弟就密谈到“初更”。谈了些什么,外人无从得知。
此后,他便一连几天,到驻扎在南京城的各营看望将领们。
握手,慰问,说大家辛苦了,个个“慰勉有加”。然后,在曾国荃的陪同下,到天王府、忠王府、英王府各处看看。在将领的陪同下,查看了攻城挖的地道。
曾国藩还特地慰问了快要死了的李臣典。
接着,曾国藩提审了李秀成。史记:曾在灯下注视良久,问:汝即李秀成耶?汝亦好汉,可惜,可惜!连叹数声。
一月之内,就是各将领请客。今天这个请,明天那个请,边吃边看戏。
因为曾国藩规定,行军打仗,不准戏子随行。所以好久没看过戏的湘军将领,就请来戏班,大过其瘾。
一时,歌台舞榭,歌声袅绕。
曾国藩忙得不亦乐乎。他要向朝廷汇报所有的工作,所以,实地查看,了解攻城情形,又要对李秀成的自供状把关,还要对洪秀全验尸。这些都疏漏不得。
洪秀全是湘军中一个叫熊登武的负责挖出来的,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扛来一验,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包裹。”
快验完了,突然天刮大风,大雨倾盆。
雨停,找来一宫女辨认。这个宫女黄氏,是湖南道县人,亲自参加了埋葬洪秀全的工作。她看过之后,确认无误。
然后焚尸!
这些日子,曾国藩共与曾国荃密谈了数次。所有的内容,外人都不知道。
可以推断:他们在谈如何处理与朝廷的关系,如何撤军。
日记中隐约有些表现,比如:弟焦愤。比如:与弟谈行藏机宜。比如:他记载几乎天天晚上“不甚成寐”。睡得迟,睡不好。有天晚上,因为审问了李秀成,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夜间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二更睡,四更,梦魇殊甚。”
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这梦到底是什么?外人不得而知。
总之,对于骤然而至的胜利,曾国藩表面上,几乎每天还与人下围棋,赴各处宴席应酬,看戏,会客,内心则波澜壮阔。特别到了晚上,他就不得不通盘筹划。
他必须有特别的智慧,才能面对即将来临的风雨。
硝烟散尽,原来模糊中的面目渐渐清晰。
无数史家已写尽了曾国藩与朝廷的争斗。
大约不外乎如下三个问题。
比如,金陵财富被湘军抢劫一空。曾国藩奏报“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
幼天王逸出城外,曾国藩奏称“据称已积薪自焚”。
朝廷要求把李秀成解往北京,曾国藩以路途遥远,怕生变故为由,把李秀成一刀剁了。
这三件事交织在一起,引起朝野议论纷纷。
旧的对手去了,新的对手来了。
各种利益集团进行了重组,开始了新一轮较量。
这些人可以分成三派。
曾氏湘军集团一派,主要代表:曾国藩。由于采取的态度比较硬,叫“挺派”。
爱新觉罗氏集团一派,主要代表:军机处,由于采取的态度以防为主,叫“防派”。
帮闲派,主要代表:左宗棠、沈葆桢,由于采取的态度以攻为主,叫“攻派”。
攻下天京,曾国藩不得不面对现实。第一,天京财富被掠夺一空。湘军的腰包鼓鼓胀胀,这需要向朝野作一个交代。由于物议纷纷,没有政治经验的曾国荃,竟然提出要湘军将士每人交一些上来,再上缴国库。曾国荃的办法,看起来很美,其实不中用。你要人家上缴,本来就是割人家身上的肉,再一个,平均交一个数,弄得多的不在乎,弄得少的,岂不是要他的命?好不容易才挖得一点后半生的养老钱,你要他交出来,结果只有一个:激起兵变。
曾国藩否决了胞弟的想法。
他使出了第一招:挺。硬挺,不顾一切物议,挺到底。
天京没什么财富,连我也想不清楚,但是,确实没有!
第二,他奏报攻克天京,几乎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洪秀全服毒自杀,幼王据说“积薪自焚”,李秀成捉拿归案。这个奏报,至少三分之二完全是事实,只是幼王生死,他虚晃一枪。为什么这么上奏,为的是让广大湘军将士得到尽可能多、尽可能快的奖赏。
这时,帮闲的出来了。左宗棠因为得到幼王逃出金陵的消息,立即向朝廷告曾国藩的状。一是欺君,二是隐患特别大,幼王可招集剩下的太平军,形成新的祸患。建议朝廷参办失误的将军。
此事曾国藩确实有错,至少奏报不严密。
面对错误,曾国藩使出第二招:类比。
他反举了左宗棠克复杭州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这次逃出几百人,应暂缓参办。
然后又对朝廷说:天京战事那么紧张,漏出几股匪是正常的,如果要参办的话,对将领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谁能保证万无一失?
第三件事,把李秀成就地正法,是不得已的举措。因为几个要害之处,如果李秀成嘴巴不稳,就会走火,首先,洪秀全是病死的,与奏报“服毒”不符,这是欺君;其次天京有财富,与奏报“全无货财”不符,更是欺君。再次,如果李秀成聪明一点,诬陷曾国藩有反心,曾想暗中联络他收拾天国旧部,打出一个汉人江山,则李秀成在战场上做不到的事,可假清政府之手做到。
朝廷当然想要曾国藩将李秀成押解进京。
但曾国藩再使出一招:恐吓!
他说李这个人嘛,投降了,他的旧部见到他,仍然马上跪下,现在路途遥远,万一生变,在路上出了问题,那可不得了。
上述三件事,尽管方法各一,总的方针是一个字:挺。
先斩后奏也好,闻风而奏也好,睁着眼睛说瞎话也好,我就这样硬挺。
再来看朝廷,整体上还算防守派。一是关于天京财富,这个问题他们倒是不太计较。因为,一块心病终于解除了,不在乎那点金银。其次是关于幼王出逃,借这个事,采取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无非是扬左抑曾,抬一抬左宗棠。
除了防守之外,朝廷开始敲山震虎。
一是派出大军立即到了江北一带布防,以防曾国藩起事。第二,语带威胁,假惺惺地表扬了曾国藩几句,说他“素来精忠体国”,但语气一转,又说:自曾国荃以下,希望曾国藩严加管束,才可长承圣恩。
言下之意,你若有异心,或者工作失误,那么,就是曾国荃,朝廷也不会宽恕。
第一回合的较量,到此结束。
通过第一轮较量,曾国藩比较满意。至少他说了的,朝廷都依了他,给足了面子。所以,他决定以退为守。
以退为守也是迫不得已。一是他胞弟太招惹朝野忌讳。所以,他劝说老弟激流勇退,暂避风浪。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辛苦,劝、教、哄,总算摆平。二是撤军。他明白,湘军打疲了,捞足了,这批人已失去斗志,只能解散。
只是如何解散的问题。先撤谁,后撤谁。
在这个问题上,朝廷与他的观点是一致的。朝廷跟他细商量。这些人都是当兵为生的,突然让他走,就可能激起兵变。所以朝廷说:以前在四川湖北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因为没有处理好,让一些人“啸聚作乱”。所以,不如先淘汰一些老弱病残,把那些精壮的士兵派到江西湖北等地,等那些地方的匪患全部肃清后,再慢慢裁减,或者把一些士兵补充到其他军营中去,免得节外生枝。
在撤军问题上,双方达成了一致。
天京攻克之后,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
各人有各人的难处。
朝廷不敢对曾国藩以及湘军下手,因为,湘军没有解散之前,仍然对朝廷是一种威胁。除此之外,太平军还有余部没有剿尽,捻军仍然在中原驰骋。善后工作,仍然得借曾国藩之手来完成。
曾国藩只有让胞弟退隐,撤减湘军,才能在“金陵无财富、放走幼天王、擅杀李秀成”三件事上,求得朝廷的原谅,平息朝野的议论。
他们在互相威胁中暗自较劲,他们在互相妥协中保持颜面,他们在互相对峙中各退一步。
各种野史,都不忘演绎有人劝曾国藩当皇帝的故事。大约不外乎下面几种版本:
一是王闿运。王一生致力于纵横学,以辅助别人称帝为职业,早年在肃顺府中,就有想辅助肃顺称帝之说。据说曾听王滔滔不绝,劝说他称帝时,他只是不断地用手指醮茶水在桌上写字,然后借机起身,王走近一看,是“荒唐”二字。
一是彭玉麟。彭写了张字条给曾国藩:江南半壁无主,吾师可有意乎?曾国藩看完,把纸条吞了,说:雪琴也以此试我?
意即我忠心耿耿,你用不着来试探我。
还有一种说法。有一天,全体将官突然涌到曾国藩帐外,要求见曾国藩。曾国藩问亲兵:九帅来否。亲兵说:没有。曾国藩说:把九帅找来,我才见他们。曾国荃来了,曾国藩才出来见大家。他见所有将官肃立不语,一言不发,就提笔写了“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然后,笔一丢,走了。众将近前一看,知道劝进没戏,互相唏嘘。
种种传说,莫衷一是。
那么,曾国藩真的不想做皇帝,还是他觉得做皇帝没把握而拒绝呢?
逼急了,他会做!
如果清廷一定要在“天京财富、幼王出逃、擅杀李秀成”这些事情上大做文章,甚至逼着他处理大批湘军将领,甚至处理曾国荃,那么,即使是他不想做皇帝,湘军将领也会逼着他做皇帝。
胜负是另一回事,到时举起“兴复汉族”的旗帜,就不要任何理由了。
如果没有逼急他,他根本就不想做皇帝。
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已五十三岁,此时,就道德文章立功立言来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圣人了。只要坚持下去,这圣人的名字,就会定格于青史。
但就其内心来说,他真的不想做皇帝。
生于末世的曾国藩,本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他科举晋升的愿景,原本是做一个光宗耀祖的人。
腐朽的帝国,腐败的官场,让他慢慢地修改和校正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希望以自己的力量,来慢慢修正帝国的航向,修复这艘漏船。后来,不止是对于帝国,更多的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希望这个国家强盛,能摆脱列强的欺凌,做一个自强自立的民族。
比如,设立江南制造局,办同文馆,遣派留学生,他希望的是早点结束战争,让国家回到正常的秩序中来,徐徐图强。
与他有同样心情的,普天之下大有人在。比如彭玉麟,他不仅痛恨作乱的太平天国,同时也痛恨这个腐败的官场体系。他希望以自己的廉洁清正来唤醒世人,又嫉恶如仇,执法如山。所以功成名就之后,他次次辞官不做。他没田没房没积蓄,过着甘于清贫的生活。
比如郭嵩焘,大力宣传西方文明,提倡修铁路、架电线、设邮局等。
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亮光。
他们是镇压天国的受益者,因战功而成为朝廷大员,同时,也是改造这个世界的呐喊者、行动者。
但是,这些,都只是这帮有责任的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
腐败的清廷,在列强的欺凌中苟且偷安,甚至不惜“以吾国之财力,结与国之欢心”。他们所谓的国家,与曾国藩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等人心中的国家是两回事。他们想着的就是皇室的命运,一小撮人的命运。只要他们活得好,国家与人民,只不过是他们好好行乐的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