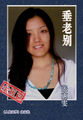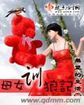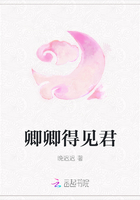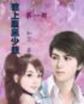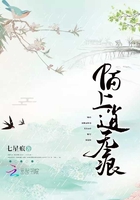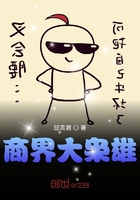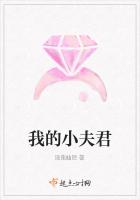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徽州驻军原来并不属于湘军统率。加上主帅张芾已走,群龙无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李元度亲自驻扎城外,兵力少了,可从城里抽调。这样,才可弹压得住。
等他刚进城不久,太平军就攻上来了。
城外的那一万多人,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来统率,顷刻之间,竟作鸟兽散。
李元度得到消息,他竟然冲动起来,率部迎敌。
他非骁将,兵力也只有三千多人。结果可想而知。
队伍打散,李元度一度没有下落。
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长叹一声。历史上有诸葛亮用错马谡的教训。可教训归教训,朝朝代代总是有人这样感情用事。
祁门立即成为危境!
兵事变幻无穷,曾国藩也没想到李秀成会来攻徽州,而徽州又败得如此又快又惨,事至如此,他也毫无办法。手中几乎没有什么可用之兵,援兵一时难到。于是,祁门深山老林之中的总部,就只剩下他一人加一群幕僚,再加上一个亲兵营。
那些亲兵营,自然只能与主帅同生死共命运。而那群幕僚就惊慌失措了。
也难怪,他们都是文人。归顺到曾氏帐下,就是想着这是最安全的地方,既可获得功名,又无生命之虞。想不到最安全的地方成了最危险的境地。
大难来时各自飞。幕僚们前来一个个告辞。
曾国藩在家信中曾告诉家人,军中乃凶险之地,很多人不愿意来帮忙。以他的洞察,这些人要走,那是必然的。
所以,凡是告辞的,他一概很客气,除了打发路费之外,都亲自送一程。说,以后你有空,就再来啊,现在你有事,我也不留你。
曾国藩一切照常,清早即起,用早餐,批阅公文,午饭后与幕僚下几盘围棋。仍然谈笑风生。该严的严,该宽的宽。
曾国藩吃饭都是和幕僚一起吃,尤其是早餐,他总是开得非常早,大约六点半就用餐。一天早晨,其他人都到了,唯独李鸿章没来。曾国藩令亲兵去催,李鸿章说身体不舒服,曾国藩对亲兵说:再去催,告诉他,他不来就不开餐。
李鸿章悻悻而来,曾国藩也不吱声,带头就吃,平时饭间谈笑风生,这顿却吃得沉闷。吃到中途,曾国藩正色道:少荃,我这儿有我这儿的规矩,既来就必须遵守。
言毕起身,众人默然。
后来,李鸿章果然找了一个借口走了。
事情缘于李元度。李元度惨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竟然逃了回来。曾国藩非常气愤。你要么战死,败了,你还有脸面回祁门?李元度仗着与曾国藩私交好,找了一堆客观原因。
他有一层更深的意思,不太好说出来:在江西那样艰苦的岁月,我去带兵了。你那些幕僚呢,一遇危险就纷纷走了。我虽然守城有误,你也不应该如此对待我。谁不犯错误,改正了就是嘛。
曾国藩不这样想。打仗可以败,但不能逃。自己打败仗都向皇上请罪,并且准备以身殉国,两次投水。你打败了,还有道理?
请李鸿章起草一个折子,治李元度的罪。
李鸿章不干。曾国藩说非治罪不可。
李鸿章说:你想治,你去治,反正我不写,我走。
这到底是真的不想写,还是一个溜走的借口呢?
这似乎是一桩历史悬案。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大家没想到。
当李鸿章来告辞时,曾国藩坐在椅子里,没起身,只对身边的人说:请去粮台取三个月薪水给少荃。
当然,也有没走的。比如李榕、程恒生等人。这些人对以后大富大贵、言必称自己是曾国藩第一门生的李鸿章,内心看不起。李榕甚至写了一首诗,讽刺李鸿章。
在此危急时刻,曾国藩再次写好遗嘱,并准备了一把短刀。他随时准备杀身成仁。
险恶时刻,李秀成部距祁门的曾国藩总部仅仅二三十公里。
李秀成完全可以活擒曾国藩。但他没有。不是他不想,是他真的不知道曾国藩就在他的鼻子底下。
或者说,李秀成对祁门没有任何兴趣。他有自己的打算!
李秀成有什么打算呢?
一切还得从几年前的那场内讧说起。
天国内讧后,洪秀全好像从梦中惊醒,他决心干点事,振兴天国气象。比如杨秀清的弟弟杨辅清,韦昌辉的弟弟韦俊,他一概不搞株连政策,继续信任他们。大量培养和放手使用天国后起之秀,如陈玉成、李秀成等人。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有些害怕了。
也不是有什么迹象让他害怕。而是内讧那一幕时不时刺激他,让他疑心重重。于是,他采取了另一个自以为保险的办法,把他的洪氏兄弟们一个个提拔重用。
于是,天国俨然“家天下”。
洪秀全多少感到有些放心了。
可是,洪秀全放心了,别人害怕了。其中一位就是李秀成。李秀成的害怕又得从一位叫李昭寿的人说起。
李昭寿,河南固始人,出生在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区,从小便是个典型的不良少年,偷盗诈骗无恶不作,家乡附近所有的大牢他几乎都蹲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李昭寿身材逐渐魁梧起来,性格变得更加凶狠阴险,他已不满足于偷偷摸摸,开始混迹江湖。
1853年,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大清风雨飘摇。此时已在淮河岸边小有名气的盐枭头子李昭寿和同乡薛之元按捺不住心中躁动,参加捻军,起兵造反。队伍逐渐壮大,可是多是乌合之众,1854年,他率领七千多人与清军道员何桂珍六百人激战,结果一败涂地。李昭寿被打败之后,干脆就投降了何桂珍,随后还跟着何道员打了好几个胜仗。
可“狗改不了吃屎”,李昭寿强盗本性是抑制不住的,他时常纵兵抢掠,这引起了清廷的不满。1856年,安徽巡抚福济命何桂珍秘密处决李昭寿,李昭寿得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何桂珍和英山县令苏秀槐等四十七名官员,投靠太平天国。
此时的太平天国刚经历天京事变和翼王出走,正处低谷,出身捻军的李昭寿自告奋勇,帮助太平天国联络捻军,促成合作。这使得忠王李秀成对他刮目相看,封为殿右拾文将帅。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横行不法,这使太平天国另一大将英王陈玉成不满,数次要杀他。
李昭寿大为惊恐,在1859年7月率领所部四万人再次降清,并献上了重镇滁州。清廷大喜过望,加封他为钦差大臣江南提督,并赐名“李世忠”。李昭寿投桃报李,利用他在太平军和捻军中的影响力大肆诱降,他的把兄弟太平天国答天豫薛之元率先叛变,将天浦省献给清军,致使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遭到围困。清政府看他诱降屡屡得手,干脆让他专门负责招降。
于是,他便写了一封劝降信给李秀成。
内容:反了吧,跟我一样,到大清来做官。
李秀成没有收到信,信被转到了洪秀全那!
洪秀全一看信件,大惊。他采取的就是老办法:扣人质。
于是,李秀成的母亲妻子都被“保护”起来了。
李秀成连天京也不敢回。
他只有两条路:一、投降;二、卖命。
他选择了卖命。直到他卖到让洪秀全相信,才放了人质。
于是,李秀成不得不考虑他的处境了。天京城内是洪家兄弟的天下,天京城外,陈玉成比自己的势力大,威信高,自己不过是任人宰割的一只小鸡。
作为军人,他只相信一条真理:手中有军队,腰杆才粗壮!
所以,他虽然也想与陈玉成会攻武昌,但他并不那么急。武昌显然并不难攻,他可以让陈玉成打头阵。于是,他一路上招兵买马,谁来投靠就收下谁。先把自己的队伍弄大再说。于是一路上的什么徽州、祁门,都不是他的重点,顺手就攻下来,不顺手继续前进。
当他来到祁门,李秀成第一感觉就是祁门布有重兵。素知曾国藩的谨慎,他误以为这是一个疑阵。
于是,他继续西进。
推来推去的勤王
1860年8月,清朝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情,英法联军进攻天津。
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联军向北京进发。
朝廷危急,下令抽调湘军骁勇善战的鲍超部赶快北上,速赴北京勤王。
按说,发生了这种事,不要皇上下令,各地军队应该迅速北上,救皇上于战火之中。但曾国藩、胡林翼又是怎样一番表现呢?
拖!
为什么要拖呢?这是一道复杂的方程式,须得慢慢解开。
第一层关系是:大清与洋人、大清与洪秀全的关系。
曾、胡两人都洞若观火:1840年以来,列强对大清的作战,没有一次是要真正消灭这个朝廷的。他们要的是利益。把大清逼到谈判桌上来,把银子和土地送给他们就行。这个国家,依然由你们统治吧,选别人来,说不定没这么听话。大清通过多次签订不平等条约,朝野也懂得这个套路了。
大清与洪秀全之间呢,那就完全是两回事了,洪秀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咸丰下岗,然后伏法。
所以列强要的是钱,洪秀全要的是命。
第二层关系是湘军与列强的关系。湘军与一支同等素质的太平军,他们都打得难分难舍,与一支洋枪洋炮的夷军去较量,基本是去送死。既然去送死,那何必去呢?
第三层关系是湘军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眼下太平军这块肥肉咬到嘴边上了,他们舍不得吐。相对来说,与外国人的关系,那是朝廷的事。特别是湘军内部,大家都反对去勤王。第一个反对的是曾国荃,他写了一封信给长兄曾国藩。
这封信现在看不到了。
丢失了?
没有,被曾国藩划一根火柴烧掉了。
那么,这封信到底写了些什么,已无从得知。
没关系,曾国藩的回信还在,于是可以逆推。
从曾国藩的回信中,可逆推出这么一个事实:曾国荃对这个狗屁朝廷看不上眼。朝廷的事,我们不要管它。只要攻下安庆,攻下天京,我们就有资本了。到手的肥肉一定要咬下来。
这段话没错,曾国藩也是这样想的。
接下来,胆子非常大的曾国荃,就议论起皇家内部的事了。大约说了朝廷瞎指挥,我们不要听。现在是我们兄弟说了算。像朝廷重臣奕訢这种人,举止轻狂,看上去就不是个镇得住场面的人物,不过是血统好,年纪轻轻就是王公贵族了。
还说了很多不礼貌的话。
阿弟是个有反骨的人,又是一个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曾国藩看完信,划燃一根火柴,把信烧了。
他怒气冲天地写了一封回信给曾国荃,狠狠地把曾国荃骂了一顿。告诉他祸从口出,要少说话多做事。特别是朝廷的事,你不要议论,半个屁都不要放。
但是,现实摆在这儿,朝廷已下旨救命,不去就不忠。于是,曾国藩先发制人。立即写信给胡林翼,说皇上有难,我们做臣子的应该赴汤蹈火。胡林翼回信说:我们绝对只能去救。曾国藩又写信道:关系是怎样救。鲍超有勇无谋,要救就只能我们两人中去一个人。你去,或者我去,你看呢。
胡林翼心知肚明,说:你说得太对,就这么定了。
于是,曾国藩向朝廷上折,说:鲍超一人去不行,在我和胡林翼中,左右定一个。一俟决定,我们迅速前来。
这个皮球就踢给朝廷。
咸丰此刻正准备西逃,收到奏折,一时毫无主张,若是真的把曾、胡二人抽来勤王,洪秀全乘机北伐,就一切完蛋了。正如前面所说,咸丰知道列强要的是钱,是土地,而洪秀全要的是命。
在要钱与要命之间,咸丰选择了给钱给土地。9月21日咸丰从北京出逃,次日,他就令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负责议和。
虽然咸丰对于曾国藩胡林翼这种拖拖捱捱,磨磨蹭蹭的举动洞若观火。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过分的态度,甚至连责骂也没有。
毕竟,咸丰觉得自己的命与丧权辱国的条约相比,更重要!
于是,勤王就这样“勤”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