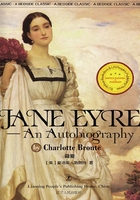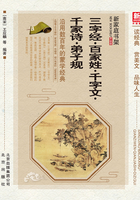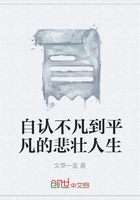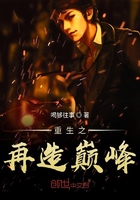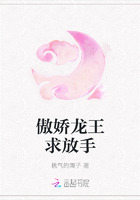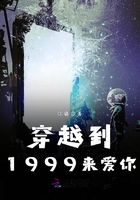雄心勃勃
左氏的加入,使湘军集团增添了一名谋大事的人。
还有一点,左氏目前虽然只带了五千人,但在湘军集团,都把他当个重要人物来看待。隐约有了曾、胡、左三巨头的迹象。于是,对于未来的谋划,三人就常常通过书信,或者相聚来商量。
进军安徽的条件成熟。人财物基本就绪,就等发起总攻了。
总攻前夕,一个惊人的消息,让大清朝野为之震惊:
包围天京的清军江南大营溃败。1859年的闰三月十六日,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全数击溃。清军先退到镇江,再退到丹阳,张国梁不知下落、和春自杀。
接着,常州、苏州、无锡相继沦陷。
这样一来,大清对天京的包围土崩瓦解。
这世界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幸,一些人的不幸就是另一些人的大幸。为这件事暗自心花怒放的是湘军高层。
不久,胡林翼昔日的一个部属死了,他本不值得曾国藩来吊丧,但曾国藩来了,胡林翼来了,左宗棠也来了。
他们来到一个叫宿松的地方。吊丧只是一个借口。三个人见了面,非常高兴。畅谈了几天,有说不完的话题。这大约是咸丰四年起兵以来,相聚最久的一次。
曾国藩作为东道主,弄来了鸡鱼鸭,把饭菜弄得丰盛一点。这三个人,论吃,胡林翼最会吃,什么山珍海味,只要能搞到,他都吃。曾国藩这人,就只要几个煨辣椒就行了,左三爷更简单,经常一棵白菜,炒一盘白菜帮,剩下的叶子打汤。
他们举杯相庆:官军势力一尽,天下就是湘军的了!
这次密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只能从三人各自的书信中去翻找了。比如左宗棠曾对人说:天意有了转机,江南大营一垮,从此官军没有讨贼的力量了。
有人偷偷问过胡林翼,谁可当大任。胡林翼说:朝廷若能将平定江南的事托付曾公,天下就会太平了。
那么,曾国藩又是一种什么心态?
这么一个修养好,老成善谋的人,在给沈葆桢的信中透露了心机:我与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畅谈了几天,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天撑一天。
在家信中则说得更赤裸了:东南大局一旦瓦裂,非胡润帅移督两师,即余往视师苏州,二者苟有其一。
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的乐观也是发自心底的。
这时候,朝廷不得不面对现实,也不得不放下面子。
世上人情冷暖,傲倨卑下,只决定于双方势力的消长,不决定于其他。
清廷倚为长城的官军势力,至此基本垮掉。北方军队,一要保卫京师,二要对付捻军,已无余力来救江南。
死死不肯放权的清廷,准备在胡曾两人中,选择一人来当两江总督。
因为两江总督何桂清临阵逃跑。浙江巡抚徐有壬已上折弹骇何桂清。何下台已成定局。
第一人选是胡林翼。
也有历史记载,胡林翼推荐了曾国藩。
就胡林翼的品格来说,如果除去早年逛点妓院那种生活小节不算,他实在比曾国藩不会差,很能顾全大局。
但改变咸丰这一决定的,是肃顺。
作为满族王室的后人,肃顺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不怎么爱学习,但尊重知识,不怎么有学问,但能治世。他是正宗的满人,但不排汉。当咸丰准备圈定胡林翼时,肃顺果断地向他建议:论名望资历,两江总督非曾国藩莫属。
咸丰十一年四月,清廷下了一道诏书:授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仅两个月后,补授两江总督,并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
苦苦相求,总不到手,时局一变,万事顺意。
这是曾国藩起兵以来,朝廷对他的最大恩典,最大信任!
祁门之困
从九江失利以来,一直受压、心情忧郁的曾国藩笑了。曾国藩把这个喜讯,派专人送往老家荷叶塘。
然后,又感恩戴德地上了一条“谢恩折”。表示对朝廷突然之间授予他这么高的职务,只有惭愧的份儿,他会非常珍惜这个荣誉,这份权力。一定努力工作,报答朝廷对他的无比信任。
当然,这个总督也不会白送给你,撒把马料就是要马儿跑。咸丰马上下了一道谕:江南富饶之地,现成洪贼天下,着曾国藩速救江浙。
刚吃了马料,要马往泥泞里奔,曾国藩当然不会干。他已经坚定信心:死去的罗泽南说的永远是对的,若攻天京,以上游为要,从上攻下,方可取胜。
如果直接回复咸丰,说自己的意见是安徽第一,江浙为末,这是战胜洪贼的关键所在。那么,咸丰肯定接受不了。
摸透了咸丰脾气的曾国藩再也不会干直言不讳的傻事了。应付这低能皇帝,他目前算得心应手了。于是,他首先上报了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三路东进计划”。表示我跟朝廷一样,急江浙之急,想江浙之所想。
应付完朝廷,他还得说服同事。因为胡林翼跟朝廷的意见一样:迅速入江浙。
意见一样,想法略有不同。
朝廷想法的着重点是:你快去,牵制他们(最好是消灭),别让他们北上。其次是江浙是钱仓粮仓,快点夺回来。
胡林翼的想法是:我们老是没有钱用,进军江浙,钱粮有了保障。
曾国藩不同意朝廷的想法,也不同意胡林翼的想法。
那么,他的想法是什么?
很简单:围住安庆,打援军;下一步,重复这一过程:围住天京,打援军。
一种非常笨的办法。
下游乱成一片,没关系。安庆是天国拱卫天京的最后一道屏障,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关哨,而且是粮饷供应的必经之道。
围住安庆,太平天国必然要来救。来救的话,下游必解围。
所以,曾国藩咬定牙关,实施围攻安庆的计划。
于是,他开始做胡林翼的工作。他们只能通过书信沟通。早在咸丰十年四月,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安庆一军不撤为妙。一撤,桐城也要撤,万一太平军攻过来,湖北又危急了。这击中了胡林翼的要害。如果兵力都拉到江浙去,湖北万一失守,那就是他胡林翼的责任了。
这个思想工作,显然做通了。到了五月份,曾国藩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就玩笑式地调侃道:胡大人,收到你的回信了。头场考试我交卷了,得到你的好评。如果今后有谁骂我何不早赴苏境,我就说“考卷”是经过先生批准了的啊。
除了上报朝廷分三路东进的计划外,曾国藩很快就作出了架势,做出一副亲率大军出征的样子。将大营从长江北岸移向长江南岸。驻扎在祁门,看上去是援苏保浙,即“以固吴会之心”。
驻扎下来以后,他就开始调集兵力。
这兵力的安排,非常有意思。看起来,既像围安庆,又像要出征。而实际上,全是为围安庆而布的疑阵。
自己带兵进入皖南,将原驻湖北、由胡林翼指挥的鲍超部调过来,加上张运兰、朱品隆部,计一万多人,渡过长江,做出出皖入苏的姿态。
这只是一种姿态,因为队伍亦可回援安庆。
胡林翼驻英山,指挥各路大军围安庆。担任主攻部队的曾国荃部,驻安庆城下;担任援军的多隆阿部,驻桐城挂车河;担任机动援军的李续宜部,驻青草塥;还有余际昌驻霍山,作为第三路防兵。
这才是重心。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他又玩起了老花样:软拖。他报告咸丰:安庆之围绝对不能撤。这是扼住太平军向西逃窜的喉咙,也是切断天京的粮道。其次,他还摆出了一个最大的困难:有兵,没将!
鲍超回四川老家没来,张运兰在湖南郴州防守,正在赶来的路上,还有粮草正在筹备,等这些工作做好,要到八月份才可正式出兵。
咸丰也没有办法,毕竟出兵不是旅游。武器、粮草、将领,哪一个方面不齐,这仗就没法打。
更让咸丰不得不同意的是:湘军集团的将领,只听命于曾国藩一人。
等咸丰同意他八月份才出兵的计划后,他就开始慢慢地给咸丰做思想工作了。他提出:洪秀全不是“流窜之贼”。他有固定据点,一攻安庆,他就必须救安庆,一攻天京就必须救天京,所以皇上您放心,他不会北窜。二是历来打仗,都是从上游攻下游。从下游攻上游常常失败。武昌打了几回,太平军都是从下游攻上来,所以失败了。江南大营,也是下游攻上游。若是能成功,他们早就成功了,不至于攻了七年,还是溃退了。我要是现在进兵江浙,形势也跟江南大营差不多。
所以,我相机行事。全力攻打安庆,早点拿下安庆,不怕太平军不退出江浙来救。
咸丰同意了吗?
只能说他在观望。如果像你曾国藩说的,能攻下安庆,攻下天京,那当然太好了。于是,他就来谕天真地问:那攻下安庆要多久呢?
曾国藩不敢夸海口,用了一个模糊概念回答了这位皇帝:要等打退援军以后。
这个回答真有趣。围住安庆,援军来救,把援军基本上消灭光,安庆也就是一座死城了,要等这个时候才攻下。
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神仙都搞不清楚。
要是平时,咸丰一定会火冒三丈。但是,他现在火不起来了。万一洪秀全这小子率兵北上,直接到北京来讨要这顶皇冠,还得靠你曾国藩来救驾。
咸丰只好说:“均酌情缓急,妥筹办理。”
这也是句模棱两可的话,你看着办。
什么“妥筹办理”?湘军姓“湘”,只听我曾国藩的。他早就下达了死命令:一切以安庆为中心,谁也不能动摇信义。曾国藩给他弟弟的指示中说:你只管给我围安庆。外间的事,你一概不要管,也不要乱说。他给水师彭玉麟的信中说:我虽南渡,水师仍以安庆为根本。
他处心积虑地把这些弄好后,就把指挥部设在祁门。
样子做得十分像:正在准备,一旦准备好了,就来。江浙的同志们不要老是向皇上上奏写折子。
1860年的曾国藩,已非吴下阿蒙,他有信心,咸丰只能尊重他的意见。
湘军围住安庆,果然是围魏救赵的好方法,把太平天国的主力一下子吸引过来。
太平天国召开军事会议,洪秀全亲自主持,通过反复商讨、天国采取的军事方针也同样是四个字:围魏救赵。
下面就形成了双方如下军事意图:
曾胡围安庆,断天京粮道。
天国围武昌,断曾胡粮道。
双方都没错,结果只看谁的战略意图实施得顺利。
天国派出最优秀的两员大将——陈玉成与李秀成,沿长江而上。
陈玉成从北路挺进,李秀成从南路挺进。
两路重兵,联手西进。
曾国藩把指挥所设在祁门。设在这儿非常犯忌。一是祁门不近水路,二是祁门处于大山包围之中。这儿是一个盆地。三是保卫祁门的部队都摆布在安庆和江西两个战场。他所需要的兵力,有的在路上,有的一时赶不到。
祁门的东边是徽州,驻有一万多人。这支队伍原属张芾管。现在,张芾被朝廷调走,这支部队就受曾国藩的节制。
有这么一支队伍,也许让曾国藩觉得还有点依靠。他派出李元度驻扎在祁门与徽州之间,筑起第二道防线。
归他直接指挥的鲍超部、张运兰部都在向祁门靠拢。
于是,曾国藩觉得很安全。
但他的幕僚们觉得并不安全。
为什么幕僚们觉得祁门不安全呢?
因为他们长期受曾国藩军事思想的影响。湘军不说总部,就是一支营队驻扎一地,也讲求背靠大山,地势高于四周。而祁门是四面都背靠大山,反而成了洼地。
这种洼地,就是有百万大军,你也施展不开。
一驻扎下来,就有人来建言,说:大帅,此处不宜扎营。
曾国藩笑笑,不说不宜,也没说宜。
曾国藩没有想到太平军进攻的正是徽州,也没想到徽州守军如此不堪一击,更想不到李元度全无方略。
1860年8月,李元度进入徽州城,他把原来驻在徽州城内的一万多人,放在城外布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