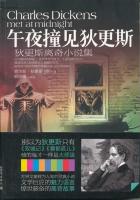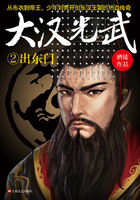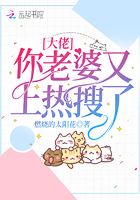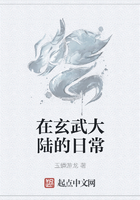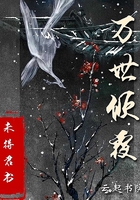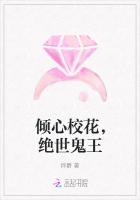家人对这具“无头尸”持有异议,曾国藩恨不得骂他们是一群蠢猪。
有关曾国华的尸身是不是真的,就成了一个谜。
但是,曾国华死了是无疑的,如果他活着,绝对难以瞒天过海。至于野史传说曾国华后来听从阿兄劝导,出家做了和尚,那不过是无稽之谈。
曾国华死后,曾国藩就只能用咸丰八年四月请刘昌储作法的那个“败”字以及“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来解释了。他安慰曾国华的妻子说:这是天命。
然后对在家的兄弟弟媳子侄一一作了安排:要纪坚、纪梁、纪鸿、纪渠、纪瑞等子侄轮流到老屋(曾国华家)去久住,好好陪着细娘,五十、大妹、二妹也要轮流常去,并且要请亦山先生(没有考证出是谁)常住白玉堂,安慰曾国华妻子的心。叮嘱家人要对国华老弟一家厚爱一等,让她们(都是女的,包括妻妾女儿)感受曾氏大家庭的温暖。
除了曾国藩的大义之外,李续宾父亲的举动,也体现了乡人的团结。李续宾与66位同村兄弟的死讯,隔了差不多一个月才传回老家。全族全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家家有死者,户户有冥魂。
一向战无不克的李续宾成了上里人们的骄傲,成了他们李氏族人的骄傲。
一时如大厦倾坠,方圆十里,亲朋戚友哀号不绝。
悲痛之中,他们尤其痛恨见死不救的赵克彰和李续焘。赵克彰还好说一点,离三河有六十公里,而李续宾的堂弟李续焘一家却在村里抬不起头。他家怀着巨大的愧疚,不得不天天面对同村同族人的指责。弄得李续焘全家一连十天,闭门不出。
得知李续宾战死后,胡林翼再也在家呆不住了,他穿着孝服回到武昌视事,第一个举动,就是处理赵克彰、李续焘两人。
听到这一消息,李续宾的父亲急了,向官文上书求情。他在信中写道:续宾已死,我不忍看赵李再死,我与同族合村谅解他们,当时敌众我寡,相救也是凶多于吉,所以要请您官大人刀下留人。然后请合族大小一一签名按上手印,派专人骑马送往湖北。
官文收到“求情书”,也许觉得自己有愧,与胡林翼商议。胡林翼感叹道:李父深明大义,读之令人泪下。
于是,赵克彰、李续焘得免死罪。
后来,赵克彰屡有战功,升至总兵。不过,三河之战,也是他一生的污点。李续焘也当到总兵,其后史实不详,估计就是胜利后,没有回乡。
三河之败后,湘军士气不振。这对湘军集团以安徽为基点、直取天京的战略,打了最闷的一棒。但信念坚定的曾国藩与胡林翼达成共识:不管情况如何变化,原计划决不改变。
作为一个战略家,曾国藩在那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佼佼者。1859年年初,他就定下了军事路线图:以安徽为重心,兼顾江西与福建。水陆并进。进攻皖南以分金陵之势;进攻皖北以分庐州之势。
二月份,他就把大营移到抚州,就近指挥。
风云突变!
石达开突然离开江西,窜入湖南。一时,湖南紧张起来。
曾国藩不得不打乱计划,分兵回湘,于是,萧启江、刘坤一、赵焕联、周世宽回湘,骆秉章除了组织湖南军队外,还向湖北借兵。胡林翼也不得不支持,湖北派萧翰庆水师至长沙,陈金鳌、舒保后继。
于是,进攻安徽的事,暂时泡汤。
一直推崇曾国藩的胡林翼看到一个机会:石达开显然只是路过湖南,他的目的地是四川那片天府之国。而四川正好缺总督。如果让曾国藩挺进四川,先把总督一职弄到手,以后办事就方便多了。对于湘军集团来说,多弄几个地方官,粮草军饷就多份保障。
但是,咸丰会不会给曾国藩这么一个实权呢?当然也不敢打包票,风险有,希望更大。
于是,胡林翼做官文的思想工作,让他上奏。旗人嘛,在皇帝面前说话分量重一点。
官文上了奏折。
咸丰说:行,让曾国藩入川吧。
不过没说给他个总督。
咸丰跟曾国藩较上劲了。自从让曾国藩第二次出山之后,他反正不说放权的事,从援浙到援闽到援川,他就让你曾国藩做一个包打石达开的“游击队长”。
好心办成坏事了。
上谕既下,不得不动身。胡林翼觉得满心愧疚,曾国藩则聪明多了,老一套,凡是不愿意的事,就软顶,磨磨蹭蹭,从江西动身到湖北,并不急着赶到四川去。
你没把我当成一盘菜,我也不把你的命令当回事。曾国藩确信,事情一定会有转机。
经过思考,曾国藩判定,咸丰只是利用他,但不得不利用他。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不再冲动,一切相机行事。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正如曾国藩所料,咸丰也是相机行事。他时冷时热,从这个层面讲,咸丰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好在湖南又帮了曾国藩的忙。
几万大军在宝庆把石达开围住,展开了一场有名的“宝庆之战”。
宝庆即现在的邵阳,它有多大的战略意义吗?
实在不大。石达开要攻长沙的话,那要占据湘潭,顺流而下,才有点意义。石达开要进四川,多条道路可进,不必从宝庆进。
它没有多大的战略意义,为什么石达开要占宝庆呢?就是他打到了这附近,顺手牵羊把这座城市攻下来,抢点物质再走。
石达开没什么大意思。
湖南觉得这意思太大了。
宝庆离湘乡一百三十公里。而湘乡是湘军将领的老巢。万一石达开进犯湘乡,那湘军在外拼死拼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保卫湘乡跟保卫长沙一样重要。把湘军的老家抄了,那湘军就谁也没心思打什么鬼仗了。
一时,湘军精锐尽返湖南。而且骆秉章一声号令,社会各界一下就捐了十多万两银子。
石达开十五万人。湘军七万人,湘军两支大军,西路归刘长佑指挥,东路归正在家里休假的李续宜指挥。
石达开当然是选错了地方。选到湘军老巢附近来打一仗,不用说,湘军比在任何时候都卖命。反复斗了几个回合,石达开无法得手。
石达开气急之下,亲自跑上宝庆东门外的木楼上,把帅旗一挂,亲自擂鼓。
湘军一见石达开竟然亲自出来客串角色了,全体兴奋,在一位叫田兴恕的将领率领下,像蝗虫一样地涌向木楼,枪炮齐射。石达开的裨将护卫死了不少人。他只好退入城中。
把城门关上之后,石达开下令:立即埋锅造饭。吃了饭偷袭。
石部攻上来的时候,湘军还正在吃饭。人人把碗一丢,立即跟石军干上了。石达开仍然擂鼓。
在老家不打点威风出来行吗?湘军进行反攻,人人拼死向前。石达开又只好退入城中。
七月份,石达开终于撤退,往南方走,然后回到了他的老家广西去了。
石达开在广西见了他亲妹妹一家。他送了几尺绸缎给妹妹,很伤感地说:阿妹,若我今后发达,你自可来找我;若我们今后不再相见,这绸缎就是我的影子。
说得阿妹眼泪双流。
石达开退走广西,曾国藩的软顶又胜利了。四川那山高路远的地方,也就用不着去了。这时,曾国藩磨磨蹭蹭到了武昌。胡林翼从黄州赶来,与他面商,请官文据实奏请,曾国藩暂缓入川。
曾国藩终于明白一个道理:软顶是最有用的一招。你说东,我往东,你说西,我往西。形势一变,你就不得不依我的。
既然不要入川了,那么下一步呢?曾、胡两人就达成了一条共识:不管情况如何变化,再不分心,一心一意联手图皖。
胡林翼的力量也好,曾国藩的力量也好,都单薄了。合作一处,统一动手比较靠谱。
石达开也好,其他匪贼也好,都是枝叶,只有撬动天京这个支点,一切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既然是好计划,就应该立即实施,越快越好。
可就在此时,有人摊上大事,需要他俩联手营救!
左狂人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1812年生,比曾国藩年少一岁,与胡林翼是同年。此人四十岁以前,是个布衣。中过举,就是中不了进士。所以后来,他当了大官,凡是来见的客人,是举人出身的,先接见,是进士出身的,排到后面。
按他的说法:进士没什么用,都是书呆子。
1859年,他快五十岁了,仍然是个狂人,一点也不收敛。
不过,凡是真狂的人,总有底气。
比如这位狂人吧,青少年时就有文名。一介布衣,连林则徐这位在当时被朝野称为伟人的大人物,路过长沙时,也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专门接见了他。两人只谈了一次话,林则徐就到处给他打广告,说那个叫左宗棠的人不得了。
再怎么不得了,中不上进士,朝廷不用。朝廷当时“人才济济”。左狂人一气之下,就取了个“湘上农人”的名字,结庐在湘潭,读书兼种麻。
怎么结庐在湘潭呢?
他因家贫,做了上门女婿。
太平军一入湖南,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请他出山,请了两次才出。后来骆秉章当巡抚,又请了两次。
所以,时人给他一个外号“今亮”——意即当代诸葛亮。
一个当代诸葛亮式的人物,给巡抚当幕僚,那就是大材小用了。所以,左狂人入了骆秉章的幕,中丞府中那点事,他一边喝酒,一边像巡抚一样地对身边的人布置就行了。
因为能力太强了,事事做对了,弄得骆秉章失业。久而久之,骆秉章就错位,好像自己是幕僚,左狂人是巡抚,事无巨细,都要来征求他的意见。
甚至有天夜里礼炮三响,骆秉章还在睡觉,一下被这礼炮声惊醒了,一问左右,是左三爷在“拜帖”(一种仪式,凡是下面送给皇帝的奏章,出发之前,要放礼炮)。也就是说:左三爷代他写给皇帝的奏章,他骆中丞看都没看,左三爷就发给皇帝了。骆中丞问清之后,躺下再睡。
可见,他对左三爷之放心。
湖南在左三爷的辅佐下,成了当时最有名的省:出了一支湘军,供应湘军这么多银子,军事经济两不误。所以,左三爷虽然是个幕僚,全省上下都知道他是个实权派,就是省城的官员见了他,也得恭恭敬敬。
左三爷能干事,却又偏偏是个“愤青”,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他最看不惯没本事有架子的人。于是,下面这一位就让他逮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