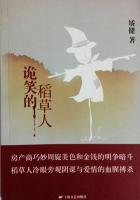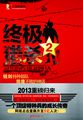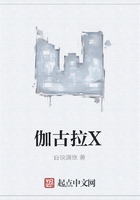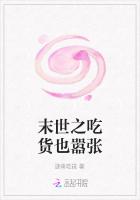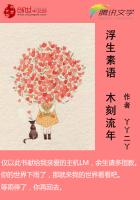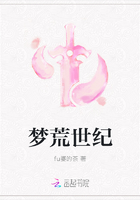没势力别叫板
湖北局面大为改观,但江西时局仍然不容乐观。
1856年至1857年年初的江西战场,乏善可陈。
太平军牢牢地控制着江西的大局。
塔齐布、罗泽南死后,太平军形容湘军是“倒了一座塔,敲破一面锣”。而这一年,曾国藩可以倚靠的大将少得可怜。嫡系精锐由李续宾率领,在湖北战场上奋战。手下周凤山,算不上骁勇之将。幕僚出身的李元度还时时让他担忧。水师方面,虽然彭玉麟来了,但被太平军钳制于内湖,也没什么作为,仅能自保而已。
江西百姓的风气,在曾国藩看来极其不好。太平军每到一处,百姓没有“血性”,给太平军带路、报信、提供粮食。“附贼”之状,令人气愤。
战争陷入僵局。他困守一隅,几乎无法动弹。
不久,曾国藩的爱将毕金科战死。
毕金科是他着意培养的一名战将。此人二十多岁,骁勇异常,是周凤山的副手。这支队伍本来是周凤山领导,但周凤山不知所终。
这是一个谜,他是逃了?病死了?披发入山了?
曾国藩派人查过了,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湘军攻克天京以后,也没有此人的消息。
毕金科很年轻,攻下饶州后,面临一个最残酷的现实:很快就要断粮了。
断饷还可以补发。
断粮就只能到阴间去补发了。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时,江西官府就说:你把景德镇给我攻下来,我给你粮食。
为什么要把景德镇攻下来呢?
因为那儿盛产瓷器——是一块财政收入的肥肉。
毕金科没办法,总不能到老百姓那儿去抢粮食吧。于是,他明知是去送死,也只能虎口拔牙了。
当毕金科率部攻入景德镇后,他一下醒悟过来:中计了。
因为,城攻得太容易了。
果然如此。太平军把城门一关,玩起了关门打狗的游戏。
这场巷战极为激烈,进城的人,只有十多个人杀出了城。
这包括毕金科与他的亲兵。
但是,他们只是出了城,并没有逃出太平军的手掌。
追上来的太平军把他们团团围住。
太平军太害怕这个二十多岁的骁将了,不敢近前,只是拿着火枪向他们喷火。
毕金科被烧得面目全非,仆地,七窍流血。
这其实就是江西官场故意这样整曾国藩的。你要粮吧,你就去打仗吧,打败了,你有何面目总是要粮?
曾国藩欲哭无泪。
此时的曾国藩,三面不讨好。咸丰是一副冷面孔,江西官场跟他是对头,太平军正在围困他。他孤立无援,几乎没打过胜仗,士气低落。
曾国藩想不清楚,这年头,好像不是洪秀全起义,而是他起义,太平军追着他杀。官府对他抑制打压,朝廷对他疑神疑鬼。几股势力,都恨不得他早点死掉一样。
他进入了人生最苦闷的时光。
唯一让他感到温暖的是:湖南没有忘记他,家人力挺他。
前文说过,湖南已派出刘长佑一支人马速赴江西来驰援。银两也在不断筹措中,设法送到军营来解燃眉之急。
几年之间,长沙官场为什么从排挤转为支援呢?
因为几万湘籍士兵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湖南百姓利益。
湖南不救危,湖南必动荡。
说不定一支洪秀全的盟友就会揭竿而起。
曾家更急,曾国华率四千人已在路上,离南昌越来越近,但曾家仍然心急火燎。曾父令儿子曾国荃速去阿哥营中效力。
但曾国荃的想法不同,他想招一营兵,前去为阿兄分忧。
恰巧这个想法得到另一个湖南人黄冕的支持。黄冕新任吉安知府,他答应负责筹集粮饷。
曾国荃即往长沙谒见骆秉章。
有人募兵,有人出钱,何乐而不为?骆秉章非常干脆:速募之。
曾国荃小名宽九,乡人尊称他九爷。九爷年纪不大,刚三十出头,比阿兄年少13岁,优贡出身。
与阿哥相比,他的特点是:不讲那么多规矩。
听说九爷招兵,湘乡出现了动人的一幕:父送子上场,妻送夫投军。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吾乡之气,尤为壮观,往往招一千人,万人从之,招一万人,数万人从之”。
难道他们不知道江西的困局吗?
当然,作为朝廷命官,曾国藩有些话不好说,比如连年征战,民不聊生,当兵至少可以混口饭吃,运气好的人,还可升官发财。
他在给弟弟们的家信中,倒是写得大胆:我在湖北时,诸事顺利,不见有人来投军。今在江西,万事皆不顺手。郭云仙十六日到营,曾莘田、易敬臣兄弟于十五日到营,罗云皋于初旬到营。事机不顺而来者偏众,可见乡间穷苦。
这才是真相。
既要支持湘军,又要负责全境剿匪。湘乡赋税之重,确实非常人难以想象。当兵吃粮,也是逼出来的出路。血性固然有,现实比血性更残酷。
很多人挤破脑壳要去当兵。
在家的日子实在没法过了。
当兵吃粮,总比饿死强。
这么多人要当兵,曾国荃立了一条规矩:只招家门口周围十里人。
十里之内,谁不认识谁?只要拐上二三道弯,保准都是亲戚。
曾国荃要招的是一班死士!
太熟了,太亲了,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他比理学名士的阿兄现实多了。
1856年冬天,这支后来称为“吉字营”的队伍也上路了,因为是保卫吉安,所以取名“吉字营”。
1857年的新年,曾国藩过得极不愉快。
虽然来了两位兄弟,也帮他打了几次小胜仗,但于大局,没有丝毫帮助。天国发生了内讧,但天国并没有衰落的迹象,反而在陈玉成、李秀成这些后起之秀的经营下,天国保持着一副活力四射的样子。
江西战场上的湘军,仍然各自为战,七零八落地分布在南昌周围。
咸丰对曾国藩开始冷落。皇帝也是吃奶水长大的,有奶便是娘。胡林翼在湖北搞得风生水起,他就开始转移注意力,把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的“署理”两字去掉,改为实授湖北巡抚。
胡林翼依托的是什么呢?依托的是湘军班底。
曾国藩自己苦心经营的湘军,就这样送给人家成为发家的资本,然后,这个过气的统帅,就会随着时光的消逝,黯然失色。
他的心情悲苦到了极点。
但有什么办法呢?耗着,也就只能这样耗着。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他更加崩溃。1857年2月,他的父亲死了。
闻此噩耗,曾国藩向咸丰上折请求丁忧。
他不等咸丰批复下来,就带着两个弟弟离开江西,径自回家。
当时,湖南湖北两地官场,一时哗然,纷纷指责曾国藩没有得到圣旨批复就撒手不管了,这分明是撂担子,发脾气,不负责任。特别是左宗棠,对他破口大骂。
蹊跷的是:咸丰没发脾气。他批了曾国藩三个月假期,赠奠银四百两,要他休假期满后,仍回江西督办军务。
咸丰为什么没发脾气呢?
咸丰觉得江西事务的安排,你曾国藩既然在奏折中交代得清清楚楚,那么,早点回家治丧也是应该的。因为咸丰也觉得欠了曾国藩一点什么:前番母丧,没守孝就出来了,今番父丧,早点回家也是情理中事。
还有一层意思:你在江西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来,要回去就回去吧。
只是最后叮嘱了他一句:三个月后,仍回江西。
三个月之后,曾国藩给咸丰上了一道折子,要求在家终制。
咸丰说:再给你几个月假吧。休息好了,还是回江西。
曾国藩看到了一丝希望,咸丰还是没有彻底抛弃他,于是,他想和皇上谈谈知心话,希望皇上理解他的苦衷。
他很真诚地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我最尊敬的皇上,请您耐心地读完我的贴子。您知道吗?我此刻的心情,就像风雨中的长江,一泻汪洋,就像婴儿之于慈母,白云之绕山岚,我有多少话儿要向您倾诉!我为这个头,实在是勉为其难。我无权无势,名为带兵侍郎,实质上不如一名提督有实权,我带的兵,虽然能保奏官阶,都是些空顶子,手下人没得什么实惠,所以要他们为我卖命,我也有我的难处。我没有行政大权,筹饷的事,都要经过地方官,粮饷难保证,几乎是向他们乞求,等同讨米叫花。我的官名官印常常变化,朝廷又不与地方通气,工作不仅得不到地方支持,有些人借此奚落我、耻笑我、侮辱我,我实在难以忍受。
当然,最终诉求是:我没实权,你应该给我一个巡抚或者总督的实权,我才好做事。
曾国藩说的没有半句假话。有职才有权,有权才有为。自古如此,永恒真理。
咸丰看了折子,非常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曾国藩万万没想到咸丰如此绝情。失落、悲愤、无望塞满了他的脑子。他的牛脾气来了,干脆来个“你做出初一,我就做得出初二”。他给这个绝情的皇帝回了一个折子,说:我就在家终制,以后,我也不出山了,湖北也好,江西也好,我所有的事都不管了。
天下缺了你,地球就不转了?
不管就不管,咸丰冷处理。不跟你玩嘴皮功夫了,直接回答:同意。
那么,咸丰为什么绝情呢?
这得从另外一桩事情说起。
咸丰接到了江南大营和春的密报:值此天国内讧,我等江南江北两营,决意联手端掉洪秀全的老巢。石达开已出走,城内非常空虚。
另一份密折是官文报来的:李续宾部已扫清湖北境内鄂州、黄州、大冶、蕲水、兴国、广济、黄梅之匪,正进军九江。
形势正发生重大逆转。
所以咸丰毫不客气地回批道:着曾国藩开侍郎缺,在籍守制。
曾国藩备感失落。
又急又闷
曾国藩又气又恨,却无可奈何。
从此,他成了一名山野村夫,天天与青山相伴,与野老相处。
如果春风得意,衣锦还乡,他还可以到处走走,访亲问友,听听一片恭维声。可官场中人都知道曾国藩与咸丰谈崩了,很少有人来访他。乡野村夫,又觉得他是朝廷大官,不敢轻易去打扰。他积愤于胸,整日郁郁寡欢,脾气也变得暴躁了。有一天,曾国荃夫人请道士在家中驱鬼,半夜深更,道士念念有词,扰得人睡不着,曾国藩爬起来,对着弟媳一顿责骂。
曾氏守孝的房子叫思云馆。
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写得非常悠闲自在,说就住在这座平房里,写写文章,教教子侄功课,也会会来客。
其实,他的心里比任何人都急。
他生怕形势迅猛发展,让别人摘了桃子,自己终老山林。
有些史学家引用曾国藩的好朋友欧阳兆熊的话,说曾国藩在山居的日子,反省了自己的人生,比如从程朱到法家,再从法家到庄老,完成了人生三大转折。
1857年8月,新任江西巡抚耆龄奏请曾国荃复往江西带兵。此时,湘军水师在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的合作下,内湖水师冲出鄱阳湖,与外湖水师会合一处,水师又成一支劲旅。形势越来越好,曾国藩不免惆怅。
曾国荃来问阿兄的主意。
曾国藩只说了一句话:尔非朝廷命官,无须守孝三年。
他急急忙忙催着老弟上路。
他毕竟关心战事,有了阿弟这根线,前线战事,他才好遥控。
9月的一天,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叫周俊大,湘乡上里人,曾经和曾国藩是同学,同中秀才。周秀才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处境,快五十岁了,没有半点功名,能不能去军中效力,弄个九品八品功名。
曾国藩心软了,说:你暂且回去,去军营就不必了,我帮你想想办法。
于是,他写信给曾国荃,列上姓名,叫他下次打了胜仗,把此人混在其中报上去。
过了几天,他妹夫带郎中给他来看病。他又觉得对不起妹夫一家,又写信给曾国荃,说有机会,把妹夫也报个功名。
大约快过年了,曾国荃一下从军营中寄回三百两银子,曾国藩写信给弟弟,说:你寄回来的银子实在太重要了。现在我住家,才知道家中的用度其实非常紧张,我以前每次寄给家里的钱太少了,太对不起父亲与兄弟们。那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一出山,就声明“不爱钱,不爱官,不爱权”。你现在在军中,收入与李续宾等人相当,寄这么多钱回来,也不为过。
曾国藩在这段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变得更现实。
比如胡翼林,通过湖北新政后,手中有钱了,他笼络将领的办法是:每次到营中拜访各位将领,就是见面就送上五百两、一千两银子给营官,说你们辛苦了,将士因此“乐而效命”。
而他的弟弟曾国荃更绝:每攻一座城,他放手让手下兵勇大肆抢劫,申请军功时,又放肆造假,没到过军营一天的,只要你报上来,他都帮你报上去,所以,他军中士兵还没出生的儿子,取个假名,也有功牌。军中皆大欢喜,每攻一城“将士冒死以进,敌为之惧”。
曾国藩反省,为什么胡林翼在湖北弄得那么好。胡林翼竟然能与官文那种昏庸的满人打得火热。胡林翼不会打仗,却能团结将士为他拼死效营呢?
也许这就是自己的原因了。自己太过于傲气,不擅长与各种各样的人周旋。连皇上也敢得罪,这种性格让自己吃了大亏。今天的处境,就是性格带来的苦果。
所以,他决定:如果有出山的机会,一定要痛改前非。
只是这种机会很遥远,咸丰似乎已忘了他,朝廷也似乎忘了他。甚至整个官场也差不多忘了他。只要有故人来访,他就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