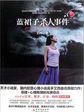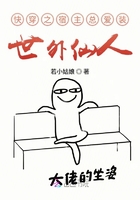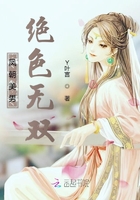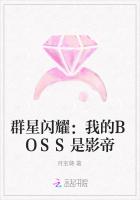一把硕大的铁剪,对准烧得通红的铁链剪去。操剪的四个湘勇,手掌间冒出丝丝黑烟。因为铁剪通红。
一二三。终于,在高温下烧得通红的铁链,气若游丝地一剪两段。
剪掉一节,远远不行,每一节中间,太平军都用木簰固定好了。
小船有好几只,在炮火的掩护下,炉火通红。
太平军发现,左侧一条战船上,站立着一个大汉。他一直站在船头,指挥着船队冲锋。
太平军没有看走眼,这位就是杨载福。
一发炮弹,落到了他的眼前,水浪蹿起几丈高。有两个胆小的立即蹲下去抱着头,杨载福一手一个,拎小鸡一样拎起来,喝道:像老子一样站直!
朝右边发炮。因为右边那一位更可恶,他连上衣都没穿。
冷冷风中,他独立。
太平军没看走眼,这位就是彭玉麟。
一发炮弹落在他的跟前,水浪快要把船掀翻了。水雾散去,那人巍然屹立。
两位都安然无恙。
太平军的炮火并不厉害。当时,清政府还可向列强购买洋炮,太平军的炮基本上是自己造出来的,其次,就是从战场上缴获的。
所以,两位不死的原因,也与太平军的劣质火炮有关。
湘军水师乘势冲进敌阵。最常用的办法:一是炮攻,二是火烧。湘军有条原则,一般不要太平军的战船,因为都是民船改造的,掳了不中用。所以,一律用火烧。
双方激战开始,太平军处于劣势。慌乱中,有很多太平水兵落进江里,拼命游向自己的船队,船队要逃命,挥刀就斩,所以船帮上,挂着许多断了的手臂;太平水兵一见,竟然游向湘军水师的快船,请他们救其一命。
这更是弄错了方向。
太平水师挤成一团,船只首尾相连,这时,杨载福说:迅速往下游冲。湘军水师直下三十里,冲到一个叫龙坪的地方。杨载福说:现在放火。
这时,刮起逆风,火从下游往上烧,上游逃出来的船,不明就里,一下进入了火海。船船相撞,互相着火。
除了湘军放火以外,太平军自己也放火烧船,因为他们绝不能让粮食和火药落到湘军手中。他们放弃船只,登陆逃散。
据曾国藩奏报:贼军水师,从此不足虑也。大小船只,计五千余条,或沉或烧,一荡而尽。
岸上,陆军发起了进攻。
太平军发现,有时候,炮弹对某些人是不起作用的。比如这群蜂拥而来的湘军,像蚂蟥一样,明明斩断了一段,另一段仍然不死,越来越多的蚂蟥,朝着炮台冲过来。
湘军水师,终于突破三道铁链,陆军攻下半壁山,大破田家镇。
是役,成为湘军继武昌大捷之后的又一杰作。
彭玉麟、杨载福以身体作为防弹衣的神话不胫而走。
太平军怎么也想不清楚——这些人是不是吃了什么药,或者吃错了什么药。
咸丰更弄不清楚,他收到曾国藩的捷报,特别是捷报中所描述的“傲立船头,以身御炮”的彭氏方法,他更是想了好久都想不清个头绪来。只能说:此乃天地神鬼助我之显象也。
湘军连连得胜,连曾国藩这么谦虚的人,写信给家中兄弟们时,也不免炫耀: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
一句话,古人早就写进了书里:箪食壶浆以迎将军。只是他自己不好意思这么写罢了。
曾国藩与湘军们认为:他们会一路所向披靡,洪秀全注定会从金陵逃窜。
曾国藩在上奏给咸丰的折子中,有这么一句话:诸路带兵大臣及各省督抚,择要堵御。
意思是:我赶得洪秀全抱头鼠窜,各路人马帮我堵住就行了。
牛人石达开
湘潭之败,岳州之败,武昌之败,田家镇之败,天国高层震动。天京城内,太平军集团对这支新兴的湘军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们迅速调整了部署,派智勇双全的石达开坐镇安庆,主持西线工作。
石达开举义金田,授左军主将,时年十九。参加起义时,他“毁家纾难,祭纛誓师”。
他年轻有为,在太平天国的五大王之中,是年龄最小却战绩赫赫的一位。
在秦日纲据守田家镇时,他就写信给秦,要他“不宜出战,固守待机”。
但秦日纲没有听他的。
现在,就轮到他来收拾残局了。石达开一上任,马上布防。他派林启容守九江,罗大纲扎兵湖口对面的梅家洲,黄文金攻都昌,以策应九江守城。
一时,猛将云集,部署得当。
曾国藩也率三万余人屯兵九江城下。
双方都积着一股气,准备决一雌雄。
屯兵九江城下的湘乡人甚至发出更超前的口号:打完天京过年。
前面不是发出了“杀完敌人我们回家干什么”的疑问,现在却想速战速决。
离家的路越远,想家的情越浓。毕竟他们都是农民。此外,更有一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想法:听说天京城洪秀全的妃子有几千,银子更是多多。
彼时,为了证明天京城里美女多,湘军内部还流传这样一个传说:
说洪秀全满周岁时,家里做了一场酒。按中国人的风俗,这天他要“抓周”。
家人放了两样东西在桌子上:笔、算盘。
传统的说法,抓到笔会读书,会中秀才举人。抓到算盘会算数,会成理财高手。大家引导洪秀全去抓,洪秀全却没有任何反应,对这两样东西毫不感兴趣。在引诱了数次之后,洪秀全终于抓住了一样东西,而且抓在手里死死不放,大人掰都掰不开他的小手。
这就是小姨手中的梳子。
于是,有人背后议论:洪秀全长大后会是个风流色鬼。
编这故事的意思很明白,打进金陵去,把那色鬼的妃子抢回家。抱着妃子睡觉,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要知道这群农民不出乡,连县长的太太都没有机会看到。
与兵勇想法不一样,湘军大佬们,考虑就更深远了。他们离家越远,粮饷供给就越困难。因为钱粮均由湖南一省提供。他们不想这样耗着时间。耗久了不行啊,后勤补给线太长。
其次,他们当然也想银子。不过,那不是最主要的,他们都是读书人,知书明理,想的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个人生价值当然不是空洞的,包括银子、顶子、名誉。
湘军上下的想法有一点是共同的:长驱直入。
咸丰也和湘军上下想到一块了,下令在湘军东进的同时,各地清军“择要之区,截贼往来之路,与曾国藩声势联络,上下夹击”。
大军云集九江,但九江城里的守军拒不出战,九江久攻不克,曾国藩改变战术,命主力绕过九江,夺取湖口。
湖口,位于九江东面,上通楚北,下达皖南,是长江与鄱阳湖的连接之处。石达开亲赴湖口,命令黄文金守湖口,罗大纲守湖口对岸的梅家洲,加上林启容的队伍,三处水陆共有两万人。又命秦日纲、韦俊、陈玉成率军三万,加大力度骚扰清军。
来吧,我自有办法对付你!秦日纲、韦俊、陈玉成从后面绕过去,直捣湘军后方。
也就是说,你想前进,我让你后院起火。
后院起火就等于扼住你的喉咙——物质供应链断了。
本来,这丝毫不成问题。总督杨霈带着几万人的队伍,荆州将军官文也率领着一支几千人的清军。他们完全可以对付这点骚扰。
但无论是杨霈还是官文,他们身为军事主官,却不想打仗,东边来了敌人,他们跑到西边,西边来了敌人,他们跑到东边。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他们就这样躲来躲去。
一个皇帝碰上这么一群人,只有吐血。
当然,帮着吐血的还有曾国藩。
曾国藩只好分兵前去扑火,又调胡林翼部增援汉阳。胡林翼部也是一支弱军,帮不上多大忙。他受曾国藩节制以后,一直在湖南与湖北边境剿匪。后来,进入湖北境内,授予了湖北按察使,只是多了一颗印章而已,他还没机会与总督巡抚等人见面。一个省政府,几大要员,各驻一个地方,分署办公。说实话,他们谈不上治理全省,发展生产,只是各保其命。
石达开看中了湘军的弱点:求战心切。于是,他定下十六字诀——避其锐气,避其锋芒,拖累曾妖,伺机下手。
曾国藩率大军来到九江城外,但只是水师到齐,陆师返回鄂东。这本是一个友军不配合的尴尬布局。但是,他错估了形势。
他以为水师勇猛,能创造任何人间奇迹。
湘军士气沸腾,情绪饱满。
朱强四这天找邓有良来写信。邓有良问:你准备写些什么?
朱强四脸红了,半天说不出。
邓有良说:问父母好,向父母报平安,说在这儿一切都好。就这几项吧。
朱强四搔头抓脑,附着邓有良的耳朵说:要我父母打听一下,红妹子嫁人了没有。呵呵。
邓有良与朱强四是同一个村子里的,自然知道朱强四喜欢红妹子的事儿,所以白了他一眼,嘻笑道:还是老想着红妹子啊?
朱强四说:仗快要打完了,叫她别急着嫁人,我回去就娶她。
一封寄往湘乡二十四都的信发出了。
连老家人也猜想:曾大人打下天京指日可待。
湘军以为水师可以倚重。石达开就是不出战:激你,气你。
连打了几个胜仗的湘军等不及了,发起了年底进攻。
季节已是隆冬,天天冷雨不断,有时又雨雪交加。湘军疲苦不堪。
但石达开定下了一条死原则:固守各寨各垒,避而不出。
如何是好?
天公不作美,太平军又固守不出战。湘军将领纷纷请战。
士气宜鼓。曾国藩决定战略大进攻。
他调鄂东塔齐布、胡林翼移师九江。
石达开下令宿松之军回师鄂东,不久攻下黄梅。
两军把各自的力量调整好之后便开战了。
从咸丰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湘军叠攻九江、湖口、梅家洲。
石达开仍然是十六字方针,他令部下在东岸湖口依石钟山连扎数营,内扎大木簰一座,小木簰一座,外面筑起厚厚的土城,安满大炮。在西岸梅家洲立木城两座,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设立木桩、竹签,挖起四道战壕,下面埋地雷,上面搭起三角架,三角架上钉满铁蒺藜。还像田家镇一样,在湖面挂起数道铁链,横亘两岸。
想要用火镕也是不可能的了。
一是天气太寒冷,烧烤难达到熔点。二还是天气太冷,士兵行动太迟缓。三是太平军调整了战术,专打熔链组。
湘军拿着这块鸡肋,啃也不是,不啃也不是。
史载:湘军虽百计环攻,终不得尺寸之进。
一天,石达开召集手下部将聚餐。
席间,这位时年二十三岁的青年统帅,与大家喝个面红耳赤之后,说: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很少听到石达开开玩笑,众将一齐望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