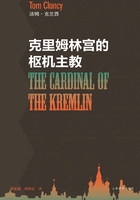早在买车前,钟铁龙和石小刚就在长益市的南区运动路旁的一条小街上各买了套四室两厅两卫房。建筑面积有一百五十六个平米。钟铁龙买了四楼的一套,石小刚买了三楼的一套,叫来力总,力总就领着他的设计师测量每间房子的长宽高,设计和装修,过了年,两人就相继搬了进去。郑小玲没上班了,长益市电工厂已停产,吃着国家救济。郑小玲在家带孩子,边指挥保姆搞卫生。住惯了小房子的郑小玲,一住进大房子就有一种辽阔草原的感觉,特意跑进商场买了双溜冰鞋,带着儿子在客厅里玩溜冰。有着四十多个平米的客厅,铺着贵妃红花岗岩,洒一点水就很滑,正好玩溜冰。母子俩没事就在客厅里溜冰。好在楼下住的是石小刚,对他们母子俩别开生面的玩法没提意见。事实上,楼下一般只有云南妹一人,石小刚基本上是在桑拿中心呆着,只有半夜里和上午在床上睡觉。云南妹不怕吵,为了抵制楼上的旱冰运动,她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没电视看她就看录像片,没录像看她就听音乐,在音乐的旋律中回想她的家乡和同学。云南妹喜欢写诗,时不时会写一首情感饱满的诗拿给郑小玲看,让郑小玲提意见。郑小玲不懂诗,只会说:“好、好、好,写得好。”
云南妹会娇媚的样子斜一眼郑小玲,用云南话说:“好在哪里呢你觉得?”
郑小玲用湖北话回答云南妹,“我不懂诗,钟铁龙的大哥是诗人,下次我把你的诗带去,让他点评下,我再告诉你。”
云南妹一笑,“钟铁龙的大哥是诗人?”
郑小玲说:“不是,是教语文的老师,写过一些诗,有些诗还在报刊上发表过。”
云南妹兴奋了,问:“钟铁龙的大哥叫什么名字,看我以前读过他的诗没有?”
“钟唤龙。”
云南妹马上检测她大脑的记忆库,就跟拼命回忆某个人似的,但那个仓库中储藏的诗人里没有钟唤龙这个名字。她摇头说:“我好像没读过钟唤龙的诗。”
郑小玲一笑,“我也没读过,他大哥在诗界好像没什么名气。”
云南妹见郑小玲不懂诗,就拿录像来看。云南妹喜欢看恐怖片,一个人又害怕看,便上楼和郑小玲一起看。两个女人看恐怖片看得非常紧张,看完后就等着各自的男人回家。云南妹说:“我要是男人就好了,我就不会老呆在家。”
郑小玲说:“下辈子吧,下辈子我们都做男人。”
云南妹没事就上楼来逗钟万林,买了很多东西给钟万林,今天给钟万林买件衣服,后天给钟万林买双鞋子,大后天又买一个玩具给钟万林,再后天又搂着钟万林上街买东西吃。云南妹是那种热情、率真、爱幻想又爱交往的女人,还是个身上所有的细胞于新陈代谢中都在生产爱的女人,她必须把这些爱用完才舒服,不然就浑身别扭。
郑小玲说:“你这么爱孩子,就跟石小刚生一个吧?”
云南妹听了一笑,“不正努力吗?”
运动路上有一家儿童玩具厂,儿童玩具厂当街,一栋楼上下三层,那是儿童玩具厂的全部。儿童玩具厂是一家大集体工厂,因生产的玩具一点也不新鲜,早十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等到钟铁龙留意到它的存在时,儿童玩具厂早停产四年了。儿童玩具厂的一旁有家面馆,钟铁龙有天早上在这家面馆吃面,儿童玩具厂的厂长也在吃面,面馆老板就笑着问厂长厂里的情况,厂长叹口气说:“要散了,工资都发不下去了。生产的娃娃和小熊,没孩子玩了。”
面馆老板问:“那是为什么呢孙厂长?”
孙厂长又长叹一声说:“现在的孩子都去玩变形金刚啊汽车火车啊和玩打得响的枪了。哪个还玩娃娃啊积木啊这些简单的玩具?”
面馆老板说:“那你不晓得生产变形金刚啊汽车啊什么的?”
孙厂长摇头说:“哪里来的钱啊?要转换产品就要投资,没有几百万是不行的。”
面馆老板说:“那你还不如把厂房租出去,可能还能租一笔钱。”
孙厂长说:“早一向有一个人找到厂里,想租我们的厂房做旅社,还有一个人想租厂房的下面一层开饭店。但租金都太低了,他只肯出五万一年。厂里有一百多人要吃饭,每个月光给职工开工资就是一万多元,一年没有十五六万是不行的。”
钟铁龙盯了眼孙厂长,孙厂长五十来岁,长一双青蛙似的鼓眼睛,秃了顶,露出一个光亮亮的赭色额头,这额头里装的不是快乐而是困窘。钟铁龙记住了孙厂长的模样。
这天上午,钟铁龙把本田雅阁停在玩具厂的破大门前,下车问传达室的一个老头,“请问你们孙厂长办公室在几楼?”
传达室的老头扫一眼钟铁龙,“三楼。”
钟铁龙就上了三楼,他走进厂长室时,孙厂长正在那儿大喊大叫地打电话,孙厂长放下电话,望着走进来的钟铁龙,“你有什么事?”
钟铁龙一眼就认出了他是那天在面馆吃面的孙厂长,便说:“我找孙厂长。”
孙厂长拿不准他来的目的,“我是孙厂长,你有什么事?”
钟铁龙递上一支中华香烟给孙厂长,“我想租你们的厂房。”
孙厂长打量他一眼,“我们的厂房很贵的,至少要二十万一年。你租得起?”
钟铁龙说:“我可以坐下跟你谈吗?”
孙厂长忙指着靠窗的藤椅,“坐坐坐。你准备租它干什么?”
“开餐馆,”钟铁龙没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也有可能是搞别的行当。”
钟铁龙跟孙厂长说了将近一个小时话,进来一个中年妇女,中年妇女的脸上挂着微笑。孙厂长向钟铁龙介绍说:“我们厂的刘书记。”
两人握手,孙厂长对刘书记说:“他想租我们的厂房开酒店。”
刘书记“哦”了声,刘书记不关心这些,问孙厂长说:“走吧?”
孙厂长和刘书记要去医院看一个病人,那是个老工人,患了肺癌,快死了,孙厂长和刘书记觉得应该去医院看看。钟铁龙对孙厂长说:“那我晚上请您吃晚饭,您有空么?”
孙厂长没有手机,但有叩机,他把自己的叩机告诉钟铁龙。“你打我的叩机吧。”
钟铁龙下到一楼,打量着这栋破旧的产房,他眼里出现了这栋楼装修后变成很热闹的情景,一拨拨的人拥来消费,钱像水一样流入了他的口袋。他看了眼街对面,对面是一栋新落成的二十层楼的金圣大酒店,他想他的桑拿中心一开业,金圣大酒店的客人不潮水一般涌来了?到时候怕是门都挤烂呵。他开心地想。他真的很烦躁,账上现在有五六百万,如果不重新投资,那是放在银行里变水。做别的行业,他没把握,他决定在运动路上开一家既唱卡拉OK,又洗桑拿的娱乐城。他把车开到银城大酒店,直接进了自己的长租房,拿起厚厚的《史记》啃读。下午四点多钟,他从梦里醒来,出了身冷汗,因为他梦见丁建倒在地上的情景,还梦见丁建一头血地抓着他的胳膊,要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去。在这个可怖的梦里,血不但在丁建头上流淌,还流到了他手和衣服上。他醒来后,首先看自己的手,手上没有血,又看衣服,衣服干干净净的,便奇怪地想他怎么会梦见一头是血的丁建?丁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跑到他梦里来?他呆呆地望着窗外,那个七岁的走在送葬队伍里的他,又出现在他脑海里,那个他的脸色是苍白的,穿着姐姐给他做的宽大的衣服。他驱赶掉这个童年的记忆,打了孙厂长的叩机,十分钟后孙厂长回话了,钟铁龙在手机这头说:“我开车来接您?”
孙厂长说:“那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