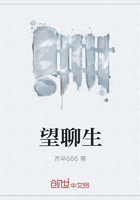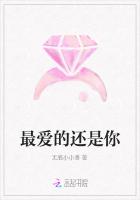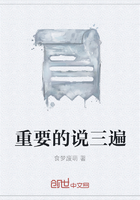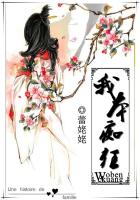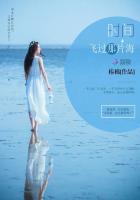哈哈——第二卷闪亮登场!小象将会努力在故事情节、悬念和可读性方面加以改进,绝对不会再出现以前那种一连好几章平铺直叙的情况了。各位读者拭目以待吧——小象会给大家一个不同的第二卷!
——————————————————————————————————
南京应天府,皇宫御书房。
大明皇帝朱元璋批改了一个下午的奏章,正在靠在龙椅上闭目养神。
惨白的冬日透过玻璃窗有气无力的照在大理石地面上。房间一角的火炉里散发出过大的热量,让一身棉衣的老人有些吃不消:“把窗户打开。”
两个小太监在总管公公王充的示意下,将两扇窗户稍稍的打开了一些。看着王充的小动作,朱元璋眉头一皱:“你个老奴才!以为朕是病秧子么,叫你开个窗户都这么小心!”
王充连忙跪下:“陛下的身体就是大明子民的倚仗,奴才们怎么敢有半点疏忽。前几日皇太孙过来的时候还特地吩咐老奴要好好留意陛下的身体,别太过劳累。”
听过王充的话,朱元璋沉默下来——他想起的,不光是自己的孙子,还有这个少年的父亲,五年前病死的太子朱标。这父子两人都是一个脾气:饱读诗书、温文尔雅、守礼孝顺、礼贤下士、宽厚仁慈……
在江南儒林和朝廷百官的眼里,朱元璋是一个马上打天下的开国皇帝,他处事果断,英明神武,重武事而非文官。而先太子朱标和现在的皇太孙朱允文则是可以与汉代的文、景二帝相提并论的守成之君。
面对朝野众人的一片称赞颂扬之声,朱元璋的心里却有着更多的想法:自己的这个孙儿文才风liu,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无论在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很好的声誉。同时拥有了朝中多数重臣的支持和江南儒林的声援,在自己百年之后,他登上大位似乎已经是注定了的事情。
可是,事情真的会这样简单吗?自己当年一手在北方册封的几个藩王二十多年来镇守边疆,屡败外犯,战功显赫。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他们的势力是越发的坐大了。自己这个父皇还在的时候,他们自然不会有不臣之心,如果是朱标登基,他们也无话可说。不同于前朝的父子相残,由于马皇后的宽容和仁爱,朱元璋膝下的子女十余人感情都非常融洽,加上朱标的宽厚、随和但是不忧柔的性格,各位弟弟对这个大哥都十分的敬服。可是,这个被自己和天下子民寄予厚望的太子居然早早的就病逝了,留下一个弱冠之年的孙子来继承这万里江山。面对一个长于诗词歌赋而不习弓马刀枪的侄儿,朱元璋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们能够继续安安份份的在北方的苦寒之地呆下去——中原的花花世界,南京城里的金龙宝座,谁不想自己一人独揽?
退一万步来说,就是燕王、宁王、晋王他们安分守己。朝中的文臣和允文又能够对他们放心吗?现在聚集在允文身边的那几个大臣、儒生如齐泰、方孝儒、黄子澄之流,整日里自诩有管、鲍、诸葛之才,时时鼓吹削藩、罢兵、尊儒,动则就给主战者扣上“靡费粮饷、残暴不仁、穷兵黩武”之内的大帽子。
自己百年之后,就是这样一群人来辅佐新帝治理江山?朱元璋苦笑着摇摇头,自己的身体日渐虚弱,他似乎已经听到了先行者在向他召唤。想想当初纵横沙场时,身边的岌岌人才,再看看现在朝中的衮绲诸公,这又何尝不是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嘲弄呢?
考虑良久,他终于提起了精神:“传旨……”
东宫,皇太孙住处。几个禁军侍卫被远远的打发到一边,书房的门口被两个小太监看的死死的,闲杂人等根本就无法靠近。
书房正中坐着的,正是在朝野之中“文才风liu,礼贤下士,颇有贤名”的皇太孙朱允文殿下。
在他面前的,是江南儒林的几位楚翘:齐泰、黄子澄等人。
“殿下,这是日前北平刚刚送来的洪武三十七年镇北军钱粮预算。”黄子澄将一份奏折交到朱允文手里:“在他们要求明年朝廷下拨给镇北军的款项增加两成,而河北以及关外三府的税收,燕王希望能够减少一半——说是今年北边的鞑子闹的太厉害了。”
“不行——”看看皇太孙没有表态的意思,齐泰道:“今年江苏、浙江、福建三省也多次被倭寇进袭,充实南方沿海的兵力防御倭寇才是当务之急,这些钱还指望着北平的税款呢!要是免掉这一项,明年户部就揭不开涡了——”
“那——两位先生以为此事该如何是好?”朱允文文才风liu,但是对于这些银钱粮草之事却是一窍不通,只能听从两位“大贤”的“教导”
“殿下放心——下官等早有对策——”黄子澄胸有成竹——在朱允文这里只不过是走一个形式而已。
就在朱元璋和朱允文苦心积虑的时候,远在北平的朱隸也在和以谢源为首的一干官员们不断的谋划、争论着。
“王爷,这个计划绝对不行!”财务司长姚泰手里挥舞着几张纸,头摇的像波浪鼓一样:“按照这个计划实行的话,至少要把镇北军的军饷节流三分之一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手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银两和物资。”
“是吗?”朱隸的眼睛紧盯着墙上的那张大地图:“军务司的看法如何?”
“回王爷!”军务司的司长周平也是老镇北军的军官出身,现在虽然是一身官服,可是依旧是腰杆挺的笔直,站在那里就像根标枪一样:“下官认为这个计划完全是纸上谈兵,要是照此执行的话,镇北军和北平就全完了。”
“你也不同意?”朱隸笑了,他直起身,看着大厅里的官员:“有没有人认为这个方案可行的?”
大厅里一阵喧哗,在座的十几位大小官员都对这个计划表示了反对。
若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这样的场面一定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是忤逆犯上的行为。但是早年深受项还影响的朱隸对于属下这种丝毫不留情面的反驳并没有太多的不满或愤怒。“既然两个关键性的部门都不赞成这个计划。那么,把你们的理由说出来!”
两个司长几乎同时想要开口,但是发现别人想要说之后,又都停了下来。看着两人谦让的样子,朱隸不禁好笑:“行了,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谦让!周平先说!”
“回王爷,军务司拿到这个协议之后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要是按照这个协议上附带的方案在边境上一次性修建如此多的城寨的话。要想守住这些城寨,每处至少需要一到两个营的步兵,加起来十二处就要六到七万人,而且这些城寨分布在近千里的边境上,相互之间很难相互支援,很可能被敌人分开吃掉。总之,这个计划的规模太大,已经超出了我镇北军的能力范围。”
朱隸有些头痛,下面的人说的都是实话,这一点他很清楚,但是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能够扭转战事被动局面的机会放在他面前,他是在是不想放弃。自己的这个北平都督看起来风光无限,可是谁又知道这里面的无数艰辛!镇守北疆二十多年以来,自己每年有半数以上的时间是在居庸关或是关外三卫渡过的。
长年的征战,自己这个燕王的光辉已经把当年的“项爷爷”盖过了。大明的疆域日渐扩大,可是自己却走向了项还的老路:朝中众人——包括自己的父皇和侄儿对自己的疑虑也就越大。除了父皇之外,包括那个只知道吟诗作画的皇太孙在内的朝中文臣们几乎把他看成了比蒙古人和高丽人更可怕的敌人!
午夜梦回之时,他都会想起自己还是个懵懂少年的时候,跟随着那位被鞑子畏惧的称之为“项爷爷”定北公项还,越马扬鞭的快意岁月。朱隸还清楚的记得项还那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豪迈情怀。斯人已逝,难道大明失去了这位“天降英才”之后,就不能再重振雄风了吗?
朱隸使劲摇摇头,把这个荒唐的想法赶出脑海。他把目光转向财务司长:“你的理由呢?”
“回王爷,下官的理由和周司长的理由相似”姚泰走上前:“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一座小型的城寨光是营建费用就要挤占一个步兵旅半年的经费。何况计划上面是要求建造十二处之多,加上驻军的军饷、粮草和运输费用,不用蒙古人打过来我们就先完蛋了!而且明年北平都督府的财政预算已经上报给南京了。就算现在我们临时申请增加这一笔款项,皇上也点头了,户部的老爷们也拿不出这笔钱。”
看着部下一脸的无奈,朱隸忍不住用手揉着额头:“难道就要本王白白放弃这个大好的机会不成!”
“王爷,下官们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周平连忙出言相劝:“下官这里还有一份计划,是下官和军务司的几个参谋一起写出来的,可能对王爷有些用处!”说完,他从身后的参谋手里接过一根短棍,在地图上指点起来:“限于我镇北军的财力物力,下官认为应该放弃在边境上全面铺开的想法,转而在我军和蒙古军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也就是南和林以北、以东设置三到四个据点。而且这些据点规模起初不能太大,以免引起蒙古人的惊觉——”
“等等!”朱隸抬手止住周平的话:“前面的话本王都能理解,可是规模不大的话,驻军怎么抵挡蒙古军的攻击?”
“这个不用担心,这些据点最远的离南和林不过三百里,北和林附近的骑兵一天就能赶到。蒙古人要不被我军发觉,南下的兵力就不能太大,这样的话,两个营的驻军完全可以借助工事顶上两天。”
“且容本王再思量。”就在朱隸权衡考虑的时候,政务司司长郭远很突兀的插嘴了:“周司长,您刚才指点的那几个据点位置是在哪里?能让我再看看么?”他那双原本眯缝着的小眼睛现在瞪的远远的,虽然不大,却是冒着绿光。
今天的人怎么一个个的都有些不正常啊?朱隸心里嘀咕着,示意周平给郭远指一指据点的大概方位在那里,他相信自己的部下不会无缘无故出来的搅局的。
郭远很仔细的看了周平指出的地方,然后又在地图上趴了老半天才站起身:“王爷,周司长的计划只要稍稍修改一下就绝对可行!”他很肯定的对朱隸说。
“哦——”朱隸半信半疑:你一个文官,能懂的什么战事?不过抱着姑且听之的想法,他还是让郭远继续说下去:“为什么?”
——————————————————————————————————
第二卷小象努力写的好一些,大家是不是也表示一下?有票的就投一票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