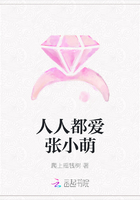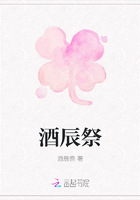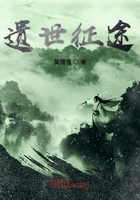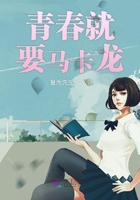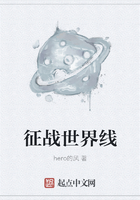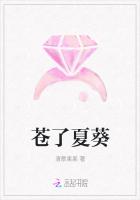三河坡,本是个岌岌无名的小地方,除了常年在此地放牧的牧民之外,没有人会将自己的目光在这片平凡的几乎没有任何特点的小丘陵上多停留哪怕是一秒钟。
大明洪武三十八年秋天的这一场大战,让三河坡一夜之间进入了了天下人视线的焦点。
半个月之间,大元朝几个强势部族和朝廷联手组成的十万大军被不到三分之一的镇北军击败。
久经沙场的老将白音莫率领的土默特部和托克托部损兵折将,一路遁回老巢。大元名将贵利赤带领六万大军长途驰援,苦攻镇北军阵线三日不克,死伤籍枕。第三日下午,镇北军一次反击便将元军击溃,死伤万人,元将额勒伯克、阿拉坦在乱军中负伤而逃。
敌军溃退之后,燕王世子朱高炽率领部下骑兵长驱三百里,斩首三千余级,俘虏近千人,战马牛羊不下八千头。一时之间,虎父出虎子的佳话传遍全军。加上某些有心人的可意宣扬,燕王父子俨然已经成了大明北方当仁不让的擎天柱,领路人。
无论是大元还是大明,大战的结果都是出乎绝大多数的意料之外的。当元军快速战败的消息四散开来的时候,它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估量。
北和林,贵利赤的战败让和林成慌乱成一团。草原民族向来是全民皆兵,平时放牧战时杀敌,损失三万五万人并不是什么无法弥补的大损失——大不了往草原深处躲个几年休养生息就是了。
但是,从中原退回的北元已经和历史上的其他游牧势力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朝堂上,几个实力强劲的部族联合起来,将其他势力完全排除在了中枢之外,这种垄断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和其背后的部族武力的基础上的。此次为了抗击朱棣北上,各家都派出了自己的基本班底,虽然相对于整个北元的军民基数而言,损失的数字并不是太大,但这已经使几大部族赶到了统治基础的动摇。
几个掌握实权的重臣在朝堂上吵成一片,为了是战是和还是走争执不休。最终,还是丞相驴儿说服了脱古思贴木尔:马上派遣使节南下求和,只要能够维持住局势,可以作出相当程度上的让步——包括他本人取消帝号,改称可汗,向大明称臣!
八月底,脱古思贴木尔的使节在镇北军即将北归的时候走进了朱棣的大帐。
面对元帝预料之外的大让步,朱棣心里并不痛快——抢占的土地被默认,还要归还被掠夺的汉人奴隶,赔偿战马牛羊,这些他都能够作主。但是脱古思贴木尔要放弃帝号称臣的举动却让他实实在在的赶到了一种来自背后的威胁。
元帝称臣,镇北军囤积重兵的理由也就少了一半,自己把持北方三省财权军权的理由也就少了一般。更重要是的:此战,新开辟的疆土不下千里,交由哪个人来管理?从前几年父皇将弟弟朱樉封到原本为北平都督府协理的山西太原府来看,十有八九还会有个小弟被封到自己的身后,一旦将来南方有事——朱棣不想去想这些,但是却不能不想。
虽然忧心,但是朱棣还是很有礼貌的打发了贴木尔的使节,在保证不会擅开战端之后,使节被朱棣派人护送入关,一路朝南京而去。
……
八月底,大宁卫指挥使璞英率步卒五千人赶到已经大大北移的边境线上,迎接凯旋归来的北征军。在璞英身后,从关内征集的八千民团和两万民夫正带着巨量的粮草建材源源不断的赶来,他们将在入冬之前抢修出至少八个边防堡垒,成为北方边境上的第一道有力屏障。
虽然还在敌人的领土上,但战事已经平息,加上朱棣有意宣扬军威,震慑四方。故此大军回师的步伐就显得有些缓慢了。好在这次周边的大小部族已经被朝廷的速败吓破了胆,让项凌觉得回程的路途更多的像是路途而不是行军了。
项凌已正式结束了行辕参谋的职务,发表为行辕直属骠骑旅副统领,朱高炽在之前的追击战里很好的执行了谢源为他设计的战术,杀敌甚多而损失不大,在军中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但是他的目标已经不在军中了,朱棣听从了项凌和谢源的建议,现在朱高炽已经很少在骠骑旅露面,成天跟在父亲身边,重新抄起了贴身书办的职务,开始政务方面的学习。朱棣已经透出口风,回到北平之后,朱高炽就将交卸骠骑旅统领的职务,至于接任人选——不言自明。
重新回到父亲身边的朱高炽已经从某些渠道知道了项凌和父亲在攻克三河坡之后的那段对话和之后的举动。虽然他和项凌都很有默契的没有提起过这事,但是朱高炽已经将此牢牢的既在了心里。
十天之后,已经等到有些心慌的璞英终于等到了凯旋的大军。没有锣鼓喧天的喜庆——新堡垒的构建已经热火朝天的展开了。大队不及修整,在补充了粮草物资之后继续南下。
……
告别璞英之后的第八天,部队已经到达山西东北三百里的地方,朱棣将一直率部拱卫行辕的项凌叫到大帐:“你对山西的情况知道多少?”
项凌沉吟片刻:“知道的不多!”眼下山西已经不是边防前线,他对山西的那点子了解多半还是在威远堡的时候听往来塞北的山西商人说出来的一鳞半爪。
“和本王去那儿看看如何?”项凌听得出朱棣并不是在开玩笑:“那儿也是个要紧的地方啊!”
两天之后,原本应该向东南行进的朱棣突然带着自己的亲卫旅和骠骑旅六千人马出现在山西北端的口北城下。口北卫守军惊惶失措,引出一城的骚动,紧接着又有官民拦路投书,状告守将杨解勾结地方官员包庇走私,掠夺民间并杀人灭口。朱棣大怒之下将守将杨解解职押送北平议罪,而宣化知府在半个月之后也被撤职查办。
借着,朱棣打着点验地方卫所军,查办军务的旗号领直下太原。
太原成为晋王朱樉的封地已经多年,但是山西作为北平都督府下辖的三省五府之一军务依旧要接受北平都督府的指导。现在朱棣未的圣旨便直下太原,虽然事发突兀却并不算无礼——谁叫当初皇上给了北平都督“临机专断,总领北方军务”的大权呢?
……
此时,镇北军北征,击溃十万敌军而还的消息已经在朝野上下传开,在有心人的操控下,燕王爷打败十万鞑子兵,逼得鞑子皇帝逊位求和的消息也在民间传扬开来——其速度甚至还要比官方的捷报更快上一些。
朝堂上,朱元璋对儿子的战绩在高兴之余更带着一些担忧——虽然自己对儿子还是抱着相当的信任,也能够理解他想要在平定辽东之前打造一个相对安定的后方的盘算。但是他也知道,朝中的大臣们——尤其是聚集在皇太孙身边的年轻一代绝对不愿意看到北方藩镇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朱棣虽然大胜,但是他却是在没有上报朝廷的情况下擅自出征的——光凭这一条,就足够抹去他此战带来的一切荣光。
但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除了几个素以“忠直清正”著称的言官御使之外,以往一向对北方藩镇军持不友好态度的几个主要文官派别却出奇的没有发出任何不适宜的声音。
当朱元璋正在盘算着这些“栋梁”们又在谋划些什么的时候,一道众臣联名签署的奏折解开了朱棣的一切疑问——宁王朱权即将成年,但是还没有选择好封地,现在北方的疆域大大拓展,正好可以将宁王殿下封到北方新开拓的疆土上,为父皇为兄长分担一部分责任。
虽然知道这样做会让朱棣反感乃至感到被威胁,但是朱元璋稍稍犹豫,还是在奏折上批下了一个大大的“好”字。
虽然现在朱元璋对自己的儿子能够投之以绝对的信任,但是毕竟将来继承地位的不是棣儿的兄长而是他的侄儿——年长、战功卓著深的军心且毫无牵制的叔叔对上一个年轻根基尚浅的侄儿,朱元璋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四儿子会没有任何的不轨之念。既然如此,那么在自己还能够掌握全局的时候为孙儿铺平道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但是此时,身为此举最大受益人之一的皇太孙朱允文却又犹豫起来——从上次项凌一案中朱棣的反映来看,四叔虽然桀骜,却并没有不臣之心。宁王就藩一事虽然是皇爷爷首肯的,但是朝野内外每个人都已经将这笔帐算到了自己这些人的头上——要是真的因此而激怒了四叔,那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