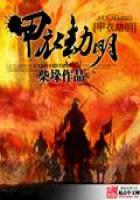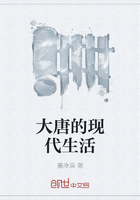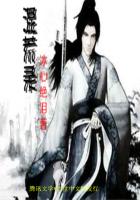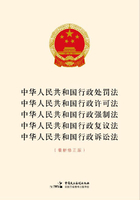虽然是堂堂燕王殿下的世子出行,朱高炽也不想弄得太铺张——毕竟南京城里的皇上也是三令五申,要各地的藩王贵胄们要检点自己的言行,不要作出违背大明律法,骚扰民间的事儿来。
于是,朱高炽带着项凌的百余骑兵和一队运送寿礼的车马,一路偃旗息鼓朝南边行去。说是偃旗息鼓,其实也就是省掉了打前站和后站的人马,这样对地方上的惊扰相对能少一些——不过话又说回来,朱高炽是执掌了天下第一强军镇北军的燕王朱棣之子,就是他本人再低调,只要地方上知道了消息,哪里有不主动巴结上来的?
为了避开地方官员源源不断的应酬,朱高炽借口急着进京,一路上轻车急进,遇到大城市都是穿城而过,这样就省下了不少的功夫。没几天功夫,大队人马就到了开封。照着朱高炽的老规矩,他们并不在开封城里逗留,而是从城东一个不大的渡口过了黄河,直接南下。
开封附近的黄河已经十分的平缓,宋以来,黄河从上游夹带而来的泥沙与日俱增,长年累月的淤积使得黄河已经成了一条地上的悬河。现在不是雨季,黄河水流平缓,南来北往的行人车马经过架设在河面上的浮桥过河,比用渡船要方便的多。
朱高炽虽说是轻车简从,但是毕竟是一方藩王的儿子,加上给朱元璋准备的礼物和大小行李,身边的人马车辆怎么也不少了。众多的车马和人员要过河,那条狭长的浮桥估计得全腾出来才行。好在这浮桥也是当地官府负责修缮的,两面桥头都有差役驻守,项凌拿着文书腰牌找到正在吃饭的差役头,要他快些安排一下。
知道了项凌一行人身份的差役头儿点头如捣蒜,几句话的功夫,几个差役将浮桥两头一拦,没多久桥上就空的差不多了。恰在此时,桥上接近对面的地方出了点小小的茬子——大概是车上的东西太过沉重,一辆马车在就要上岸的地方压断了几块木板,沉重的车身压得一侧的车轮深深的陷入塌陷的空洞里。赶车的车夫急得满头大汗,鞭子在拉车的健骡背上抽的“啪啪”响也无济于事。
见队里的马车出了问题,已经上岸的车队领队急急忙忙的带着副手跑回来,围着已经陷下去的马车和车夫一起紧张的商量起来。比这些人更加紧张的,是守在浮桥两端的差役们——虽然这队马车也有些来历,而且过桥的时候这些人还给了他们一笔不少的茶水钱,但是这些和燕王殿下的世子比起来又算的了什么呢?
急得上火的差役头领飞跑到马车旁加入了车队众人的讨论——在确定短时间内不能将沉重的马车挪开之后,他强硬的向车队的领队下令:要是在一刻钟之后浮桥还是不能畅通的话,“就把这辆招瘟的马车推到黄河里去!”
将满载着贵重物品的马车推下河自然是绝对不行的,但是他的话确实让车队里的人用最快的速度解决了车子的问题——二十几个膀大腰圆的护卫从陷下的马车边上一直排到岸边,将车上的东西一箱一箱的传递到岸边的空地上。卸空了的马车很轻松的被拉了出来。
“要是我们家大人没——” 车队领队看着岸边再次装货的马车,嘴里很是不满的嘟囔着。
“这都是那家的啊?这么沉,不像是官府的车队,也不像是镖局和商队?”项凌站在对岸看着这一切,很有些不解的问身边的一个差役。
“这啊——”那个差役年纪不大,满脸的机灵像,听到身边的官爷有话问自己,赶忙凑上来殷勤的为他解说:“这是给一位刚卸任的知府大人运行李的车队。”
“行李?”项凌自言自语:“那家的大人能够有这么多的行李啊!看样子还都是挺贵重行李!”
“呦——大人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那差役很有些不信的望着项凌:“这位知府大人的任所是在山西大同府,不要说别的,光是大小煤矿每年孝敬的银子就不下几万两,就是除去上下的打点,几年下来腰里的银子也绝对少不了。”
项凌哑然……
过了黄河之后,沿途的景色渐渐的有了些分别——村庄越来越多,河流分布的更加密集,水田逐渐取代了旱地。虽然从理论上而言,水稻的单位产量要比小麦更高,但是按照项凌的观察,沿途的农民生活的要比北平那边窘迫的多。项凌知道,这是因为南方的税赋比北方高的缘故。
其实,按照大明律,南方和北方的税赋比例基本上是一致的,真正的区别在于地方上擅自增收的加赋——因为发达的工商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北平都督府辖下的各级衙门并不需要向农民征收过重的赋税,加上上级的监督有力,即便是有一些加赋,增收的也不多;而南方各级衙门似乎并未受到像样的监督,虽然正式的税收不多,但是各级衙门加收的加赋却足足是正税的好几倍。
……
一路行军,一路观察,朱高炽一行人很快来到了南京附近。
一路上朱高炽轻车简从,但到了天子脚下,应有的礼数还是不能少的。虽然看起来人人数少了些,但是当随员们打起半副亲王仪仗的时候,在前方开路的项凌等人还是很有些精神一振的感觉——人家都说相府的奴才七品官,自己是堂堂亲王世子的亲卫,又该怎么算呢?
南京毕竟是京师,警戒森严,虽然项凌他们在离南京很近的时候才打出旗号,但是南京礼部在十天之后就已经派了个书办来联络。过了两天天,驻扎南京郊外的禁军大营派来了联络官——京师周遭,天子脚下,要是没有禁军的许可擅自行动的话,那就是谋逆的大罪了。
让项凌感到意外的,是此次禁军大营派来的联络官居然是朱高炽和他的老熟人,说起来此人还是项凌的前任——他就是剽骑旅中军营的第一任管带李少忠。故人相见自然是分外的亲热,尤其这故人还是一起上过战场,共过生死的战友。
在长江北岸的一个小镇上,一行人停下歇息一日,准备将全套的行头打理起来好进京面圣。趁着这难得的机会,朱高炽和项凌摆下一桌酒席,和李少忠好好叙一叙离别两年以来的别情。
酒过三巡,三个人都有了些醉意,说话的范围也渐渐的超出了日常的范围。从旧日的共同经历,到分别之后的各自境遇再到镇北军和禁军之间、北平辖下和南京辖下的的区别等等——
说到动情处,李少忠带着三分醉意和七分意气的对朱高炽说:他很想念在镇北军服务的日子,至少不会受这样那样的窝囊气。
“你一个堂堂的禁军将军,又是将门之后,还能有什么人能给你受气啊?”项凌很有些不解的问道。
“唉——”李少忠愤愤的摇摇头:“南京不是北平,这里的事情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项凌还想追问下去,但是被朱高炽用眼神制止了,两人不再追问李少忠,反而频频向李少忠劝酒。心中不愉的李少忠不胜酒力,很快就醉倒了。这时,天色已经快要黑了。
走出满是酒气的房间,朱高炽伸了个懒腰,对项凌道:“天色还没黑,咱们俩出去转转吧?”说完,不待项凌回答,转身就朝后面的马厩走去。
小镇不大,朱高炽一鞭子下去,吃痛的战马一溜烟的跑出了镇子。项凌心中叫苦——虽然此地是在天子脚下,但是朱高炽的身份实在是太过敏感了些,要是此时他出了什么意外,自己无论如何都是负责不了的。而现在自己再去叫人跟上已经来不及了,只能自己飞身上马,紧随在朱高炽之后。
朱高炽并不想甩开项凌,而且经过两年沙场历练的项凌骑术早已是今非昔比,片刻之后就追上了朱高炽。一会儿之后,朱高炽在一处小河湾边停了下来,绕过一片密集的灌木丛,项凌隐约看到在河边的一片沙洲上,一个披着蓑衣带着斗笠的渔夫正在那儿垂钓。
见到那渔夫,朱高炽落下笑脸,放缓了脚步,轻轻走了过去。项凌想要跟上,但是被朱高炽制止了:“在这儿守着,别让无关的人靠近。”
项凌知道朱高炽绝非临时起意,便老老实实的远远守卫着。因为距离太远,项凌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此时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项凌甚至连那个渔翁的面貌也看不太清楚。只是依稀记得那人脸色蜡黄,长着一张马脸,而项凌映象最深刻的,则是那人的眼光十分的锐利,仿佛能够洞穿人的心腹。
过了大约一刻钟,朱高炽才结束了和那渔夫的谈话。项凌发现,朱高炽的神色似乎凝重了许多,他虽然很想问问原因,但是看朱高炽不想多说此事的样子,项凌知道,自己最好当作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