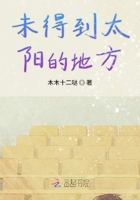支遁(313-366)字道林,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人,或曰河东林虑(今河南省林县)人,是东晋高僧,般若学五家七宗之一的即色宗代表人物。支遁的家世史籍阙载,我们只知道他本世家子弟,适逢乱世,先游于山林,“隐居余杭山,深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经。”(《高僧传》本传)二十五岁出家。先在吴(今江苏省苏州市)白马寺修道,因注《庄子》,作《逍遥游论》,弥声士林,在清谈场上骋舌。后在吴立支山寺,作八关斋,并采药游乐山水。又欲移入剡,因谢安招,又与王羲之交游,留住灵嘉寺,不久投迹剡山(今浙江嵊县)立沃洲小岭寺行道,跟随学道者常百余人。晚年移驻石城山(今浙江省绍兴东北),立栖光寺,游心禅苑。晋哀帝即位,慕其德音,频招入京,止于东安寺。淹留京师将近三载,上书哀帝告辞归山,终于余姚山坞中,并葬于此,名士郗超为之作序传,史学家袁宏为之作铭赞,周昙宝为之作誺文,深受士林钦敬。
支道林是一个具有高僧与名士双重身份的人,在僧俗两界都有很大影响。他贯通儒、道、释各家,尤其是阐释佛理,明显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因此为听众所喜闻,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人物。他虽然外貌很不雅观,但是才气纵横,论辩迅疾,辞采华茂,为士林与僧人共戴。他在东晋名士中交游广泛,与众名士重臣王洽、王濛、刘惔、殷浩、许询、孙绰、郗超、王敬仁、何次道、谢安、王羲之、袁宏等过从甚密,特别是他在京城瓦官寺等处讲《维摩诘经》等大乘佛经,宣传居士思想,听众中就有许多名士达官权要,而支道林与许询一为法师,一为都讲的精彩演说,令人喜悦惊绝,因此对佛教在士林的传播贡献甚大。他是一个很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可以说是高僧中名士的杰出代表,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游于三教。支道林对儒、道、释三家均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努力沟通融合,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也给传统的玄学注入了新的生机。道林于儒,历代鲜有人言。其实,他的儒学根基不浅。我们可以在他的文章诗歌中,随处看到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文字典故。如他的《上哀帝书》:“洋洋大晋,为元亨之宇。”“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前者的“元亨”来自《周易》,后者是孔子的原话,出自《论语》。他甚至在言谈中脱口而出的也是儒家经典中的文句:“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王坦之),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世说新语·文学》)其言自然是孔子成语。如此烂熟,可见其对儒家典籍的修为,加之以特别出众的领悟能力,其于儒学可谓登堂入室者矣。我们在他的《释迦文佛像赞》中,可以看到他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来歌颂佛祖,简直就是以儒释佛。他还深于儒家的人伦之理。“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陨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这种笃于同学之深情,儒门中遗教也。
他在玄学修养上也是名士翘楚。以清谈才能而言,他与当时最负盛名的殷浩互有短长,不相上下。殷浩长于《才性》之学,而支遁谙于《庄子》之学。谢安认为支遁之玄学超过嵇康:“郗嘉宾(郗超)问谢太傅:‘林公谈何如嵇公?’谢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问:‘殷(殷浩)何如支?’谢曰:‘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然亹亹论辩恐殷欲制支。’”(《世说新语·品藻》)这样的评价应该是有道理的,将支遁的玄谈才能与殷浩并列,已经属于东晋最高水平,自是无疑。孙绰《道贤论》将七位道人拟配“竹林七贤”,其中就是把道林与向秀相配,可见其玄学水平超出嵇康不是谢安一人的看法。自“竹林七贤”开始,玄学从重《老》转向重《庄》,但是《庄子》之学,经向秀、郭象注释后,鲜见新的发展。“《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世说新语·文学》)玄学在东晋之初,延续西晋的老调重弹,徒骋口舌之才。至支道林出来,以儒、道、释兼通之才阐释《庄子》,注《庄子》,作《逍遥游论》,超越向、郭之学,才使玄学获得生机,一时成为士林清谈的宗主。名士王濛感叹道林:“寻微之功,不减辅嗣(王弼)。”(《世说新语·赏誉》;《高僧传》亦记录此语,“寻微”作“造微”,意同)
支道林在佛学方面,著述甚丰。他辨析分判三乘之异同,不仅宣讲,也作有《辩三乘论》。(《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大唐内典录》卷三均有著录,已佚)他对当时人们疑惑的问题也有辨疑析难之功。俗称《大品》的《放光般若经》与名称《小品》的《道行般若经》之间的关系,时人以为既然详略不同,那么应该是佛涅槃后从“大品”钞出“小品”。支道林作《大小品对比要钞》进行比较,然后又作《大小品对比要钞序》阐述两者关系,使迷惑众人的疑难释然。作《妙观章》(现在残存的《即色游玄论》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阐述“色空”之理,解说般若性空:“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表明物质世界(“色”)没有自性,故本质上是空的;但是毕竟为色,因此与“空”并不完全相同。他还注《安般守意经》《四禅》等佛教经典,作《道行旨归》《圣不辩知论》,属于三藏中的“论”,系统阐述自己的佛学主张,以时间先后言,也是我国僧人自造佛论之先驱。与汉末魏初的《理惑论》比较,自然晚了许多,但是《理惑论》毕竟只是谈释家与儒、道的异同,并不是专门的佛学“论”著。与僧肇的《肇论》比较,精深自然难敌,然而时间明显早于《肇论》。
支道林在我国思想史上的绝大贡献在于融通三教,虽然还不是非常精密深微,但是开拓之功是不可磨灭的。他沟通儒与释。东晋名士孙绰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周、孔救时弊,佛教明其本耳。”(《喻道论》)其人就是长期追随支遁的信徒,他与许询都自称是道林的徒弟。道林在《与桓太尉论州符求沙门名籍书》中说:“邦乱则振锡孤游,道洽则欣然俱萃。所以自远而至良有以也,将振宏纲于季世,展诚心于百代。”其意虽为佛教而发,其形迹显与儒家的有道则显,无道则隐之理味同。《释迦文佛像赞》云:“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仁义有本,道德之谓也。”“导庶物以归宗,拔尧孔之外犍,属八德以语极,罩《坟》《索》以兴典,掇道行之三无,络聃、周以曾玄,神化著于西域,若朝晖升于旸谷,民望景而兴行,犹曲调谐于宫商。”在他的陈述中,简直儒、道、释三家一体,没有根本的区别。至于其《即色游玄论》与《逍遥游论》等都是佛教与道家思想融通的妙文,不必细说。
第二,才藻惊绝。在禅林,支遁也是才气超人。于法开为僧中高人,《名德沙门题目》云:“于法开才辨纵横,以数术弘教。”他的口才辩论能力甚好。但是他与支公争名,结果退居剡县:“法开初以义学著名,后与支遁有竞,故遁居剡县,更学医术。”(《高逸沙门传》)他欲与支遁争锋,结果败下阵来,只得遁迹山林,并且改学医术,可见道林的佛教义学与辩论之才。《世说新语·文学》记录一次支道林与许询、谢安、王濛在王濛家言咏,大家共对《庄子·渔父》阐述,结果支遁第一个完成,作七百余字,敏捷超人,而且“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其才之秀、之捷、之丰确在众人之表。
确实,支道林以敏悟为著。《高僧传·支遁传》言曰:“幼有神理,聪明秀彻。”“卓焉独拔,得自天心。”说明道林天资聪颖,捷悟过人,再加之沉思研想之功,自然更加超人一筹。他之解经也是与众不同,粗略章句,善标宗会,得其要旨,所以谢安誉之曰九方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骏逸。他与文学才子许询共同讲解《维摩诘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每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措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竟两家不竭。凡在听者,咸谓审得遁旨,迥令自说,得两三反便乱。”(《高僧传》本传)这一段极为精彩的描述,生动地再现了支遁与许询师徒互相巧妙设难解疑的功夫。其阐理之清晰明了,令幽微难明之奥旨明白昭示;其所阐之艰深难彻,令众人已解已明之义理难言难说。其悟理之才,言理之才,不亦惊人么?《支遁别传》云:“遁神心警悟,清识玄远”。其实,支遁自己非常欣赏捷悟之才。《世说新语·赏誉》载:“林公云:‘见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不住,亦终日忘疲。’”“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这种相惜之情尤其能见道林天才卓越,敏悟超群。
支道林的文学成就,也是相当突出的。他的诗歌创作,今存十八首,为东晋沙门作家之首,即使与东晋其他作家相比,也毫不逊色。其诗歌,题材广泛,既有赞佛之作,也有咏怀之诗,还有山水之吟,为谢灵运山水诗之前驱,较慧远还略早。清人沈曾植说:“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又说:“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支、谢皆禅玄互证,……谢固犹留意遣物,支公恢恢,与道大适矣。”(《王壬秋选八代诗选跋》)他作有许多佛像铭赞,以中国传统的文体歌颂菩萨佛祖,实为后代佛教文学的滥觞。他的文集,《隋书·经籍志》录为十卷,梁十三卷,在有晋一代属于著作很丰的文学家了。他的文字雅洁,辞采丰茂,对偶工整,骈俪秀美。
第三,游心禅苑。支道林三教并蓄,交融不悖。不过,他之归宗还是在禅苑。他“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高僧传》本传)看来他不仅因家庭渊源,而且幼年即对佛理早有夙慧因缘。在出家前,“隐居余杭山,深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经。卓焉独拔,得自天心。”(同上)他似乎天然地对佛经禅理有卓然的领悟能力,而且在出家前就长期覃思深究般若经典,根基深固。他研习佛经,人生大部分时间在体味禅理般若之学,一生弘法无数,不辞辛劳。当时人对般若经的大品《放光般若经》与小品《道行般若经》的关系不明,他先作《大小品对比要钞》,对大小品作具体的对比,然后作《大小品对比要钞序》,详细分析两者关系,认为大小二本不异:“大小品者,出于本品,本品之文,有六十万言。”“二本之不异统,致同乎宗”。廓清了混淆的是非,而且在瓦官寺等处宣讲《小品》,演义佛经要旨,听者僧俗两道均喜闻,大乘般若之学,赖以宏大。他先后立支山寺、沃洲小岭寺、石城山栖光寺等供自己与欲修佛道者研习弘法之所。他虔诚修道,与僧徒立《座右铭》,严格恭敬礼佛习经;晚年虽得哀帝多次敦请,不得已入京讲论《道行般若》,“白黑(僧俗两界)钦崇,朝野悦服。”(《高僧传》本传)获得很高荣誉,但是他的心灵仍然在于禅苑,因此向哀帝上书,表达自己殷切的归禅之意:“盖沙门之义,法出佛圣,雕纯反朴,绝欲归宗。游虚玄之肆,守内圣之则,佩五戒之贞,毗外王之化。……贫道野逸东山,与世异荣,菜蔬长草阜,漱流清壑,褴褛毕世,绝窥皇阶。……上愿陛下,时蒙放遣,归之林薄,以鸟养鸟,所荷为优。谨露板望路,伏待慈诏。”(《高僧传》本传)其归山养真,修道弘法之心,可谓深挚矣!当时佛教界还没有必须素食的规定,但是支道林自动实行蔬食。他对于佛教的贡献,东晋名士郗超《与友人书》中评价道:“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实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同上)
第四,以鸟养鸟。支遁热爱自然。他热爱自然之物,喜欢以自然态度待自然之物。“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世说新语·言语》)他还喜欢养鹤:“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锻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新语·言语》)爱好马,爱好鹤,乃道林喜欢自然之物;马之神骏,鹤之特立,都甚有神理。爱之常人亦或有之,只是常人无道林之神韵。他之爱物,纯然爱其自然之性。爱鹤,本欲常处而赏其韵致,但是当他“以鸟观鸟”,发现其凌霄之志未泯,毅然养护其翅,令其回归自然,去自己的所在;他之爱马亦如此,蓄养马匹而从不骑坐,只是爱观马之神骏之姿而已。支道林更爱与大自然亲近,甚至融入自然之中。早年,他出家前,以及出家初期,都是在自然之中,学道悟理,所以一出山林就以思理精警,征服了整个士林。他与孙绰等二十四人同期在吴县(今苏州)为八关斋,斋毕,“众贤各去。余既乐野室之寂,又有掘药之怀,遂便独住……登山采药,集岩水之娱”。(《八关斋会诗序》)众人去而独留,以尽山水之乐。晚年长在石城山行道,因晋哀帝的多次征聘,不得已出东山留京师,但是不久就要求归山:“遁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还就岩穴。”(《高逸沙门传》)《高僧传·支遁传》还全文收录支遁的《上哀帝书》,言辞恳切,回归大自然之情甚为殷勤。自然之旨意,首先是以各种事物自身的特性去理解它,并顺其特性与之相处相安,如果违反其本性,强求其按照人们的意愿生活,那么其物必然生活于一种违反其自然本性的状态之中,如以锦衣玉食喂养鸟儿等宠物便是。其次,各种事物的本性千差万别,就是同一种物类,也会因其个别性而具有不同于其同类的特性,因此尊重其个性,不要求其按照主体的愿望生活,完全任凭其自己按照个性去自由地生活,那就是“以鸟养鸟”。支遁以其深刻的思想与冥通人情物理的睿智,提出了契合万物自性的理论主张,并以自己的实践践行之。
第五,至人境界。支道林的人格理想,其特异之处在于他明确提出了一个人格标准:至人。他的“至人”境界,比较集中地表述在他的《逍遥游论》(残篇)中,因此要把握和理解“至人”的人格思想,必须具体细致地分析其《逍遥游论》,并且与郭象和向秀的《庄子·逍遥游》注的相关文字对比,再参稽道林其他的有关论述。其辞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屝。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屝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向秀与郭象的《逍遥游义》:“夫大鹏之上九万,尺屝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从两者对《庄子·逍遥游》的阐释来说,向、郭之说明显有违庄生原意。因为庄子的逍遥游境界是无待,绝对地不依凭外在条件,也没有任何的内在欲念,完全彻底地自由自在,而他们认为“各任其性,苟当其分”就逍遥了,而且在《庄子》里,大鹏与小屝等等均不是属于达到逍遥境界的。以理论之,庄子的逍遥游,主要是存在于精神状态的,显然缺乏现实性的境界,因为任何人,只要存在于现实中,就不可能完全“无待”。支遁的阐释,一开始就抓住了庄子理论的核心:“明至人之心”!鹏之游因为对客观条件的依赖很大,因此“失适于体外”,不能逍遥是由于受制于外在的条件。屝之没有达到逍遥游的境界,是因为其内心有思想观念等等局限,笑话大鹏,乃心存欲念也。其实,真正的逍遥游应该没有任何的限制,游之空间无限(“游无穷于放浪”),游之条件无限(“物物而不物于物”),游之心念无有(“遥然不我得”)。如果有了一定的欲念,那么必然会满足于自己的欲念所求,虽然快然,但是并不逍遥,仅仅如饥者吃饱了一餐饭,渴者喝足了一次水一样,满足度是有限的。只有完全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也没有任何内在欲求的行为,才是真正的逍遥游。而这逍遥游更多的是属于精神状态,也就是说,只有精神上彻底摆脱了对外在条件的要求,摆脱内心的欲求,那么人(至人)就是无觞爵而能饮,无粮而能餐了。若有欲念,肯定要受到来自内外两方面的限制,不仅难以很逍遥地游,即使游了也不会逍遥。
支道林的“逍遥游论”是更加确切地对庄子《逍遥游》的阐释,超越了向与郭,也超越了以前其他庄学者。他所论述的境界,与佛教的禅境有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绝念弃想,摆脱人对物质的依赖和束缚,也抛弃精神上的任何企求与欲念。这样,人真的可以达到无可无不可的境界。然而,至人毕竟只是现其理想的精神状态,而非现实相。他在《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中说:“夫至人也,览通群妙,凝神玄冥,灵虚响应,感通无方。”又说:“是以至人顺情以征理,取验乎沸油,明小品之体,本塞群疑幽滞,因物之征验,故示验以应之。”在他看来,至人应当是无所不通,无所不明的,而且他的大化之能,到处可以见到,随时都可得到印证,使普通人能够感觉到。这个“至人”显然具有佛教的特色,在佛经里,菩萨或者化身为菩萨的佛祖,他已经“天眼通”,能看见千里之外的事物,也能看到事物内部任何不显露于外的情景,自然他也感应得到群情群心,他们需要证验时,立刻就给他们看到验证的事实。这样的至人,确实有“观音菩萨”般的神通。他在《释迦文佛像赞》说:“夫至人时行而时止,或隐此而显彼,迹绝于忍土,冥归于维卫,俗徇常以骇奇固以存亡而统之。”这个至人是形迹不定的,行动无常,显隐无常的,那是由于其神通广大决定的,也是与常人常事迥异之处,但是世俗之人总喜欢以可以看见的实际形迹,或者明白知道其消亡等具象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其特征。因此自然只能感到不可思议,惊骇奇怪。这里的“至人”是佛教化的人格形象,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也是他的“至人”理想人格。所以,支遁的“至人”境界,既具有庄子的彻底自由的特质,也具有佛教的神通广大的特点。是一个与凡庶迥然不同而又不完全离开众人的人格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