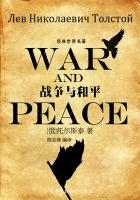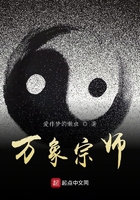老哈河绕村而过后,就向着更开阔的大厂方向奔流。冬天,不下雪的日子,我们便从老哈河上滑冰去学校,十多里的路程仿佛缩短了许多。我们要绕开高高的冰包和没冻死的河眼,温度稍高一些的早晨,河面上漫着一层浅水,也要绕开。那天河面有雪,我们只好从路上走。
玉兰和凤霞正在村口等着我们。路上还没有人走过。春燕在前面开道,我们循着她的脚窝跟在后面。雪不时钻进鞋里,脚脖子一阵冰冷,渐渐地就木了。先前,脚趾头还像针在扎,后来也没了反应,动一下脚趾,心里别提有多别扭。我们走着,互相说的都是和上学第一天不相符的丧气的话。
我爹对我还算好呢。三丫儿更倒霉。小学没毕业,我爹就不让她念了。一个丫头片子,念那么多书有啥用?我爹谁也不瞅,蹲在炕头,双手捧着粗瓷大腕,他哧溜喝一口水,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这是他一贯的观点。对我念书,他还能容忍的主要原因,是那张旗里的奖状。这样的奖状,整个大厂公社只我一个人有。我拿着奖状回家的那个下午,设在我家的牌局正热火朝天。一进屋,满屋的旱烟味就径直冲我的肺管灌进来,令我不住地咳嗽。一圈人挤在我家土炕上,我爹靠窗台坐着。他手里抓一把牌,嘴里叼一根很粗的旱烟卷,以至于他说话时必须歪着嘴:快点!到底吃不吃?他眯着眼,样子滑稽极了。拥在炕沿边的几个人,都冲着桌子伸长脖子,目光兴奋而期待。有人还时不时指点几句,引得炕上的人发出不满的抗议。
那天,“小先生”也在。“小先生”是我们老哈河的秀才,过年时每家的对联都他写,红白喜事,他是万万不能缺的人物。我奶奶死时,所有的“文告”都是他用毛笔在黄纸上写的,古文多,白话少,没人看得懂。我疑心那是鬼话。那天,他把我的奖状拿过去,细细看了一回,立刻伸出大拇指:“二丫儿真有本事!”又转脸对满屋人说,“这丫儿将来准保有出息!”
屋里的人一个个传看我的奖状,念过书的,没念过书的,都赞赏我。轮到我爹了。他依然叼着烟,半眯缝着眼睛,煞有介事地在奖状上盯了半天,好像他识字。我等他说点什么,谁知他抬手向后一挥,那张奖状就轻飘飘地落在了他的身后。随后,我爹眼神夸张地盯着桌子上的牌,小心翼翼地抓起一张,一路把牌拖到跟前,好像拖着千斤重的东西。刚才还对我赞不绝口的那些声音,一下子消失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我爹的样子吸引过去,专注而渴望。我爹一脸神秘,偏偏不把牌翻过来,直到人们快要松懈的时候,他才突然发一声喊:起,带响声的!随即把牌一翻:可牌面上却是整齐鲜红的四道杠!我爹定定地看着手里的牌,满眼失望,然后放下,习惯地搔一把后脑勺,努力挤出一片笑容。别的人则释然地呼出一口气,仿佛躲过了一劫。土炕上,空气重新活跃起来。
从那天以后,尽管我每天早晨起来检一筐牛粪的任务没变,可我爹的脸色好看多了。一次,他对几个邻村来的人说:“我们二丫儿作文在全旗得一等奖呢。”正好我进屋,他立刻停住,神态有些讪讪,端起带豁的粗瓷碗喝了一口水,随后把目光移向一边。我迈进屋的脚又退了出来,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怨恨。在老哈河,我爹好吃懒做出了名,家里穷得叮当响,就算我考上高中,他拿什么供我?
直到邻村的王玉柱和马小军从身边经过,我才闭住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