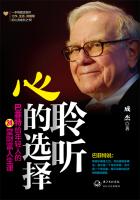在火车上,一位打工回家的民工告诉我说,一想起当时的窘态,心里就凉凉的,当时做出那样的举动,自己也感到意外,一起打工的同伴常用它作为说笑的亮点。事情不大,一两句话就可以交待清楚。这位民工在救助西部贫困学生的捐助活动中捐了自己的3块钱。同伴们笑他,捐3块钱不如不捐,和城里人一出手就是好几张百元钞票一比,就矮下去了。再者说3块钱能够做什么?它几乎做不了什么,和零没有什么区别。
他当时衣服口袋里有5元钱,留了两元钱买晚上的两个馒头和一份咸菜。他说着说着脸就红了。他不掩饰地说,他有3个孩子,前两个是女孩,第三个是男孩子,后两个是偷着生的,被罚了不少钱。孩子多,支出也多,在生活相对较富裕的冀中地区,他依然过得很清苦。他的大女儿上初中,交不上书费和学杂费,打算不上了,到私人做鞋的小厂里挣钱……
这个世界穷人还有很多。用物欲的眼光,我们看到了命运的不公,看到了难以置信的穷困。不过,我们只要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方式,就能够看到他们的富有……正如一棵树,它不是很高大,也不能够开出艳丽的花,它贫穷而孤寂地站在荒原上,构成了别样的、耐人寻味的风景。
我无言以对。对于她那次的古怪举动,我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离奇解释,却没想到自己最终从她手里接过的是一份如此美丽的礼物!
一株常春藤
●卡罗尔
我结婚时用的花束是我自己精心挑选的,每一种花都有着不同的含义:蓝色鸢尾是我丈夫最喜欢的花,白玫瑰象征着纯洁的爱情,而预示我俩将白头偕老的是几根翠绿的常春藤。
婚宴上,我一只手端着一杯香按酒,另一只手拿着一束鲜花,在人群当中来回穿梭,不时与朋友们聊上几句。尽管忙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我心里喜滋滋的。突然,有一只手搭到我的肩膀上。我转身一看,是我婆婆的一个朋友,我与她只匆匆打过几次照面。她手里捏着一根常春藤。
“这是你跳舞时,从花束里掉下来的。”她说。我向她道了谢,正要伸手去接常春藤的时候,她又说了一句:“我想自己留着,你介意吗?”听到这样的请求,我十分惊讶。我还没有抛花呢,况且我几乎不认识这位女士,她要我的常春藤干吗?不过,明天一大早,我就要出门去度蜜月了,到时肯定不会带着这束花同行的。我也不打算婚后留着它。再说,我今天收到的鲜花已经够多的了。
“没关系,您留着它吧。”我微笑着说,为自己能大度地对待这个古怪的请求而欣慰。这时,音乐声骤然响起,我离开了她,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人群。
几个月后,有一天,我们新居的门铃响了。我打开房门,来人是在婚宴上向我要常春藤的那位女士。这一次,我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我心里嘀咕:她究竟想干什么?
“我有一件结婚礼物要送给你。”她说,随后递给我一个枝叶婆娑的小花盆。突然之间,我明白过来了。“这是你在婚礼上掉在地上的那根常春藤,”她向我解释,“我把它拿到了家里,修剪了一些枝叶,然后替你栽在了花盆里。”
原来,多年以前,在她自己的婚礼上,有人为她做了同样的事。她说:“我那株常春藤还在生长着,每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就会记起自己结婚的那个日子。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尽我的力量,为其他新娘栽种一些常春藤。”
我无言以对。对于她那次的古怪举动,我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离奇解释,却没想到自己最终从她手里接过的是一份如此美丽的礼物!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株来自婚礼上的常春藤就一直蓬勃生长着,它的生命力比我栽种的任何其他室内花草都要长久。正如这份礼物的赠送人所预料的,看一眼它那翠绿明亮的叶子,就能勾起我对身披白色婚纱、许下结婚誓言那一时刻的甜蜜回忆。
这件事已经过去快20年了。如今,我已是3个儿子的母亲。总有一天他们也会长大结婚。那时,作为新郎的母亲,我会建议在新娘的花束里放几根常春藤,而且我知道,常春藤将剪自何处。
他是一头倔驴,认死理,嘴拙,可有一手焊工绝活儿。
心声
●李开忠
热烈的掌声中,他登上讲台。黝黑的脸涨得紫红,他舔舔嘴唇,瓮声瓮气地说:“同志们,我……我……”
数不清的目光,像无数支闪光的银箭齐刷刷地射向他,早已准备好的话语被吓得无影无踪了。
“哈——”人群发出了善意的笑声。他也苦笑笑,用袖子擦擦额上的汗。
“小王,别慌。”刘厂长在后排座上轻声提示道,“就说说你是怎么连续两天两夜抢修加热炉的。”
这话题对他并不难。有次加热炉管道漏水,为了多轧钢,没等炉温降下来,他便穿上用水浇湿的棉袄,第一个冲进了炉内。等同志们硬把他架出来时,棉袄已经快烤干了。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家劝他别进去了,可他喝了一肚子凉水,又冲进炉内。
“好,我说……我说……”
无数只眼睛闪烁的火苗,像无数支气焊枪喷射的火焰。困窘扼住了他的嗓子。“小王,你说说那次抢修转炉烟罩吧。”刘厂长又在后边轻声提示。
那次烟罩严重漏水,转炉被迫停止冶炼。他站在3米多高的平台上焊补。炉体辐射热像万颗钢针般刺着他,黄烟、灰尘像舞动的纱巾紧裹着他。他一会儿仰焊,一会儿立焊,一会儿用小锤敲去渣皮,检查焊缝。他坚持着干了两个多小时才焊好,可是,他却虚脱了,是工友把他背下了平台。
“好,我说……我说……”
无数支气焊的火苗变成了一片电焊的闪光,照得他脑际苍白一片。
“小王,要不,你说说脑子是怎么转的弯吧。”钟书记端了一杯开水放在他面前。
他是一头倔驴,认死理,嘴拙,可有一手焊工绝活儿。有段时间,不知怎的,他认为当官的好人不多。他不像有的人发牢骚,骂大街,可就是工作起来没有劲。有一次,班长安排他干一个急活儿,他眼皮动,身子却不动窝。班长急了,扣了他当月奖金。他拿起焊枪,在班长头上砸了个大疙瘩,为此,受到了厂纪处分。他憋闷,借酒浇愁,喝得胃大出血。他躺在病床上,脸像白蜡,脑子里一会儿热,一会儿凉,生命危在旦夕。厂领导紧急决定,从市里请来了专家为他动手术,救了他一命。
他颤抖着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开水,霎时,一股热气从心底慢慢升起,早已准备好要说的话冲到喉咙,他抓起话筒,大声喊道:“厂里拿咱当人看,咱就像牛一样干!厂里拿咱当主人,咱就豁出命来干!”
哗!掌声像雷鸣一样响起。
孩子僵硬的小手慢慢地伸了出来,像要吃力地抓住些什么东西,接着,眼睛也睁了开来,静静地盯住母亲的脸。
爱就一个字
●佚名
我听说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冬天,一个叫云架岭的地方下起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几乎将所有的沟沟坎坎夷为平地。恰在这时,一个3岁的聋哑孩子突然得了一场怪病,高烧烧得像一块火炭,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急坏了他的父母
在村里能请到的医生一个个摇头而去之后,他的父亲试探地对妻子说:“那……只有到县医院去看看了。”
前来探望的村民一齐将吃惊的目光投向他的脸。从云架岭到县城,至少要走100多里路,其中60多里是险峻异常的山路,平常人走都提心吊胆,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下山,谁都觉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弄不好连一家三口的命都得赔上。
可是,做妻子的听了丈夫的话,近乎绝望的眼神一下子又有了亮色,迅速用棉被包住毫无知觉的孩子,抱起来就往门口走去。年轻的父亲顺手拎过一把铁锨,紧紧地跟在后面。
乡亲们说不出什么话来,默默地让开一条道,目送着他们一头扑进漫天的风雪。接着,他们看见那位年轻的父亲紧走几步赶在妻子前头,用铁锨在没膝深的雪地里铲出一条路,让妻子稳稳当当地往前走。
不知是谁带了个头,大家轰地一下追了上去,夺过他手里的铁锨,轮流在前边开道,一直护送他们到了60里外的山下。
然后,丈夫借了一辆手推车,推着妻子和孩子连夜往县城赶去。
他们到达县城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这时,孩子通体冰凉,连心跳也消失了,县医院的大夫无比遗憾地告诉他们:“晚了,给孩子……找个好地方吧!”
丈夫沉默半晌,嗫嗫嚅嚅地对妻子说:“到这一步了……咱们……把孩子送走吧……”
神情木然的妻子仿佛受了电击一般,猛地一抖:“不!我不丢!娃还活着,我要跟娃一起回家……”
无论人们怎样规劝,执拗的母亲总是咬住这一句不放,丈夫只好叹了口气,又推起妻子和孩子,艰难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雪依然在下,天地间混沌一片,似乎要将这对悲痛欲绝的小夫妻彻底地淹没。走着走着,坐在手推车上的母亲索性解开自己的衣襟,将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仿佛要用自己的体温将冰凉的孩子暖热。每过一会儿,她就要温柔地拍拍怀里的被卷、梦呓似地呼唤几声:“娃乖乖,妈带你回家……”丈夫机械地走着,汹涌的泪水从眼角流下,在脸上结成长长的冰凌。
“要么,你哭出声,让心里好受些?”丈夫说。
妻子摇摇头,她哭不出声来。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走了多少路,天黑了又明了,雪小了又大了,忽然,手推车上的妻子一声惊呼:“他爸,快看,娃动了,娃活了!”
丈夫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妻子和孩子一起揽在怀里。果然,孩子僵硬的小手慢慢地伸了出来,像要吃力地抓住些什么东西,接着,眼睛也睁了开来,静静地盯住母亲的脸。
“妈!”孩子的嘴唇一动,轻轻地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声音。
可怜的母亲头一歪,稀泥似地瘫了下去,幸福地死在丈夫的怀里。
直到现在,这个孩子仍然只会叫一个字,那就是——“妈!”
可这个字的分量,却比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要重。
这一下,村民们惊骇了,继而是深深的感动。他们抢了小伙子的货,小伙子理应怨恨他们,即使他们吃了那种淀粉被毒死,也是罪有应得。而小伙子不惜以下跪的方式来请求他们别吃这些工业淀粉,拯救他们的生命。这样的爱心,这样的善良,这样的胸襟,让他们羞愧难当,感动不已。
善良那根弦
●方冠晴
印度北部有个村庄,叫格依玛村。这里土地贫瘠,人们生活穷困,连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村民们也想改变现状,苦于找不到生财之道。
离格依玛村不远有一条公路,属于那种简易公路,路况不算好,经过那里的车辆经常发生事故。有一次,一辆装载着食用罐头的货车在那里翻进了沟里,一车罐头滚落一地。司机受了伤。拦了一辆顺道车去了医院,那些货物无人看管。格依玛村的村民见了,就将那些罐头偷偷地运回家,一连好几天。家家户户都有罐头吃。
这件事给了格依玛村民以启发,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完全可以靠路吃路了。所以,他们经常到那条公路上转悠,希望再有运载食物的车辆在那里出事故,他们好乘机有所收获。
但车祸的事毕竟不会经常发生,眼瞧着一些运载食物的车辆来了又去,他们一无所获,这让他们很不甘心。所以,他们想到一个主意,晚上,趁公路上没人的时候,他们就拿上工具,将公路的路面挖得坑坑洼洼。这样一来,车子在那里出事故的情况就多起来。即使车子在那里不出事故,但路况太差,所有经过那里的车子行进速度都非常缓慢,这给了格依玛村民以可乘之机,他们会跟在车后,趁司机不注意,偷偷地从车斗里拿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
这件事在渐渐演变,起初,他们只是偷拿一些食物,后来,其他货物他们也拿,好送到市场上去卖一些钱,发展到最后,他们就不是偷偷地拿,而是明目张胆地抢了。一时间,格依玛旁边的那条简易公路成了最不安全的路段,警察局每个月都会接到好几起关于车上货物被抢的报案。
警局出动警力破案,他们在现场抓住了两个正在抢货的格依玛村民,给这两个村民量刑。但这样做并没有威慑住其他村民,反而让村民们学会了作案时更加隐蔽更加机警。他们的作案开始有组织并有序起来,有专门的人负责望风预警,抢到货物后就拿回家藏起来,或者更换货物的包装,让前来搜查的警察找不到物证。一时间,警察束手无策。
当地政府也想了很多办法,想让格依玛村民放弃哄抢货物的不道德和非法行为,引导他们走上正途。无奈,格依玛村民已经从哄抢货物中尝到了甜头,他们习惯了这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
哄抢货物的事在格依玛村附近屡屡发生。那年冬天,司机们因为从格依玛经过经常丢失货物,所以,许多司机选择绕道行驶的方式避开了格依玛路段,这样一来,格依玛村民好几天没有收获。这一无,终于有一辆货车从那里经过。车上装的,是一袋袋磷酸脂淀粉,一种工业用淀粉。格依玛村人都没有什么文化,在他们看来,淀粉就是粮食,可以制作成各种各样好吃的食物。当下,大家就一拥而上,抢走了二十多袋磷酸脂淀粉。
司机见有人抢了他的货,便停下车,跟在抢货人的身后往格依玛村追。这样一来,反而给了其他格依玛村人机会。他们不慌不忙地将车上无人看管的所有淀粉搬了个空。
小伙子追进村子,就请求村民将他的货还给他,格依玛村人哪会将到手的“粮食”轻易地交出来,他们都不承认拿了他的东西,并采取了应对措施。
小伙子百般恳求都没有作用,他只得告诉村民们,那些磷酸脂淀粉不是普通的食用淀粉,而是工业淀粉,有毒,吃了会死人,他们拿去了也没有用。
小伙子说的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