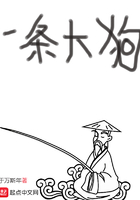乔装易容的许长栋夫妇由山阳郡登船,走水路经江南河进入长江,转道向西往鄂州而去。
开挖运河虽然劳民伤财,但运河贯通后南北交通确实方便了不少。往常走陆路前往鄂州少说也要小半年时间,如今在水上潮平风正,一路上畅通无阻,只用四天就已经进入长江。
桂云庄久处内陆,风袭月坐不惯船,在船上呆了十多天,颠得头晕眼花,上吐下泻。许长栋疼爱娇妻,带着风袭月在蓟州提前下了船。
蓟州码头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沿江叫卖的小贩和往来搬运的脚夫挤在一起,叫声喧天,许长栋好不容易带着风袭月挤出码头,晕船的风袭月脸色已经变得一片煞白。
码头外有一间临江的小酒肆,往来的船夫和货商都趁船靠岸时来喝两杯酒,歇一歇脚。许长栋夫妇走进酒肆,捡了一张僻静的桌子坐下,许长栋心疼地倒了一碗水,道:“来,喝点吧。”
风袭月伸手推开茶碗,道:“喝什么水?小二,来一壶酒!”小二高声应了一声,端上一壶酒和几碟粗糙的小菜来。
许长栋皱着眉头道:“你的脸都白成这样了还能喝酒?”
风袭月笑着摆了摆手,道:“下了船就没事了,这一路在船上颠得我头晕眼花,早就想喝点酒提提神了。”说着倒了一碗酒一饮而尽。
许长栋也不争辩,倒满酒和风袭月对饮起来。
夫妇二人正在对饮,酒肆门前忽然传来一阵喧哗。
“没钱还想吃饭?快滚快滚。”店小二扯着嗓子老大不耐烦地道。
“阿弥陀佛,贫僧只想化一点残羹剩饭,请施主行个方便。”一名中年僧人双掌合十,向店小二恭恭敬敬地道。
许长栋看这僧人身上的僧袍破破烂烂,满面风霜之色,心中一动,低声道:“这和尚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风袭月道:“这是少林寺的高僧,曾经到过桂云庄。”
许长栋这才想起风袭月接任桂云庄庄主时曾经有两位少林寺的和尚道贺,这名和尚就是其中之一。
门口店小二和僧人仍在争执,风袭月低声道:“这位大师衣着简朴,面有饥色,看上去是个苦修的僧侣。若不是咱们不方便表露身份,倒应该请他饱餐一顿。”
僧人似乎是饿得很了,实在不愿意走,仍在苦苦哀求化缘。这时店里忽然冒出一个声音:“臭和尚,快滚快滚,别在门口叽叽歪歪,打扰大爷喝酒。”
风袭月循声望去,见一个粗豪大汉坐在店内,恶狠狠地瞪着和尚,吃了一惊,道:“怎么他也来了?”
许长栋顺着风袭月的眼光望去,一口酒险些喷了出来:“谢映登?”
那粗豪大汉面生得很,他旁边一个瘦小身形的华服汉子却是熟面孔,正是西路绿林总瓢把子,如今已经归附天机悬的谢科谢映登,不知他为什么也到了蓟州。
风袭月转过脸不再看谢映登,低声道:“把头埋低些,等风波一过就结账走人,咱们俩都不是他的对手,千万别露出痕迹。”
僧人宣了声佛号,道:“这位施主,贫僧只想化点斋饭,无意打扰施主,请莫见怪。”
谢映登身边的大汉拍案而起,道:“让你滚就滚,废什么话?”
僧人不再理他,仍转过头专心向店小二化缘。店小二不耐烦起来,抄起一根木棍就打,边打边道:“快点走,别影响大爷做生意!”
那僧人左躲右闪,木棍一下都落不到他身上,风袭月低声道:“看来这位大师身手不低。”
僧人并不还手,一边躲闪一边道:“施主,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就算不愿施舍也犯不着动手啊。”
谢映登身边的大汉再也忍耐不住,喝道:“秃驴,你找死!”拍案而起,一纵身冲到门外,挥拳就打。
酒肆中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物有,见有人动手,非但没有人退避,反而一哄而上看起了热闹。
许长栋摸出几文钱放在桌上,一拉风袭月,道:“正好,咱们趁乱快走吧,免得留下来多生是非。”
风袭月紧了紧腰间的长秤,道:“不忙,谢映登归降朝廷应该呆在京城,这时无缘无故出现在蓟州肯定有什么玄机,咱们且看他一看。”
大汉挥拳击向僧人,僧人肩膀一抖,侧头闪过拳锋,大汉收势不住,踉跄着往前冲了几步,僧人伸出脚在地上一勾,将大汉绊了个嘴啃泥,围观的酒客发出一阵哄笑。
僧人连忙扶起大汉,道:“施主小心,可摔到哪里没有?”面上神色倒显得十分关切。僧人身上的僧袍很长,刚刚伸出一脚又很隐蔽,看上去像是大汉自己发力过猛摔倒在地上一般。
风袭月低声道:“那位大师腾挪时身形雄健,隐隐有龙虎之形,武功只怕远非你我二人可比。”
谢映登一个闪身,如同鬼魅般蹿到酒肆外,眯起眼睛盯着僧人,缓缓道:“原来是少林寺的大师。”
僧人看到谢映登的身法,脸上闪过一丝凝重,行礼道:“施主有礼。”
大汉被僧人从地上扶起来,愣了一愣,一把推开僧人,见谢映登也来到店外,胆气顿时壮了起来,骂道:“狗秃驴,刚刚是大爷脚滑,现在就把你大卸八块!”
许长栋低低冷笑了一声,道:“谢映登归降朝廷,朝廷官员就是这般做派么?这样的人在我绿林道中也容不下,那位大师武艺不弱,咱们不如和他联手,就在这里将谢映登杀了,给桂云庄中死难的兄弟报仇!”
风袭月轻轻握住许长栋捏紧的拳头,道:“别冲动。少林寺是江湖白道,和绿林一向没什么交情,那位大师未必会帮我们和朝廷作对。再说就算能杀了谢映登,也一定会引起官府的追捕,你别忘了咱们还有要事在身。”
酒肆门口围观的人群中忽然闪出一个白衣翩翩的后生,张开双手挡在僧人身前,道:“这位师父和和气气的,你凭什么要打人家?”
风袭月眉头一皱,道:“这下可热闹了。”转过头看着许长栋,只见许长栋双拳紧握,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咬紧的牙关里蹦出两个字:“阿光?”
白衣后生正是齐遥光。齐遥光带着齐二从京城出发奔赴鄂州,走的是渭水支流,无巧不巧,也在今日到达蓟州,路过酒肆门前看到大汉要动手殴打一个风霜满面的和尚,一下子激起了侠义之心,站出来相助。
风袭月紧紧抓住许长栋的手,低声道:“长栋,千万沉住气。”
许长栋重重地出了一口气,道:“你放心,我只是……只是猛一见到他有些心神不宁,绝不会冲动误事的。”
大汉在绿林中是横行惯了的,面子上如何拉得下来?挥拳就打了过去。
谢映登认得齐遥光,知道他是刑部的二品大员,未来的驸马爷。他谢映登自己如今没品没级,只把西路的人手挂在天机悬名下,哪里敢得罪齐遥光?连忙抢上一步,一把拉开大汉,赔笑着向齐遥光拱了拱手,道:“齐……”
齐遥光也认出了谢映登,忙挤了挤眼睛,道:“兄台,大家素不相识,这位大师若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二位,还请二位海量汪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罢。”
谢映登是何等精明的人物?听了齐遥光的话立刻明白他不愿表明身份,马上顺着他的话道:“兄台说得对,是我这兄弟鲁莽了。”拉了拉大汉转头欲走。
这时酒肆中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又有一名后生信步走了出来,团团一拱手道:“萍水相逢即是有缘,各位何必动怒伤了和气?不如大家握手一笑,交个朋友如何?”
许长栋低声道:“这又是什么人?”风袭月摇了摇头,道:“没见过。”
齐遥光、谢映登和那僧人一齐向那后生望去,见他穿了一件青布长袍,面如冠玉,眉似飞星,虽然不像谢映登那样锦衣华服,但眉眼间天然有一股英武之气。
谢映登并不将其他人放在眼里,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没有说话。齐遥光见后生气宇轩昂,心中先生出一丝好感来,拱了拱手道:“兄台说得有理,这里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各位都不必动气。”
后生笑道:“既然如此,不如小弟做东请各位共饮一杯。”说着伸出手来,将众人往酒肆里请。谢映登淡淡地拱了拱手,道:“不必了,在下还有要事在身,这就告辞了。”说着掏出一小锭碎银扔给了小二,道:“不必找了。”看了齐遥光一眼,带着大汉扬长而去。
后生也不以为意,目送谢映登离开,转身向齐遥光和僧人道:“这位兄台,这位大师,若不嫌弃就和在下一起用些饭菜吧。”
僧人看了看齐遥光,又看了看后生,丝毫没有客气,宣了声佛号,道:“那就多谢施主了。”
后生满脸笑意又看向了齐遥光,齐遥光道:“在下自己带了钱,就不劳烦兄台了。”
后生笑道:“兄台不必客气,一顿饭而已,值不了几个钱,请吧。”说着拉起齐遥光,也不管他愿不愿意,硬将他拉进了酒肆。齐遥光只好招了招手,将躲在人群中的齐二也叫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