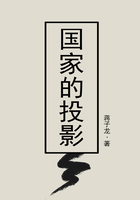心中颇不宁静,也没有了大风大浪的感觉,只是一潭平静的死水,而死水的微澜都是混浊而生涩的,实在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痛。
我坐在他家炕头,接受煎熬的洗礼,实在是对我的惩罚,我做梦都难以想到,善良是如此可欺,有人竟要把善良当做软弱来欺。
老天总归是公平的,不管是对于善还是恶。善有善的回报,同时苦涩;恶有恶的惩罚,同时享受着比针尖还微小的可怜的自作聪明的快乐。而上帝的嘲笑在这种自作聪明的头脑里注入邪恶的种子,由他的行为方式培育出贫穷的根,长出受难的叶,结出子孙不孝的恶果。他是一个恶人,对我来说不够,但他的行为对后世的影射,上帝不会原谅他,因为他违逆了道德与良心,同时亵渎了善良。
有时候上帝是邪恶的,他像猫一样喜欢玩一只将死的老鼠,我不知道我在这场游戏里是不是也充当了老鼠的角色,但我即使是只老鼠,也是上帝对我无原则善良行为的惩罚,我照样行的端走的正,而对面与我抗衡的那只老鼠却是被上帝愚弄惩罚的罪恶的老鼠,上帝把世间最可怜的自作聪明注入他的血液,令他的生活与行为常常受到世人的鄙视,我是不曾有过他那些羞于面对世人的思想,而我受到的来自于他对善良的欺负与亵渎的伤害,却是上帝对我毫无原则的善良之举最直接、最无情的批判。
人在渐渐地成长的过程中,慢慢的细化与分辩出一些真正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与邪。
我是那种成长很慢的女人,虽然我的年龄早已不是幼稚的女人,当善良被欺负心中颇不宁静,也没有了大风大浪的感觉,只是一潭平静的死水,而死水的微澜都是混浊而生涩的,实在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痛。
我是那种成长很慢的女人,虽然我的年龄早已不是幼稚的女人,但我真正的面对这个世界的人与事我还正处在青春期。可是这么多年的经历于我,就像一种煎熬,一种上帝有意安排的煎熬。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发生着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让我在这些事件面前一次次的兑变成熟。
我的心也渐渐的被磨砺出一层薄薄的硬壳,这些硬壳使我的心免受一些纤尘的干扰,但这些薄薄的壳一旦被某一稍微尖一点的微刺刺破,还是会流出一些殷红的血来。
我不停的品尝每一次血液的味道,除了恶心,除了酸,还有一股难言的血腥味。这种感觉让我害怕,我害怕自己蜷缩在他家炕头的心会突然由最初的对血腥的反感与恶心一下子过渡到对血腥味的渴望,我为自己突然的想法感到恐惧与后怕。
我不能任自己的感觉像一道滑坡一样承载着我的真性情,一次次地经历这些可怕的血腥味而毁掉自己,可是我能把握命运对我的安排与考验吗?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在同一个地方以同一个姿势一直坐着,我的腿很凉,我的心更凉,我又一次想起六年前他来向我借钱的经历……我的心越来越冷也越来越硬。冷到没有一丝笑容挤上我僵硬的脸,硬到没有一丝理由为自己曾经的善举落一滴泪。
上帝要造就一个人的成长,是不是都要这样去打磨一个人的心灵?难道仅有善良还不够是一个完整的人,还必须具备一双犀利的能直视正邪善恶的眼睛才算一个完整的人?那么我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声音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人与事啊。
有些人的眼睛是树,心是木头。有些人的眼睛是木头,心却是树,更多的人的眼睛是眼睛,心是心,只有少数人的眼睛即不是树又不是木头,是一潭死水,一潭得过且过的死水。就像他的眼睛与心。
我前后向他要了四次款,六年来就这一回,就这一个月内。是因为我非常需要,是因为我知道他有。我以为六年来没向他开过一次口,他会理解我的急迫,我以为六年来从没向他开口,他知道我理解他没能力归还的苦衷。我以为六年来这第一次向他开口,因为他有,他会还给我的。
而他硬是没给,还一次次的把我往后推,他在耍我,以为我好哄骗。
我以我心度别人,所以我一直在高看他,他以奸诈小人之心度我善良之心为懦弱可欺。当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邪念又一次在我心里响起,我终于明白了世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手,义无反顾地抡起刀子砍向对方是为了什么。
人活着,不就是争口气吗?况且连宽厚无边、仁慈无疆的佛都知道要争一炉香呢。
我有时间等待他的下一轮,只要他肯为自己的后世赌上罪恶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