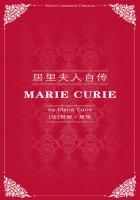五月三十日星期五
赶写一个稿子,好些天没去张府,下午去了,室内多了两把椅子,张先生说来了两个客人,刚走。问是谁,说了名字,我认识。保姆过来将椅子搬走,沏上茶。桌上有《儿郎伟》诗稿。
韩:又有改动?
张:没有,刚才来的客人,说起这首诗,翻出来让他们看了改动的地方。老王(客人中的一个)说像我这样的人,不该说“闭门补课学文化”,该说闭门谢客做学问。
韩:这老兄还是不懂诗,做学问就没这个味儿了,还是“学文化”好。我看这首诗里,就这句最好,最有意味。
张:噢,你这么认为?
韩:这是自嘲,有复归于本初的意思,说来可笑,有深意存焉。人都要学文化。这些年,还有前多少年,都是叫人学思想的。实际上,文化最重要,有了文化也就有了思想,有思想而没文化,这个思想也就难说是思想了。学文化最大的好处,不在于知道什么是对的,而在于知道什么是不对的。没文化的人,什么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赵树理的小说里,写过一个叫“常有理”的人物,就是没文化的典型。
张:我倒没想这么多。老王大辈子当记者,考虑问题直杠些。哎,我问你,你是作家,写文章的,学者和记者也都写文章,作家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韩:这真问住了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文章的流向不同。学者记者的文章是往上流的,可称为上流文章,作家的文章是往下流的,写的是普通人的事,也是让普通人看的,可称为下流文章。这只是流向不同,没有高低优劣的差异。写下流文章而能达到高的境界,就是上流作家;写下流文章又是低境界,只能说是下流作家了。
张:妙!你算什么流的作家?
韩:我是三流作家,能上流,能下流,还能横流——江河横流。这是说笑话,不过我说我是三流作家可不是笑话。九几年过年,我大门上贴的对联就是:“一级职称三流作家,四口之家六人在望。”那时儿女还没成家,盼着来年他们都找下对象,让我能看到六口之家的影子。那时说三流作家,说的是一二三的三。今天受你的启发说了这番话,往后再说自己是三流作家,就有了新的解释。什么时候刻一方闲章,就刻上这四个字。
有个事差点忘了,那天你说的那首诗,就是“典却青衫供早厨”起句的那首,回去我写了篇小文章挂在博客上,引用了这首诗,说是听你说的,你忘了作者是谁。有人见了回帖说,是元代中书左丞吕仲实的诗,收在他的《辍耕录》一书中,诗题为《闲居诗》。还给改了一个字,说第三句“瓶中有醋堪浇菜”里,浇字应为和字。后来我在网上查看,丰子恺先生也喜欢这首诗,抗战期间在桂林,曾以后两句为题,一口气画了八幅画,有的送了人,有的自己留下。
张:这首诗是年轻时记住的,什么书上早就忘了。意境好,句子平实,默念上几遍就记住了。最重要的是,不悲观,相信将来会过上好日子。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日子难过,雨湖夫人急得都哭了,我就给她念这首诗。这诗越念到后头,感情越高昂——“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等于说,挨也挨着了,轮也轮到了,会有好日子过的!
韩:是好诗,我也是念上两遍就记住了。能让人一读就喜欢,念上两三遍就记住的准是好诗。
张:这首诗不光是说家居艰难,砥砺气节,做学问也要有这种精神,耐得清贫,耐得寂寞。
韩:清贫好耐,难耐的是寂寞。一个学校出来的,在学校说不定不如你,几年天气,人家就蹿红了,你还在那黄卷青灯,老牛破车地走着,能不着急吗?
张:这就看你的自信力如何,自持力如何了。通常有了自信力,也就有了自持力了。做学问还有一条,要多跟外界接触,好处是开阔眼界,多方比照,全面认识自己,不光是认识自己的不足,还能认识到自己的足。
韩:这得要自己有真本事,没真本事越比越气馁。
张:没真本事的人不敢跟人比,要比也是往下比,不敢往上比。往下,那不叫比,叫往下出溜。
韩:在这上头,哪个人对你启发最大,印象最深?
张:叫我想想。郭宝钧这个人你晓得吗?
韩:有一段时间,我爱看傅斯年和史语所的书,对这个人有些印象。参加过殷墟发掘,当时好像负责与地方上的联络协调,后来正式进了史语所,成了考古专家。他没有去台湾?
张:你以为他去了台湾?
韩: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解放前夕,中央研究院往台湾撤退时,就史语所和另外一个什么所,全部人员和资料都迁过去了。
张:郭宝钧肯定没走。一九六三年来过山西,我们也算老相识了。我这儿有本书,也说郭去了台湾。是高增德送我的,就在那个柜子里,你取出来看看。
我俯下身子,在旁边书柜下层逐一看去,取出一本什么人的集子,说不是,又取出一本,说是。名为《思想操练》,是丁冬、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五人的“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一月出版。递给张先生,很快翻到第八页,上面有他的批注。我凑过去。
张:你看这儿,我写的——此处所言“郭宝钧到了台湾,在学术上很有成就”。据我国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词典》第一七七六页着录郭宝钧条载,郭氏生年为一八九三,卒年为一九七一,未见有去台湾的记载。郭先生也算得上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去台湾我竟无闻,真是孤陋寡闻,莫此为甚!
韩:这几个人都是我的朋友,这话也不是老高说的,他们这种对话,天南海北,随兴而谈,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还是说郭宝钧吧。你们谈话时互相怎么称呼?
张:我叫他郭先生,他叫我张主任,我一直是文管会副主任兼考古所所长。官都是拣大的叫,还要省了那个副字往上靠,单位的人都这么叫,给他介绍时也这么介绍了。个头?比我高,比我排场。河南南阳人,南阳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董作宾,就是四堂之一的彦堂,也是南阳人。就是他把郭宝钧引进考古界的。他是哪年来山西的?一九六三年还是六四年,就说是一九六三年吧,也七十岁了。住在迎泽宾馆东楼,那时还没有西楼。我去宾馆拜访过,还领上郭先生到文庙看过青铜器。博物馆在文庙里头。
没有见面,我对他就有所了解。郭先生是中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名气大,知道的人多。早先曾说过,这辈子要挖一千个墓,将来去世了,给他坟前立个碑,别的都不写,写上“千墓老人郭宝钧之墓”就心满意足了。实际没挖那么多,一是解放后挖掘古墓有了新规定,再就是他身体不好,有糖尿病,不能多往下面跑,总共挖了三百个左右。要按解放前他在史语所考古组的挖法,活了那么大,一辈子下来是能挖一千个墓的。谈话中能感到,这个人很自信,有股子豪气,也聪明。这样的性格,用到做学问上,就爱下判断,有时是对的,有时就难说了。
韩:郭宝钧是跟梁思永一起进的史语所,后来还主持过几次殷墟发掘,起初在史语所不甚得志,史语所里留洋的人多,相互之间问话免不了夹杂着英语,有次傅斯年跟他说话,无意间用了英语,他就受不了了,以为傅斯年欺他英语不行。好像他有个论断挺有名的,说是古代大型墓葬里,陪葬的马车,不是整个马车埋在一起,而是将轮子拆下靠在墓壁上。有的学者不相信,后来墓挖得多了,证明郭先生早先的论断是对的。
张: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一事,发掘青台史前遗址的房子,有火烧的痕迹,他说是用泥土木骨做起后,放一把火烧烤,使之坚实。据说夏鼐先生也不相信,说可能是自然火烧的。事过几十年后,大量挖掘证明,他老先生是对的。不过,也有些事上,判断就错了。他曾写文章说过,古墓葬里,凡发现带钩的,都是赵武灵王以后的墓,意思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带钩才传到中原。这种说法,后来证明是错的,许多更早的墓葬里出土了带钩。
韩:好像在什么酒器上,他的判断也是错的。
张:爵,一种古代的酒器。边上有两根小柱柱,也是铜的,郭先生说古人喝酒时往上倾,两个小柱正好抵住鼻梁上部两边,就这样(两手拇指翘起夹住鼻梁),让人不会喝得太猛。斝也是酒器,上面也有两根小柱柱,斝的口面有这么大(用手比作小盆大小),也是抵住鼻梁吗?说不通嘛。人都说他想象力丰富。
韩:想象力丰富是好事。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这些人,后来搞了古文字研究,闻一多搞古典诗词研究,也跟古文字研究有相似之处,所以能有那么大的成绩,恐怕与他们当初是诗人,想象力丰富有关。有联想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