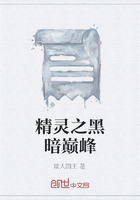女子身形瘦小,光以外形轮廓来判断的话,同陈游倒确有几分相似。只是她的脸上被施了墨刑,发丝凌乱地披散在前额,实在是无法真切地看清她的面容。此时,女子正被麻绳五花大绑地捆扎着无法动弹,嘴巴也被严严实实地堵上了,唯有身子在不住地战栗着。
“这便是当日被尚书令大人所斩伤的刺客陈游。”茹法珍道。
“是吗?”萧懿苦笑了一声,“居然如此命硬。不过,茹大人也不必特地将她带到殿上来吧,毕竟此人是有弑君的意图的。”
虽然看不清她的脸,但是,萧懿的心中明白得很,此人并非陈游。萧懿默默松了一口气。不管目前状况如何,至少,陈游现在是安全的。
“不过是只受了伤的瘸鸭子罢了,再说,近旁有禁军看着,又有尚书令这般的高手在,想必这刺客也做不了什么。”
“茹大人过奖了。”萧懿对上茹法珍那双几乎眯成一条缝儿的笑眼,内心不禁有阵阵不安袭来。他预感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只是没有勇气去设想事情的结果究竟会变得如何罢了。
萧宝卷像是半打着盹儿,有气无力道:“法珍,别讲究礼数了,赶快进入正题吧。”
“遵旨。”茹法珍朝着萧宝卷行了君臣之礼,又转向萧懿,幽幽道:“萧大人,事情是这样的。今夜将您召进宫来实是另有他事。”
“茹大人请讲。”萧懿尽管心中已是焦躁不安,却也被茹法珍这种拖沓的问话方式弄得有些不耐烦。
茹法珍将手中的鱼肠剑举起,递给萧懿:“请大人再次用这柄鱼肠剑将陈游处刑了。”
萧懿一愣,剑被递到手里,自己却在瞬间失去了握住它的勇气。
“这是皇上的意思。”茹法珍冷冷一语,如冰锥刺心。
“陈游”虽然被堵住了嘴,无法为自己辩白,却也听明白了方才自己已被子虚乌有的“罪状”给判下了死刑,身子颤抖得愈发剧烈了,口腔里也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声响。那零乱发丝中隐约露出的浑浊眼神,已被恐惧所占满,瞳孔的聚光点也集中在萧懿的身上,像一只乞怜的丧家犬般哀求着他。
茹法珍朝其中的一名禁军使了个眼色,那名粗壮的汉子便给了“陈游”一个结结实实的肘击,“陈游”便悄无声息地倒在了萧懿面前。
“萧大人,您这是怎的了?”茹法珍将鱼肠剑往萧懿的手心里推了一推。
萧懿方才回过神来,取过爱剑。
剑出鞘,白刃映着自己的眼眸。那是一双慈父的眼睛,温润如玉;那也是一双臣子的眼眸,忠耿正直。
萧懿举不起剑,更抬不了手。
或许,他一剑斩下,便能从萧宝卷同茹法珍为他设的这一个陷阱里爬出来,破了他们的疑虑。然而,若是就这样一剑斩下,萧懿的这柄鱼肠剑从此便承载了一名无辜少女的冤魂。这柄鱼肠剑便会变得愈加沉重而无法将之举起了。
“只要一剑刺下去,尚书令大人便可领功回府了。”茹法珍催促道,嘴角神经质地轻轻抽搐着,眯着眼凝视着萧懿握着剑的手。
萧懿拿捏着鱼肠剑,同时,拿捏着生命的重量。
其实,作出一个决定,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萧懿跪在了地上,双手捧起鱼肠剑,额头紧紧地贴上了冰冷的地面。
“臣下不了手。”
殿上静默片刻。
茹法珍挥挥手,让禁军将假“陈游”抬走,而后去扶萧宝卷下殿来。
“萧懿,你实在是太让朕感到失望了。”萧宝卷一把夺过鱼肠剑,冷冷道。
萧懿没有抬起头,他知道今日自己已是厄运难逃了。
“朕曾经以为,即便天下所有人都会欺骗朕,惟有萧懿你不会。”萧宝卷虽然嘴上这么说,事实上,他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萧懿忠于自己也好,不忠也好,都动摇不了萧宝卷,也不会使他一贯坚持的肃清原则发生任何的改变。
“算了,”萧宝卷扬起暧mei不清的笑容,“今晚你就留下陪朕畅饮一夜吧。”
茹法珍识相地吩咐下去,让人摆了一桌酒菜,恭谨地请两人坐好,自己则陪在一旁,替两人添酒。
“爱卿与朕多少都算得上是血亲,论辈分,用民间的说法也应以叔侄相称。”先开口的还是萧宝卷,他举觞轻抿,不时地用眼角去瞥萧懿。而后,他看着茹法珍端来一盏酒,轻手轻脚地摆在萧懿面前,便浅浅一笑。
“这是湘阴出的酒盏,成色温和,不由得让朕想起了像爱卿这般温和的人。”
萧懿默默端起酒盏。透明的液体在酒盏中轻轻晃动,盏底那一点朱丹却鲜红得刺眼。
萧懿明白那一点色彩代表了什么,手指剧烈地一颤,酒洒了几滴。
“怎的,爱卿不满意这酒?”
“皇上赐酒,臣怎敢有丝毫不满?”
“那就喝了它吧。”萧宝卷说完,身子朝后轻轻一仰,看着萧懿下颚一扬,浊酒下肚。
浩儿……
据说人死的那一瞬间,会想起一生所历经的一切。在理论上,这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不死一次,又怎么会知道呢?当然了,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在确定了这件事的可行性之后,将结果告之他人。所以,面对死亡,人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与臆想。
萧懿死的时候,很是平淡。他没有因为肉体的痛苦而挣扎,只是吐了几口血,便倒在了萧宝卷的面前。
茹法珍上前检查了一下尸体,而后将萧懿的死讯告诉了萧宝卷。
“很好,接下来,将其余贼孽扫净便是了。”萧宝卷将自己酒杯中的液体一饮而尽,舔了舔嘴唇,道,“若不是念你救过朕一命,朕也不会那么仁慈留你一个全尸的。萧懿。”
黑夜更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