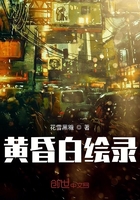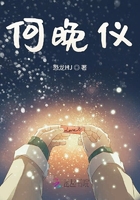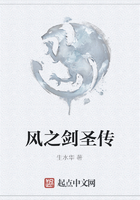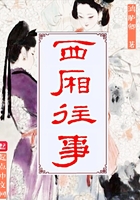徐志摩遇难后,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关于徐的部分是这样说的:
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时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心理的酝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与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
冰心对"从来就不是朋友"的徐志摩,怕是恨铁不成钢吧。
她欣赏他的诗,他的魄力,却看不惯他"聪明人自己的糟蹋",格外强调"女人"与他,到底是谁误了谁的问题。
"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谁是这个"女人"?其实大家心照不宣,暗指的应该是林徽因吧。
她曾是徐志摩"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是他至死都在惦念的女人。因为被她所吸引,他宁愿斩断与结发妻子的姻缘,结束不自由且没有任何感情的婚姻,甚至绝情到让妻子张幼仪去堕胎,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打掉。
在他生前,即使是林徽因已经与梁思成完婚,他依旧挂念着老朋友。1931年,林徽因在香山养病,徐志摩常去看她,把她看作可以诉衷肠的人。
据林徽因堂弟林宣说,徐志摩去主要是为了"躲气"。
"陆小曼生活奢侈浪漫,在上海搞得乌烟瘴气,弄得徐志摩心情很不好。他在北京城里有许多熟人,但没去,就是要上香山,并说"我很不幸","我只有到这里来了",他到香山跟我姐姐是叙旧,舒舒心气。"林宣说。
梁思成极尽东道主之谊,徐志摩与林宣入住旅店的住宿费都是他掏的。
"二哥(梁思成"给我的任务,就是陪徐志摩上山。"林宣坦露。
"我和徐志摩都住在香山的甘露旅馆。每天吃了早饭就去林徽因住处,我们的中晚餐一起吃,夜里回来。"
有人私下与梁思成说起过,徐志摩三番五次地上山来与林徽因畅谈文学,文化圈里都在纷纷猜测是不是二人旧情复燃,话里话外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梁思成听了,不知心中作何感想,可他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对妻子无条件的信任。
林徽因不会去解释什么,她与徐志摩聊文学、谈创作,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外人如何传言,那是别人的事情,与她无关。她不仅要与他开怀畅谈,还会将满意的作品寄给他,发表在他主办的刊物上。
女人是害怕流言蜚语的,即使是一身清白,也担心从别人的口中说出什么不得当的话来。舆论的压力有时好,有时坏,一人相信,也许并不是真相,五六人之后,或许就变成了确凿的事实。
拿出你的真性情来,为什么要让谣言坏了心情,敢作敢当的人,本身就令人信服。
不虚伪、不造作,何惧那些非善意的口舌。
无须你解释,时间会向世人证明一切,说明真相。
率性与刻薄一面之隔
什么是率性?
《礼记·中庸》中谈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取义遵从自己的本性来做事的态度。
率性之人,说话办事直截了当,不会拐弯抹角兜圈子。它带有褒义的感情色彩。
什么是刻薄?
说话句句带刺,待人冷酷且提出过分的苛求,不给他人丝毫回旋的余地,让人感觉特别没有人情味。
直率的人多有一颗坦荡的心,以及包容豁达的胸怀,人们乐意与之交往,或开怀畅饮,或谈天说地,无所不欢。
刻薄之人则多心胸狭隘,看什么都不顺眼,完全一个牢骚"制造机",让人唯恐避之不及。
李健吾用"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来描述林徽因,这与以往铺天盖地的赞美之词不同,让人们看到了更加真实可感的林徽因,她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她也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瑕疵的女人,甚至"几乎所有女性都把她当作仇敌"。
林徽因心直口快是出了名的,不论是在自家的客厅,还是在别家的聚会,或是其他场合,她时刻保持着高调,李健吾在文章中有过一段描述:
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现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
面对神采奕奕、蓄势待发的林徽因,几个平日里滔滔不绝的大男人,却一直缄默不语,恐怕是忌惮于她的伶牙俐齿吧,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林徽因的"威慑力"。
慈慧殿三号对于当时北平的文人圈来说,并不陌生。这是朱光潜在景山后面的寓所,在他入住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迫不及待地着手组织"读诗会",这是与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同样有着深远影响的文化沙龙。
沙龙的主人朱光潜,笔名孟实,是香港大学文科毕业生,20年代中期先后留学英法,只身游历过德国和意大利,1933年7月归国后,应胡适之聘,出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朱光潜在谈到组织"读诗会"的目的时曾说,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专门卖诗的书店,这个书店每周四会举办一场朗诵会,他在伦敦时,也常常去听。他认为这种朗诵会很好,并且认为诗要有音节、节奏、能朗诵才是好诗,于是,他回到北京后组织了诗歌朗诵会。
读诗会每月集会一至两次,到访的宾客们会朗诵中外的诗歌和散文,因此得名"读诗会"。慕名而来的学者诗人们,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感言,或就某一问题展开争论,不必有所忌讳。
聚集于此的人也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北大的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清华的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此外还有冰心、凌叔华、林徽因、周煦良、萧乾、沉樱、杨刚、陈世骥、沈从文、张兆和,以及当时在京的两位英国诗人尤连·伯罗和阿立通,等等。
1934年,一个冷风刺骨的寒冬,当时还是燕京大学一名普通学生的萧乾,收到沈从文和林徽因的邀请,初次造访慈慧殿三号"读诗会",前辈们精彩绝伦的对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有一种喝足了醇酒而醺醺的感觉"。在他眼中,读诗会"恰似一座金矿","到处都是闪光的矿石"。
沈从文《谈朗诵诗--一点历史的回溯》说:(读诗会上""长于填词唱典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习德文诗的冯至先生,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诸先生,都轮流读过些诗。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
读诗会借用集体讨论的方式,针对某一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争个面红耳赤。
有些自傲又有着独特见解的林徽因,显然将这里当作了战场,冲锋陷阵,摇旗呐喊。恰好,与梁宗岱棋逢对手,成为读诗会上最爱争论的两个人,说到兴致高昂时,更是忘乎所以。
林徽因果敢坚决,据理力争,不将对方说个心服口服决不收手;梁宗岱是大嗓门,"揎拳捋袖,大吼大叫,震得人两耳轰鸣,像与人吵架一般"。
两个人旁若无人地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看样子是不将敌方杀个片甲不留,誓不罢休。
言辞一向犀利的林徽因,与人争论起来也是毫不含糊,相当霸气,句句精准,好几次让梁宗岱措手不及,越争论就越是兴奋,两个人似乎都忘记在座还有其他人了。
熟悉林徽因的友人,将她的争强好胜看作是率性而为,是这样的真实生动,将心中所想自然流露,不虚伪做作,这样想的多是男人。不熟悉她的人,则多会认为这是一种刻薄表现,这样想的多半是女人。
凌叔华曾略带偏见地说:"林徽因被周围的男人宠坏了。"的确,林徽因是真正"受宠"的人,她周围的朋友多为男士,在他们眼里,她的自傲和直率绝非是什么不能容忍的缺点。比她稍微年长的人,甘愿迁就、放任她,陪她一起海阔天空,与她岁数相仿的平辈,则顺从、佩服她。
至于"刻薄与否"的问题,分歧在于她的女性朋友。实际上,林徽因并没有多少深交的女性朋友,甚至连泛泛之交也属少数,费慰梅是她最贴心的女性朋友,算得上知己闺密。
不受女性朋友的欢迎,也许多多少少会有嫉妒的因素在里面,如果深究起来,则可能是由于林徽因的太过直白和苛刻。
她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别人的短处,在她眼里是不能容忍的,不论对方是谁,常常出语尖锐,男人会容忍她,甚至因此而欣赏她,但女人绝对不会。
谁都有过被他人劈头盖脸一顿臭骂的经历,也许是长辈、上司,或是同事、朋友,被数落的人心里总是不好受的,尤其是对方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样子,对被批评的人而言,简直是可怕的心理伤害。
的确,大多数女人没能如林徽因这般出类拔萃,她们或许也有满腹才华,也许只是平凡甚至平庸的人,当她们遇到林徽因,心理上的自卑是不会自行消退的,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是,林徽因没能做出谦卑的姿态去迎合她们,久而久之,受到冷遇、漠视的女同胞们,自然很难再与她有进一步的交流,就更不要说推心置腹的交流了。
陈钟英的《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札记》中,林徽因的亲戚陈公蕙说过:"林徽因性格极为好强,什么都要争第一。她用煤油箱做成书架,用废物制成窗帘,破屋也要摆设得比别人好。其实我早就佩服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