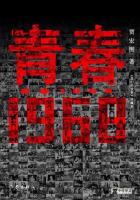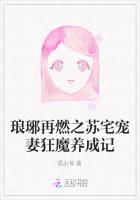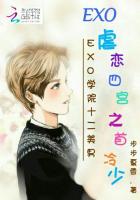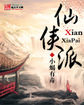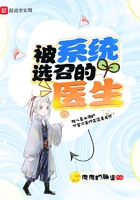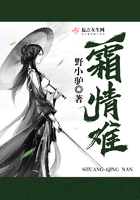李生滨:因为有长期的追踪阅读,王之文的发言条理比较充分。我最后还要强调几点,西方的弗洛伊德学说可能给了他关注少年性意识的视角,但郭文斌并没有停留在弗洛伊德学说简单的性冲动的意识层面。关于怎样理解生存的艰难,我所要补充的是,不论是公众舆论还是文化批判,在普遍态度的背后都存在话语与文化的强权,若以文学批评的外来话语作参照,就始终在强化一种以外来人的眼光看待边缘和对象的误读,自然会产生优越的话语姿态和不真实的情感,包括貌似高尚的同情,等等。具体到某个地域环境的生活态度和生存真实,就应该避免这种误读和虚伪同情。所以阅读郭文斌这些本土作家的作品,应当以西海固这一地域的原态生活作为观照和审视的依据。最后,讲到“禅”,每个人都有本真的自我,诗是唯美的人性自由的追求,禅同样追求空灵的美的境界和人性本真,就像王之文说的明月清风。人常常无法控制自己,但唯美向善的上进性从来都不会失去。人无法走向完全的明月清风,亦不可能完全走向恶俗和虚伪,都是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们永远渴求美好和崇高的人性自由,所以文学的审美和批评永远涵养着人作为人的人性关怀和艺术价值。
王静在她的书面批评中写得很好。废名和郭文斌本着对日常生活的捕捉,共同着力于乡土生活的细致描写和浪漫抒情的意境营造,同时还包藏了隐忧悲凉的对一切生命的深切同情。这样一种审美与叙事的回归传统,却又融合了最现代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讨论这样两位作家作品的原因和意义。
讨论到此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这里,还是借李兴阳先生作为《大年》“代前言”的话作为结语吧:“郭文斌还在路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不断地惊大我们期盼的目光。”
李湟水王之文整理
见2006年第3期《黄河文学》
论汪曾祺小说艺术的和谐美
文学的美学风格有自己生成、发展、流变的过程,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系统范畴。美学风格是作家审美创作独特和个性化的自我实现与呈现。在文学群体、流派涌动更迭的20世纪80、90年代,汪曾祺是为数不多的个性化的抒情小说家。“他40年代受业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并有了文学创作,在经历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沉寂后,在80年代复出,重新显示了“京派”文学的文学立场和艺术魅力。”他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表现他熟悉的、经过情感和心智沉淀的记忆。在对童年、故乡、往事的回忆中,将热情寓于恬静、沉重融入乐观,用自然、清雅的笔调抒写健康、美丽的人生,以宽厚通脱的胸怀构建理想的生活境界,形成了和谐优美的小说艺术风格。在他的艺术创作里,他用自己艺术的心灵体味更其真淳的生活,并用美化了的生命热情再现。本文拟就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从以下三方面作一些探讨。
首先,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体现为多重关系的和谐与协调。
汪曾祺用小说表现了对生活的理想寄托,在作品的叙述描写中用和谐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丑恶和阴暗,进而追求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传统伦理中的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和谐美直接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多重关系的冲淡协调之中。
汪曾祺的小说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表现民间的生活立场和道德观念,并给予认同。又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三人的生活并不怎么宽绰,但当地方上要做公益,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簿伸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三人的急公好义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在朋友身处困境需要资助时,王瘦吾、陶虎臣为靳彝甫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穷画师外出谋生;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一家人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脱朋友于困厄。《徙》中的谈甓渔与高北溟师生情深,在高北溟受业时,谈甓渔不收高北溟的修金;在学生业满出师后,谈甓渔将别人求他的文字、碑文墓志,寿序挽联都推给高北溟,让他靠润笔所得养家糊口。谈甓渔去世后,高北溟为了恩师的遗稿得以刻印,节衣缩食,并不惜牺牲爱女白雪的前途。在艰辛的窘境中,还时时周济恩师不争气的儿子。谈甓渔、高北溟的身上体现出读书人的正直善良和多情重义的品质。《故里三陈·陈泥鳅》中的陈泥鳅挣来的钱除了自己花销外,“也偷偷地周济一些孤寡老人,但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茶干》中的连老板待人热情诚恳,没有惯常生意人的精明狡猾、唯利是图,他做生意靠的是勤快和实诚。《七里茶坊》中的掏粪工人老乔、老刘、小王在劳动时特别关心年长体弱的“我”,执意不让我下粪池凿冰,只干点轻松的活;当老乔、老刘和“我”三人得知小王为结婚的经济拮据而愁眉不展时,立马凑钱,解除了小伙子的心头疙瘩,四人之间宽厚体贴、诚挚互助。《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小工团结友爱,《安乐居》中的酒友们友爱共处,《受戒》中尘世与佛门间亲密融洽,《大淖记事》中锡匠与挑夫们睦邻友好、同甘共苦。这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多具一副仁人君子的热肠,有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他们热情诚恳、正直善良、多情重义、舍己助人,强调自身的责任和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自觉地使自己的情感行为与群体沟通,与社会道德认同,与客观环境协调,表现出一种平和友爱的生活态度。
和谐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真正建立人与客体世界的和谐共存关系。《故里杂记·榆树》中的侉奶奶疼爱那头牵磨的驴,驴乏了,打滚时,侉奶奶“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乡下人进城卖牛给屠宰场,是侉奶奶地方上的人,出面将年老的牛买下来,使得这头老牛能够在众人的照料下“颐养天年”。《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在这种人与物的关系中,物似乎成了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人对“这一部分”分外的珍爱,可以与之交流,与之勾通,物我之间显得十分和谐。形成了亲切优美的共存关系。
由于这种多重关系的冲淡平和、亲切美好,构成了一个真正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争斗,家庭之中慈孝悌爱,乡邻之间和睦互助,师生之间情重谊长,朋友之间相濡以沫,同事之间谦和宽容。这样的氛围空间生存的人们性情平和、胸怀宽广,有着自己的生存规则和道德标准。言行纯真质朴,发自内心,出乎自然,似乎看不到外在因素的强制作用,兼体万物的仁厚善良不仅促成了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还形成了宁静和谐的田园情怀。优美的本质在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存中,是人对这种和谐状态的情感肯定。和谐之为美就是这种多重关系间相互共存的宁静与美好。
其次,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典型地表现在作品人物内在的谦抑节制和外在的无拘无束。
汪曾祺在构建着理想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深沉地思考着人生的本质——生命自身的存在方式。同样,和谐也是汪曾祺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并给予成功的艺术揭示。优美和谐成为个体生命最理想的存在状态。作为相对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客观地说,自身有诸多的矛盾,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内在因素,但汪曾祺小说以人物性情的秀雅和通达调和了生命中的狭促和痛苦。内在的平和淡泊的谦抑节制和外在的率性自然的无拘无束互相协调,从而使生命处于自由自在的和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