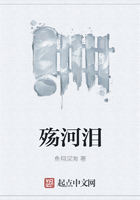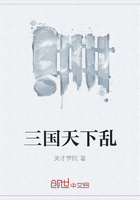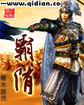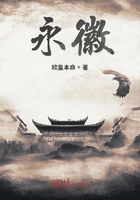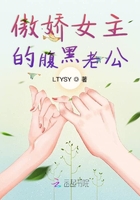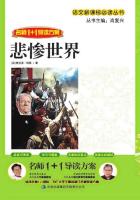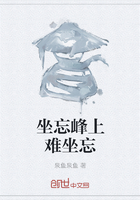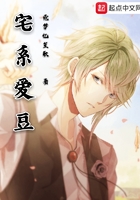昭宗喜欢搞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昭宗很聪明,他很清楚地看到影响帝国的多股力量,他们互相扭和在一起,任何一方的变动对于其他而言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平衡是帝国的当务之急。
问题在于,这是个年轻的天子,在他脑子里边翻腾着有关帝国未来的种种期望;在他眼睛里便燃烧着改变现实挽救帝国的壮志豪情;在他手上握着代表天子权力和地位象征的玉玺……
因此,平衡对于他和帝国来说,是矛盾的统一体。他和帝国需要平衡以延长自己的生命长度;而他们又讨厌甚至憎恶平衡,因为那意味着放任意味着无所作为意味着眼睁睁的看着帝国崩溃。
帝国快崩溃了,每个大臣都很清楚。长安的百姓们早已经习惯了打个小包袱跟着皇帝逃亡的命运,他们慢慢地开始变得淡漠,开始冷冷地打量这个曾经给他们带来了荣誉和富饶的帝国。
这时的长安已经变成了地方诸侯们眼中的洛阳,那是东周天子的都城。每一个稍微有点实力的节度使都开始幻想哪一天能够像楚庄王一样,把自己麾下旌旗鲜明枪戟林立的队伍摆在都城下,然后问躲在城里瑟瑟发抖的天子——当年大禹铸造的九鼎到底有多重?
显而易见,昭宗陷入了两难的选择——或是尊重现实,保持帝国原有的平衡;或是大破大立,自己来设计和掌控平衡。他选择了后者。
有人说,当人类开始思考的时候,上帝笑了。
而昭宗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帝国则是苦笑了。对于一个年轻的帝王而言,还有什么能够比在位时大权在握随心所欲身死后青史留名后人称道更加令人向往呢?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没事也得找事做。
昭宗就是这样。他总是在自己搞出一大堆事情,看着臣子们乱糟糟地收拾残局,他居中作出各种令人惊诧的平衡,对于他而言,这就是最大的满足。
帝国最主要的政治势力有三:南衙、北司、藩镇。南衙和北司都被皇帝视作“自己人”,就是他们都得靠皇帝吃饭,虽然也会让皇帝很麻烦,但对于帝国皇室来说还是很安全的。另外无论南衙还是北司他们都属于帝国中央。皇帝们有时候依赖南衙,有时候信赖北司;而藩镇则一直作为地方割据势力而受到历代皇帝的打击。但凡有点野心和责任感的皇帝总都要动一动藩镇。
到了昭宗这儿,情况变得比较复杂。
昭宗他也想动一动藩镇,但后来发现这是自讨苦吃,于是开始走中庸路线,大搞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
首先是藩镇之间的平衡。德宗曾经试图利用一个藩镇去攻打另一个藩镇,自己坐壁上观,最后出面收拾残局。可惜这一招没有玩好,还惹来了一场兵变,自己狼狈逃到凤翔。而昭宗则不一样,在攻打藩镇碰壁之后,他决定小心翼翼地保持各个藩镇之间的平衡,不让任何一个藩镇坐大。
其实这种想法很笨。对于孱弱的帝国中央而言,任何一个稍微有实力的藩镇都足以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在昭宗平衡羽翼庇护下的诸侯们便动辄把昭宗放在手里玩弄一番,以最大程度地争取自己的利益。
当时的基本局势是,关中长安附近有三个藩镇,其中以凤翔军阀陈茂贞最为强大;而李克用盘踞山西;韩建盘踞陕西华州;朱温盘踞开封;这些都是距离长安比较近的藩镇。在这之外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藩镇,帝国中央事实上已经只相当于一个土地分散,政令不畅的大藩镇。
早在杨复恭奔逃山南西道时,昭宗便为了保持藩镇之间的平衡而拒绝了陈茂贞等人请求攻打山南的上表,导致陈茂贞大怒,上书辱骂朝廷。
昭宗愤而出兵讨伐。结果被打得大败,陈茂贞领兵进入长安,逼迫昭宗杀死宰相杜让能,然后在京城耀武扬威。其他的藩镇看不下去了,同时对他的收获也很眼红,李克用大叹一声,说这小子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举兵杀入关中。
陈茂贞哪是李克用的对手,赶紧服软。这时李克用对昭宗说,让我帮你把这小子彻底灭了吧。
昭宗必须作出决策,一方面是这个沙陀人现在实力强盛,另一方面是陈茂贞在李克用的巨大压力下向昭宗不断说好话,还保证说以后不会再犯云云。昭宗想了又想,派人跟李克用说,爱卿你先回去吧,陈茂贞既然认错了就暂时放过他。他最终选择了留下陈茂贞,理由很简单,关中有个实力还算不错的藩镇对于河北的朱温和山西的李克用来说好歹也算是一个牵制。
昭宗自以为得计,但直接结果却是陈茂贞随时环伺左右,稍有风吹草动便领兵杀入长安,导致昭宗只得一逃再逃,窘迫不堪。最后还被韩建扣留在华州,宗室子弟几乎全部被害,昭宗整日以泪洗面,盼望有人能够帮他脱离华州,回到长安。
昭宗不仅仅在藩镇之间搞平衡,他还试图在南衙和北司之间建立新的平衡,结果同样是灾难性的,朱温趁虚而入,把帝国的长安祖业烧了个干干净净,然后把所有的人都驱赶到得洛阳,至此,离昭宗的大限之期也就不远了。
事情是这样的。
昭宗被困华州,太原的李克用听说后长叹道,要是当年昭宗让我干掉陈茂贞那小子的话,就不会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但虽然相距不远,但他这时是束手无策。因为,朱温也插手其间,还大肆进攻他的地盘,他正忙着全力防御。
宰相崔胤一向与朱温交好,他秘密地写信给朱温,召他前来救驾。朱温并没有真正的前来,只是摆出一副要兴师问罪的样子,写信给陈茂贞和韩建,把他们两个谴责了一番;同时李克用虽然滕不出手来,但声势也丝毫不减,他同样表示如果陈、韩二人不罢手,他要准备兴师问罪。
陈、韩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确做的太过了。李克用和朱温他们谁也惹不起,更不用说两个人同时前来讨伐了。于是陈茂贞表示出钱修复自己放火烧毁的宫殿,韩建请求昭宗允许他护送昭宗等人回京。
昭宗忍着气,终于回到了长安。但回来之后,他的性情大变。他变得暴躁、易怒。欺负弱者一向是人类的天性,他又准备拿宦官开刀了。最先倒霉的是平时服侍他的宫女和小太监,他们整天心惊肉跳,担心这个怒气冲冲的天子把火发到自己头上。
宰相崔胤凭借朱温的关系,在朝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朝廷官员们稍微得罪了他便被贬斥,就连有权势的太监们都不得不对他退避三舍。不过他还是觉得不够过瘾。宦官们成了他进一步掌握权力的最大障碍,他极力鼓动昭宗除掉宦官。
昭宗此时已经完全沉醉在了华州的耻辱当中,他急需一个可以稍微让自己振作的理由。而除掉宦官,便是他在绝望中的救命稻草。
于是,昭宗先将两位专权的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清除出京,没过几天又派人去将他们赐死。这引起了其他宦官的恐惧。几个月后,昭宗在外边打猎回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暴怒,杀掉了好几个亲近的太监和宫女,一时间宫中人人自危。
四大宦官首领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左、右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四个人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决定发动政变。
第二天四大头目带领数千禁军杀进皇宫,见人就杀。昭宗吓得躲到了床底下,但最后还是被拖了出来。刘季述逐一数落昭宗的种种不是,并说,像你这个样子,已经做不了皇帝了,还是让太子来当吧。昭宗还想做点挣扎,他略带些讨好地对宦官们说,我昨天主要是多喝了点酒,所以杀了几个宫女和太监,不至于这样吧。
宦官们当然不理他,把他和何皇后、小儿子等人一起锁进少阳院,每天从一个小孔里边给他们送一些东西。刘季述还在锁里浇注了铅汁,表示不会再让他出来了。
昭宗再次面临危机,少阳院里的生活标准已经到了少衣缺食的地步,冬天昭宗的小儿子因为没有棉衣而被冻得整天啼哭不已。帝国的皇帝居然过到了这个地步,实在令人可叹可气。
昭宗在少阳院了忍饥挨饿过了一个多月,宰相崔胤联合一些力量杀了杀了四大头目,把昭宗放了出来,他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聪明”。
崔胤极力建议趁此机会把禁军手中的兵权收归皇帝所有,让大臣们掌管。如果成功的话,那将是自宪宗宦官掌管兵权犯上作乱以来最大的胜利,但被昭宗拒绝了。他认为掌兵权的宦官之所以作乱是因为所托非人,于是他把兵权又交到了亲信宦官韩全悔等人的手里。他自有小算盘,崔胤越来越大的势力让他觉得很不安,亲信的宦官掌握兵权多少还能给他一些安全感。同时这也保持了南衙和北司的平衡。
这一次自作聪明的结果很快显现。崔胤和韩全悔等人互相猜忌,都各自联系藩镇作为己方外援,然后挟持皇帝除掉对方。
昭宗并不笨,他看出了风头,曾经也想让二人和解,但此时他已经失去了任何的发言权。韩全悔抢先动手,挟持着他一路奔到凤翔投靠李茂贞。
而崔胤的外援是朱温,老朱起初并不愿意起兵管这些杂事,他已经将最难对付的河北三镇之地收为己有,并一心想吞并李克用。但这时候有人劝他说,勤王之事,霸业之资。就是说要成就一番霸业,没有什么比勤王的旗号更管用的了。老朱幡然领悟,带兵围堵凤翔,不仅仅把昭宗从李茂贞手里解救了出来,还趁机把昭宗迁移到洛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最后干脆杀了昭宗,另立哀帝,不过这已经是他称帝的前期准备了。
帝国到了现在,已经是完全陷在了宦官、大臣和藩镇的泥淖里边无法自拔,昭宗有所作为的每一次冲动给帝国带来的都是更深的陷没。
其实,他并不可爱。他想效法前代的有为君主却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他陶醉于自己的平衡之术却一再使帝国陷入更深的混乱和衰败中。对于帝国而言,他很可怕。因为,是他把帝国直接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当昭宗这轮太阳落下的时候,帝国也就沉入茫茫的历史黑夜之中了。幕布拉开的,是另一个混乱的年代。而这个时间,已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