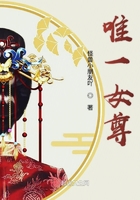从海文家走出来的那会儿,杜英英并没有急于回家,在庄子附近的田埂上徘徊了很长时间,才来到自己家大门口。听到院里传来了母亲送客的声音,她立马停住了脚步。继而又听见韩维民和丁凤芹向母亲说着道谢的话,她立马躲到院门附近的一棵树后,待到韩家夫妇走远,才蹑手蹑脚地走进了自己家的院子。
若按她心里的想法,自己还要在冷风里麻麻木木地走。那样,至少可以减少心中的烦躁和苦闷。作为女儿,她却没有忘记每晚必须服侍母亲吃药和洗锅抹灶的事情。来到厨房,发现母亲已将她惦记的那些活,已干去了大半。她系着女儿的花围裙,身子那么硬朗,动作那么麻利,居然还轻声地小声唱着一首当地的情歌。
杜英英没有声张,呆呆地站在对方的身后观察并沉思着。母亲的变化让她感到格外震惊:这些日子,尽管每天都要吃两顿汤药,那病却一直不见好转,把女儿的这颗心拴得好苦好苦。她出门之前的那阵,母亲也像往常那样,病病秧秧地坐在炕上。可现在,怎能判若二人?
这种突变,勾起了女儿对以往一些事情的疑问。是啊,若按自己心里本来的想法,只要韩家想让她去做儿媳,不管让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家里提及,她都可以将他们狠狠地指责一番,乃至奚落一顿。她有这种胆量,也有这种能力。但恰恰是考虑到了不能使母亲的病情加重,便不得不保持沉默。
这是爹至今也未能发现的一个秘密:只要韩维民到这个家里来过,哪怕只露一下面,一个字也不说,一点好眉目都没有,对方走了之后,妈的精神就会立刻充沛起来。她这个“贼溜子”女儿,甚至对娘还有过这种发现:凡是她病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恰恰是韩维民很长时间没到自己家来过,仿佛对方是娘的什么灵丹妙药似的。
她无论如何也解不开这个谜。当然,她也知道,对于这种似是而非的所谓问题,实在不便张口直接去问母亲。即使自己有那种胆量,母亲肯定也不会对女儿如实道出原委,女儿更不可能去向其他人打听。她知道,那样不起任何作用,还会造成很糟糕的影响。于是,只能一直疑惑,有时这种疑惑里竟然闪现出几个让她心惊肉跳的可能来。
忙完了厨房里的活,周凤莲猛一转身,发现女儿竟然站在自己的身后,不免有些惊讶,但又怕女儿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就急忙问:“阿依莎,你怎么啦?”
“没啥事。”女儿以为妈问的,绝不是自己对她反常行为的惊愕与疑虑,是自己的神色里明显表露出的在海家所受的那番刺激。对病人,杜英英向来报喜不报忧。即使无喜可报,也只能保持沉默。她急忙拿起砂锅,到大屋炕桌上的火盆跟前,准备给妈熬第二回药。周凤莲也解了围裙,擦干了刚洗过的手,随着女儿向大屋走。
就在这时,母女俩都听见了窗根外边响起的脚步声,每一声都是那么沉重,声与声之间的距离也是那么急促,居然在东屋门口毫无停顿地朝西屋走去了。她俩谁也没说什么话,可心里都知道那是谁的脚步声,并且也能猜出传来脚步声的那个人要去西边屋里干什么。
匆匆忙忙从张佐铭家走出来,杜石朴的心情愈来愈沉重,想起今儿一天发生过的诸多事情,心里就像打开了五味瓶,酸涩苦辣咸哪一样都不少,惟独没有预期的要治服海文的得意感觉,懊恼的波涛在脑海里时起时伏。唉,这种动荡不定的岁月当中的人啊,怎么能这样难做?
尽管心情烦躁而沮丧,当来到自家院子里的时候,他仍是没能直接走进自己所住的东屋,而是一如既往到西边屋里看望两位老人。若不这样,他的心里就会不踏实,吃饭不香,睡觉不着。刚走到西屋的窗根,却听到屋里传出了爹和娘哄孩子的声音。
父亲用嫩公鸡般的嗓门,嗲声嗲气地哄着小淘气:“嗷嗷嗷,你的小肚肚吃饱饱了么?”
“没——没——”仿佛学着说话的婴孩,正吃力地回答着老人刚刚提出的问题。
母亲也用仿佛是年轻了许多岁的格外娇美的声音:“还没饱啊,我的小饿死鬼呀。你看,瓶瓶里的奶水,已经让你吃得空荡荡了,过一会儿,我再给你熬吧。”
二位老人的反常行为,使杜石朴立即停住了脚步。他清楚,二老自从上些年纪以来,无论谁家的孩子来了,都不愿与之多打交道。怕吵闹,又怕抓扰,更怕自己眼花耳聋感觉迟钝,会把小宝贝逗出什么毛病来,一直格外喜欢安静。
可今儿晚上,怎会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和心劲?而且是许多年以来自己都未曾听到过的声音。这样的声音,让儿子感到格外惊讶和别扭。没错,对自己的亲孙女阿依莎和法蒂玛,与那时还活着的亲孙子叶尔古拜,他们老俩也从未有过这般有失身份的声音啊。
这件事情,让他有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莫非嫌日子过得过于寂寞,二老又从哪里要来了一个婴儿。他知道,这是搞计划生育这年头经常发生的事情。一些人怕罚款,就将超生的孩子做一些特殊的安排。比较稳妥的办法之一,就是送给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干预的人家去抚养。
他想,很可能是两位善良的老人,经不住别人的诱惑,瞒着他这个当队长的儿子,抱养了别人家超生的孩子。一旦那样,麻烦可就大了。首先,他这个一队之长,要受到别人的攻击。还要影响自己以后的工作,按当地人的话说,就像在他的下巴底下支上了一摞砖——干了一件让他无法开口说话的事情。
领导可以带头违反,那么其他社员还怎么管理?有人若乘机再到上面告恶状,没准儿就会把他这个生产队长立马赶下台。老人们啊,你们可曾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决不是你们那善良而又传统的心理想象得那么简单,而是一件牵扯到国策的重大事情啊。连锁反应肯定很大,也会牵扯出一系列特别难处理的问题。
你们二位都已高寿,这个孩子到底是当你们的儿女,还是做你们的孙辈?若做你们的儿女,那就是说,我杜石朴又有了一个弟弟或妹妹。你们都那样大的年纪了,合适吗?我这样大年纪了,再有那样一个或弟弟或妹妹的小东西,像话吗?
若是给我领养的,那就是说,我杜石朴又有了一个儿子或女儿。想到这里,他的心弦被狠狠地拨动了一下,这样的可能性最大!大概父母总觉得,他这辈子没儿子太遗憾了。自从叶尔古拜去世以后,这也是他们的老话题了。再说,像他家这种特殊情况,别人也能理解,当地的生育政策也能蒙混过关。
可如今,非常年轻的夫妇都在提倡计划生育,我都这般年纪了,再搞来一个小小婴孩,岂不笑掉别人的大牙?这种事情一旦处理不好,就会特别棘手。可不,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啊,有没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呀,他们的父母离这里远吗,他们知道是到了我们家吗?
世事复杂而多变,老人们啊,你们可曾想到或听到,有许多就像你们这样的好心人,费心费力花钱受罪还不落好,要么被当作虐待了人家孩子的罪魁祸首,被告上了法庭;要么让外来的沙子压住了本地的土,所有家业自己家的亲生子女都没资格继承,却统统落到了外来者的手里。越这么想,他的心里就越焦急,越焦急就越觉得二老的的确确做了一件特别糊涂的事情。
他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躬身作揖向二老用经文问候色俩目的时候,就想尽快捕捉到父母倾心呵护的那个宝贝的身影。娘却将之围裹在自己的棉袄衣襟里,让他根本无法看到。更让他蹊跷的是,平常时候,每当自己向二老郑重问好的时候,他们总会比他本人还要当回事,无论拿着多么贵重的东西,都要立刻放下,将双掌合抱于胸前,向他致以热情的回问。今天,却只作了口头回答,这些细微而又非常重要的变化,愈发增加了他想见到那个宝贝的迫切感。
可是他哪里会想到,费心猜测了不少工夫的宝贝,竟是一只又小又瘦的绵羊羔羔。这样的结果,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两位老人的脑子很可能出了特别大的问题。他知道,年迈之人的身体,各种功能都在不断减弱,由于思考能力不再景气,往往会做出一些很意外、很荒唐的事情。是啊,羊羔儿再好看,总比不上后辈人可爱吧?
当得知他们的深远打算,杜石朴竟然是那样的无地自容和悔愧不已。二老已是风烛残年的人,若扎实些说,是有今天无明天的人。可这些年来,家里的光阴一直紧啬,自己这个当儿子的,一直没能给他们在宰牲节许诺并宰过牲。每年的那个节日,他们都是在无奈和失望中度过的。
对宗教信仰本来就很有感情,年龄的变化又让他们的心态产生了一些改变。越上年纪越感觉到了信仰的神奇魅力,越愿意相信天堂和来世,越觉得天堂和来世很亲切,越觉得那将是他们将后长久呆的地方。正是这些原因,同样是每年都有的一个宰牲节,愈上年纪就会愈加重视。据说,去世以后,要想到达天堂,必须要经过火海上面细如头发、快若刀刃的岁拉提桥,可以借助的,是自己活着时候,行下的好、干下的善和宰牲节许过的牲。
鉴于这个家里的具体状况,二老不能不为这件事情时常操心?看来,靠儿子给他们买牲,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可不,连他自己婆姨的事情,都难以顾妥贴,何况肩上还担着那么一副为全庄子人挣巴光阴的担子?若不去积极准备,一旦性命的大限已到,难道就眼睁睁去受那份火狱之苦吗?这些年来,不论谁家给他们施舍几分硬币或几毛钱,二老总会投进柜上的那个瓦碴壶里。
经过几年的积蓄,前些日子倒出来一清点,还只是一点点。大些的牲,他们确实买不起,就将那点儿钱,委托给一个进山人,让人家从羊场上买到了一只失去了母亲的小羊羔。按规定,绵羊羔必须长大成年的时候,方可许牲。那样一来只有待到明年的宰牲节了。到那时,它定会长得高大、硬朗和俊美了。将来到天堂去的时候,就会更加得力一些。
对小生灵的痴情,使得杜石朴愈发担心起了二老的行动和健康。他先为火桌旁边的木匣里添上了过夜用的炭块,接着从屋外提来了二老起夜用的尿壶和尿盆,又伸手摸摸他们的炕,感觉到也还挺热乎,就想通过问话,看看他们的言语表达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到底怎么样:“爹妈还有啥吩咐吗?”
妈用手指着炕边的一个地方,让他尽快先坐下来,自己有话要对他说。爹见他坐定下来,先是扶着两个膝盖站立起来,随后又扶着墙走过去,从悬挂在炕头房梁上的小竹篮里,拿出了庄里人舍散给他们老俩的一些水果类食品与两个烫面油饼,放在他近处的炕桌上,妈又赶忙给他递过来一双干净的筷子。
自己什么也没给老人孝敬来,反而要吃众人舍散给二老的东西,他觉得自己的心里愧疚得慌。可他知道,若是自己一点不吃,爹妈肯定就会见大怪,赶忙象征性地各样品尝了一点。然后,眼巴巴瞅着两位老人那清秀可敬的面容,等待他们给自己吩咐什么。爹捋捋白花花的大胡子说:
“刚才,来看望我们的几个上年岁的人都说,今儿你又和海阿丹闹仗了。往后啊,可再也不能干这样的傻事了。人家海阿丹,可是国家费心费意培养了十几年的读书人,千万不能小瞧人家。你是好娘好老子继续下来的善良生命,即使理全在你这边,也要与人家好说好商量,谁都有个会听话的耳朵、想事的心。说话做事,一定要把后路留开。你要知道,知书达理的人,目光远大,后劲儿也足。
“过去有兄弟俩,哥哥是个靠打柴、驮炭过光阴的睁眼儿瞎。弟弟呢,是一天到晚念书作画赋诗作词的文墨人。哥哥却看不起这个弟弟,总认为,过光阴必须得靠实实在在的本事,对方只不过是用笔和颜色在纸上胡涂乱抹了一些玩意儿,莫非还能生出庄稼、牛羊和钱财来?
“一天夜里,他赶着毛驴路过一个山梁,忽然听到有嫩狗娃子的叫声,就把驴拴在一块石头上,想跑过去捉那只狗娃子。他缩手缩脚又缩着脖子溜到跟前一抓,没想到那肉墩墩样儿的狗娃子,却一下子飞走了。他想,狗生娃,每窝大都有好多个,刚才只飞走了一个,可能还会留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