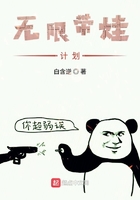张家又最了解他和他家里的这些具体情况,每过一旬或半月,总要准备些有油水的饭菜,等夜色能遮掩住人影的时候,把他请过来改善生活。实话说,若不是对方扶帮,自己这个副队长难干下去。每次,杜石朴只是尝点就行,丢皮舍脸地要上些带回去敬奉一对老人。平时,手头没了零花钱或是女人看病没办法缴费,也只有到这里来张口绕舌。是啊,张佐铭毕竟是队干部,总比向一般社员低三下四心里好受得多。
女人周凤莲几次住院的开销,也是张家垫支的,细算起来也有大半千了吧。他想,等女儿的亲事确定下来之后,手头有了彩礼,一定给张家立马还上。他心里明白,再是队长和副队长的关系,吃吃喝喝的小事,还可以说的过去,有关钱财的问题,必须界限分明。他就是这么一种个性,在这世界上,最不想欠下的,就是别人家的账债。即使当穷汉,也要当得干干净净、清清秀秀和正正派派。
被让进屋之后,杜石朴在炕上坐了片刻,保玉凤就用盘子端上来一碟辣爆鸡肉。一整天来,忙活开会和对账的事情,就连午饭也没顾得上吃,他毫不谦让地拿起了筷子。就在这时,他却发现张佐铭的儿子阿里,站在炕沿跟前眼巴巴瞪着他,先是咽唾沫,接着将自个儿的食指伸到嘴里吮吸着,他立即用筷子夹了一块肉递过去。
阿里不敢接,直是往后退,两只贪婪的小眼睛,一直盯着他爹的眼睛。直到张佐铭发了准允之话,才诚惶诚恐地接了过去。孩子的这些举动,让杜石朴发现了事情里边潜在的问题。看来,张家对他的招待该下了多么大的狠心,竟然到了捏住自己孩子咽喉的地步。
杜石朴啃着一截滑油油的鸡脖子说:“海文打架这件事总算处理了,差一点翻盘子了。”
“你把那块鸡骨头放下,吃这块软的。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有情后补吧。”张佐铭给杜石朴夹了一块软腾腾的鸡大腿,表达着自己的激动心情。
杜石朴干脆放下筷子,去啃那截鸡脖子。逼着张佐铭不得不把那块鸡大腿放回到原处。他心里想,我怎能吃那块软肉呢,那是我拿筷子时候就给父母瞅准的。他边啃鸡脖子边道:“话不能这么说。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把姓海的尕娃整治整治,不然,队里的事往后还怎么管呢。”
“唉,说起现阶段你我做这种官,也真够窝囊与寒心的。对不听话的人,打不得、骂不得,也斗不得,想不打、不骂和不斗,盼着人们都顺顺溜溜干活吧,可这生产队里的经济收入,又像是个要哪样没哪样的丑媳妇——一点儿也不吸引人。”
“这光阴真叫人难以捉摸,把我们手里的鞭子收掉,还叫我们赶这沉重车,我们不舍生忘死,这车还怎能往前走啊?”
“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哎,你估计海文还告不告?”
“告到哪里我也不怕,你有病住院都是确凿的事。”
“听阿里他妈说,会上姓海的说了我住院时候夜里拉坷垃的事。”
“你到底拉了没有?”
“拉,拉了。”
“你,你怎能做出这种事?”
“家里活太多,我在医院里躺不住。”
“难道你真的没病?”
“有是有,没那么严重。”
“啊,你怎么讹人呢?”
杜石朴本以为,张佐铭果真被人打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今天的大会上,才硬逼着姓海的一家,往出拿杂七杂八。不受严厉整治,海文又怎么能改邪归正。没想到,张佐铭正是会上人们揭露的那种恶心人。这样一想,立刻觉得吃这鸡肉也成了可耻之事,赶紧撂下鸡骨,下炕去穿自己的鞋。
“刚吃了没几口,你怎么又放下了?”
“你们这样做事,叫我还怎咽得下去呢?”
“这也是被海文那伙人逼出来的嘛。”
“你拉坷垃的事,谁见了?”
“你家的两个女儿。”
“海文是从哪里知道的?”
“我估计是你家英英说的。”
“不可能!”
窘迫中,张佐铭想大献好心,以便扭转局面:“你可知道,海文对你家阿依莎一直谋心不善哩。”
“你快不要借风扬场了吧。”他不想牵扯这种事情,怒气冲冲走出张家门的时候,又转过身来强调说。
张佐铭边拦边劝:“有话坐下慢慢说嘛,你炸了肝肺做啥?”
“事情已经做到了这种份儿上,真叫我骑虎难下。队长竟然支持副队长讹社员,这话传开了,让我这老脸还往哪里搁啊?你快让开路吧,我家里还有急事呢,得赶紧回去处理。”他轻轻推开拦在前边的张佐铭。
仍是一如既往,保玉凤用小塑料袋装了些软活鸡肉,追上来给杜石朴往手里递着:“带回去,敬奉老人。”
“今天,我家里也宰了鸡呢。”他连连摆着手,说过之后,扬长而去。张家夫妇俩一直追到院门口,见到的却只是被他那匆忙身子搅动了的弥漫在地面上的炊烟。
忽而,那烟云深处又传来了杜石朴的声音:“你家姬丽哈到公社看电影去了,是我同意的,有女伴儿呢,回来之后,你们不要审喝。”
那么大的姑娘,黑天半夜到公社去看电影,也不给家里的父母提前打一声招呼,万一遇上坏人怎么办?一直沉浸在侍候杜队长的气氛中,张家夫妇竟然连女儿姬丽哈去了哪里,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听到杜石朴的叮嘱,这才一边向公社那边张望,一边在心里埋怨女儿是个没家教的贼胆子货。
阿里趁爹妈抬脚出门的当儿,匆匆饮尽了碟子里的鸡汤之后,在爹妈跟前蹦来跳去。他想,姐姐今晚回来,不知该有多少生动故事要给自己这个弟弟讲述呢。然而,俏皮的阿里却万万没有想到,有些生动的故事,姐姐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讲的。
那阵张丽丽离开庄子之后,一直隐蔽在路边的树后,心荡神驰地等着马贵到来。见他迟迟不来,心里便犯起了嘀咕,怕他以为自己不去,会独自前往。一旦那样,可千万不能耽误了开演时间,她立即摸出马贵塞给自己的那个票团,想看清楚开演的准确时间。打开之后,却一下子怔住了。这哪里是什么电影票啊,而是用圆珠笔写成的一张小纸条:
你的眼神,
让我心灵颤动;
你的声音,
让我生命飞升;
你的气息,
让我醉死梦生;
你的感情,
让我坚守一生。
吟罢来,顿时觉得从脚指头蛋儿到头发梢梢,都禁不住微微颤栗开来。光阴仿佛又回到了她和马华说情话儿的那个月夜。朦胧之中,她依稀觉得,身旁不再是什么冷清之树,是马华兄长与她一起重演那个月夜里的一切,她将自己娇嫩的身子偎依到了对方那汗涔涔的胸脯上。
十九岁那年,爹妈就做主给她订了婚。对象是城里商业单位开卡车的一位合同工。那时,她特别憨,见人家驾着方向盘来了,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运的女性,往后就可以跟着对方满世界去风光,还敢再挑剔什么?后来,人家方向盘抓牢固之后,开始嫌她家穷,也怨她没女人的趣味与气质。订婚时轰轰烈烈,整个梨花湾都扬了名,退婚的那天,家里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寒霜打蔫了的野蒿子。
知情明理的人,责备男方太不地道;搬弄是非者,说她本身就有缺陷;甚至还有人猜测,可能是她不怎么检点,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爹当副队长这些年,惹下的人真不少,好不容易才抓到了这个把柄,借风扬场、加油添醋当大戏来唱,把她损得一钱不值。远近想求婚的人,真假难辨,再也不愿上门来搭话。自己心比天高,命却只有纸薄。二十几岁的人了,惟有那个月夜里感受过马华的爱抚。
夜色渐渐暗了下来,四周已经没了一丝声响。以往,天黑时候出院门,她一直特别害怕,总要疑神疑鬼。此时此刻,却不知道什么叫胆怯了。仿佛浑身的每个细胞都是铜浇铁铸的。寒风不时地刮着,她穿得很单薄,但也不知什么叫冻了。青春时期的痴痴诚诚的爱啊,仿佛可以弥补世间所有缺憾似的。她正觉得冷清与寂寞,马贵从黑暗中气喘吁吁地钻了出来,将一件女式短大衣披到了她的肩上。
“姬丽哈,给你披上,天太冷了。”
“谁的?”
“管它谁的呢,合身吧?”
“还好,那你呢?”
“这不,我穿得特别厚实。”
“你怎么哄人呢?”
“这话啥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
“先前那阵,你给我的是电影票吗?”
“当然是电影票啦。”
“哼,还想继续欺骗呢。”
“真的没有啊。”
“是你写给谁的诗吧?”
“哎呀呀,可能是我掏错了口袋,票还在我的身上呢。怎么搞的,竟然把那首诗送给你了。”
“谁写的诗?”
“是我的一个女同学赠给我的。”
“是不是杜英英?”
“这个先暂且保密。”
“这么说你已经有对象了?”
“才打算谈呢,还没决定下来。”
“我还以为是你写的诗呢。”
“你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
“那我就送给你吧。”
“怎么拿别人的诗送人?”
“其实,那是我最近创作的。”
“谁信呢?”
“刚才是想和你开个玩笑。”
“我不信。”
“你想,女人能写出那么阳刚大气的好诗吗?”
“你写给谁的?”
“当然是写给你的。”
“你让我的心头热乎乎的。”
“这也是我最盼望的呀。”
“你可真坏!”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咱们不能光顾说话,别把看电影的事情耽误了。”
“谢谢你的提醒。”
“你说晚上八点公社演电影,我站在这儿等了好大工夫,怎么路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大概他们还没得到确实消息,再说这票特别不容易搞到。咱们走快点吧。”
“若是看半截电影,那就太可惜了,咱们边走边说吧。过去你经常和杜英英一起走路,一起干活,一起说话。这次和我一起看电影,万一让她知道了,生起气来该怎么办?”
“她活该生,这些日子,我不想理睬她了。”
“谁信呢?”
“以往,我之所以和她亲近,因为我们是同学,中学时候还在一搭里演过节目。近来,我才发现,她的心术不正。别的先不说,就论谈对象的事情吧,我要是韩大林,她白送给我,我也不会要。”
“为啥?”
“水性扬花嘛,见海文回来了,又想和人家好呢。”
“看来,你还挺有眼力的。”
“你的亲事,怎样了?”
“八字没见一撇呢。你的呢?”
“也没有。你打算怎么办?”
“没合适的,就独身到老。”
“我和你想得一样。不过,若那样,咱们就吃了大亏。”
“没那么严重吧?”
“李大钊先生曾经说过,‘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强制它,侮辱它,污蔑它,屈抑它,使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
“你再说一遍,让我记一下。”
“以后再给你说。鲁迅先生也说过,‘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萎落,甚至于变态。’”
听罢之后,她突然觉得,两位伟人的话,好像正是说她自己。以往,她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些人说话或作文章,总要运用一些名家名言。以为有了那样一种借助,定会水涨船高地显示出自己的学养来。她却觉得,那是一种无能和卖弄。一个人有无水平,水平高低,若是懂行的人,仅从对方的眼神、行为、姿态和简单的对话,就可以看出来,绝非出自狐假虎威或装腔作势。今晚,她却觉得,马贵引用名人名言的做法很合适,至少说明他读过一些上档次的书,也很有鉴赏力,更能应用自如。
“你觉得,啥样的人,才适合你?”
“活人不窝囊,看着顺眼,在一起过光阴心里不别扭就行。”
“哎,公社大院里怎么一片冷清,好像啥电影都没演似的?”
“姬丽哈,你骂我吧,打我吧。”
“你怎么啦,好像突然间得了神经病似的?”
“今晚公社是没有在银幕上演的那种电影。”
“那你为啥说,演的是意大利的《求婚》呢?”
“其实也不算真哄你,你和我演的,不正是‘一搭里’的‘求婚’吗?你看,我这个人合适么?”
张丽丽顿时醒悟了,真没想到,马贵用谐音一搭里和求婚二字组合在一起,将自己巧妙地捉弄了一番。立即捏起拳,正准备狠狠擂他的背,他却屁颠屁颠地跑了,黑暗中还嘿嘿嘿地笑个不止。声音不大,却震撼得整个夜空仿佛都在怪味十足地颤动。猝然,他那笑声戛然而止了。原来,就在马贵狂笑之时,嘴边发出了好似爆竹般的两声脆响。她正觉得疑惑,那边传来了不堪入耳的辱骂:
“马贵,你这驴婊子养的,还是先尿泡尿,照照你那老汉相吧!”
“张队长,我没干啥坏事呀,你可千万不能误会啊。”
“还犟啥,你把眼窝揩干净好好看看,我们家是啥皮毛,你们家是啥皮毛,还想把我家的娃往火坑里带吗?”
张丽丽立即听出来,是自己老子的声音。意思是说,其他权且不论,主要还是两家成分之间的差别太大,政治条件相距得过于悬殊。若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一旦成立,就会使自己的女儿深受其害。当然她能感觉出来,爹说的倒是这个年代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俗话所说的“叫花子捏泥鸡”,是被生活逼出来的一种见识。
又是两声爆竹脆响之后,就听见马贵往出吐着什么,一口继着一口的。张丽丽正想走上前去为马贵求情,忽然听到之前传来说话声音的地方,又响起了一阵阵脚步声,哒哒哒地,接着又是两个人的,像是一个人在追另一个人。声音越来越激烈,随之又越来越远,最终却让此起彼伏的犬吠声吞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