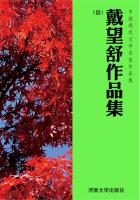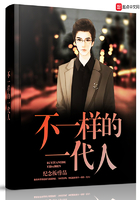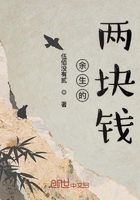宝玉不长进,尤其不喜欢读书,还不喜欢与那些当官作宰的多联系,整天在女孩堆里混,赖嬷嬷仗着自己的老脸,先就瞧不上他“扎窝子的样”,连湘云都说“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的出些什么来?”湘云的功利心是高了点,可在那个年代不读书上进求仕行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真到了顶门立户过日子时,可就麻烦多了,养家糊口都是问题。湘云只是劝劝,人家已经是名花有主,反正以后又不跟他过日子,爱听不爱,真正焦心的是做家长的贾政。
贾政的着急缘于还指望着这个儿子有出息,将来能光宗耀祖。若是根本不想培养成接班人的人,也看不出焦急来。比如对于贾环,看他跑来跑去不像大家子弟的做派,跟宝玉一对比,又觉得这小子长得也拿不出手,便放弃了选择,独守着老太太喜欢的这根苗,盼着它长成大树。对于贾兰这个孙子,隔了一层,到底不如培养儿子直接受益,血缘关系更近些。
贾政一直创造条件想把宝玉推到众人面前,每次会客都是叫了宝玉来。只是他不理解这个儿子,也不想去理解,他只想以家长的权威逼迫他就范。而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宝玉对此极为反感。宝玉对待红颜褪尽已是抱孙子年龄的奶妈远没有对待自己屋里莺声燕语的小丫鬟们好,李嬷嬷算是白喂了这小子好几年奶,他也没把自己当娘看,本想提老爷的名号吓唬吓唬他,他反倒嫌了。但宝玉虽然叛逆,却没有彻底叛逆,他还遵从封建礼教那一套,别以为老太太是无条件喜欢这个宝贝孙子,那是因为老太太看透了宝玉,她对甄家媳妇们说:“就是大人溺爱的,也因为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给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贾政气急了,说宝玉将来还不得杀父弑君,这话真说重了,宝玉见客时何曾不规规矩矩的呢?就是不当着贾政,路过父亲的书房时也要主动下马步行以示尊重。
其实宝玉并非完全不肯读书,也不是什么才能都没有。宝钗说他“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这“杂学旁收”就是读书杂,知识面宽,什么都懂点,也就是杂家。宝玉的书法也不错,路上遇到两个清客相公和七个管事的头目,他们因在好几处看到宝玉写的斗方儿,“都称赞的了不得”,便向宝玉也讨斗方儿。连黛玉看了他写的“绛芸轩”三个大字,都称赞说:“个个都好。怎么写的这样好了!明儿也替我写个匾。”宝玉在诗词对联上更是出色,但因宝玉的这些才能不是“正经学问”,在贾政看来不过是“精致的淘气”。若在现在逼着孩子练书法、弹钢琴的家长看来,说不定这宝玉还让家长感到欣慰呢。
两人的分歧在于读书的目的不同,宝玉只为娱乐,贾政为的是应试考试,应试的背后是仕途经济,袭人对此的理解通俗明白:“念书是很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辈子了,终久怎么样呢?”宝玉没想那个“终究”,贾政为他想到了,当然着急。
父子关系一度极为紧张,宝玉虽然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但见了父亲还是吓得战战兢兢的,甚至平常听不得“老爷”二字。宝玉和黛玉到梨香院看望生病的宝钗,他的奶母李嬷嬷说了一句“你可仔细今儿老爷在家,提防着问你的书!”的话,宝玉立即蔫了。还是黛玉抢白了老婆子一顿,薛姨妈又哄了一番,这才重又提起兴致来。但回到家时,宝玉还是忍不住先在贾母面前告了李嬷嬷一状,说她比老太太还享受呢,又借着一碗枫露茶大闹一场把气撒出来。这一切,表面是对李嬷嬷的不满,其实暗地里是针对压制他的贾政的。贾府中奶娘的地位半高不低,被奶过的公子小姐却要尊重奶娘。贾琏的奶娘赵嬷嬷在贾琏那里,是与贾琏凤姐一块吃饭的,那凤姐还特意把早晨炖得软软的猪蹄给她吃。但是无论怎么说,奶娘也是下人地位。赖嬷嬷那么大岁数了,孙子都当了县官,但在贾府也还主动按规则办事,时刻注意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但偏偏李嬷嬷年老昏聩,整日唠叨,还搬出贾政来吓唬宝玉,让宝玉怎能不反感呢?
父子之间没有亲情,只有怕。不止宝玉怕得要命,那贾环因不受待见,见到贾政更是吓得骨软筋酥。贾环一被吓就吓得进了谗言,致使宝玉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打。宝玉虽然也害怕,但在大观园题对额时,却不顾贾政的不断呵斥,到底把自己的见解与文采表现出来。环玉二人的高下立见分晓。
贾政对宝玉的态度因了元春的关爱有所改善。二十三回,元妃省亲后,命众姐妹和宝玉到大观园居住,把家人叫了来开会。贾政看到宝玉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又看看贾环人物委琐,举止粗糙,意识到王夫人只有这一个儿子,因此上把平日嫌恶宝玉之心,减了八九分。父子关系后来也有了改善。但宝玉不学好,竟敢招惹贾政都要毕恭毕敬对待的南安府的戏子,差点连贾政都给拖累了。又有金钏被“因奸不从被逼死”的大罪,贾政这时对这个儿子已经失望气愤到极点,差点把他打死,亏了老太太不问青红皂白地保护,宝玉才拣了条小命。不过这一件事使得贾政后来再不敢轻易下手了,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省。再加上后来又赴外任,“因年景渐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离异,今得宴然复聚,自觉喜幸不尽。”生命日渐走向衰老之际,使人看到了碌碌人生的虚妄,斤斤于眼前利益,也无法改变人生的最后结局。也许此时再来看当初的努力上进,到头来不过如此。贾政以这样的灰心的状态,这时看到宝玉进来请安,心中自是喜欢。对于儿子的功课,也只是“自然问问”,再没有从前的苛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