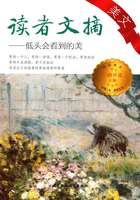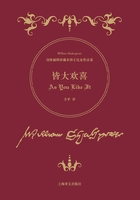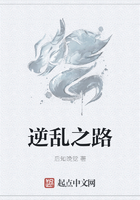尽管大观园女儿个个有其可爱之处,但每个人又都是不完美的。宝琴一来,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喜欢,贾母立即逼着王夫人认了做干女儿,还让她跟自己一起住。下雪天送她一件连老太太“这么着疼宝玉,也没给他穿”的野鸭子头上毛做的“凫靥裘”,连一向“小性的”黛玉,也赶着叫“妹妹”,一点也不忌妒宝琴得到多于自己的宠爱。难怪宝钗连着两次感慨:真是各人有各人的缘法,我就不信我哪点不如你?宝钗一向是“总依贾母素喜者说”的,可始终没见贾母这么爱怜过自己,也算是有感而发了。
也是奇怪,虽说宝琴长得可人儿,可也不一定真比宝钗漂亮到哪去。所以袭人听到人说来的几个女子都很漂亮,就说还能怎么样呢?都是青春妙龄的女子,美丽当然是美丽的了。但宝琴的突出可能正如宝钗所说是各人的缘法。贾母的评价基本观点也是:宝琴配上那件衣服,才那么出众。这话当然透着贾母的得意,因为那件衣服恰是她送给宝琴的。那么是这衣服衬托了人?别人穿上也会这样?湘云又说了,“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别人穿了实在不配。”也就是说,她的气质最适合这样的打扮。
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背后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贾母喜的忙笑道:“你们瞧,这雪坡儿上,配上他这个人物儿,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象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象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的‘艳雪图’。”仇十洲是明代画家,擅长人物画,尤工仕女图,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他本人出身寒微,与明四家中的其他三人皆出身为书香门第不同,但他的画却追求文人画的风格,有儒雅飘逸之气,带有文人情趣与思想,是所谓的文人画。近代著名画家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曾提到一个观点:“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贾母的欣赏品位已是不俗,她对大观园里的画家惜春说:“第一要紧把昨儿琴儿和丫头、梅花,照样一笔别错快快添上。”这是很有道理的,不然大观园只照原样画园子,那和设计图有多大区别?那么,宝琴的入画,其实是有着贾母的主观愿望在内的。
贾母生活在由繁盛走向衰败的过程中,凭她的经历,她一定感觉到了这种无可逆转的趋势。但她只能抱着幻想,或者希望延续它的繁盛。她对宝玉的异常宠爱,除了宝玉身上有当年荣国公的影子外,恐怕就是只有这个孙子还不算坏。她希望贾家永远留住这一场富贵繁华梦,永远不要在梦里醒来。她已经到了喜欢听吉利话的年纪了,她在玩牌时不是在乎输赢的那点小钱,而是在乎那个赢了时的“彩头”。此时,宝琴与这个富丽堂皇的园子间的意境重合,使她对这幅图画有了一种心理上的亲近,从而使她对画中人更增好感。宝琴的光彩也是她站在冬日的银装素裹的山坡上,一片清洁空旷的诗意雪景之中,在梅花的陪衬下,才显出那份不同凡俗的艳丽来,也只有身后的小丫头抱着瓶儿,才显出富贵来。若是只琴儿一人站在雪野中,就有点像宝玉披了猩猩毡站在雪里,多少会显出些末世的凄凉与孤独来。
宝钗只有在贾府衰落后才会显出她的珍贵,她的朴素与周到,算计与安排,只适合计算着过的日子。但此时还用不到,大观园华丽的气氛只有宝琴的气质最相配,那样一种安然的富贵气,那样一种不与人计较的从容。这种气质只有鼎盛时期的自信与财富充裕背景下才能衬托出来。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有这样安富尊荣的自得,才能培育出这点发自天然的纯真、娇憨、不谙世事的气质。何况她从小跟父亲走南闯北,走了大半个中国,在那个时代可谓见多识广。这样的女子又怎么是囿于深闺庭院拥挤狭窄的目光中走出的女孩可比呢?
宝琴还有单纯。宝琴的单纯在于她的头脑中根本没有那个礼教的影子,她写了十首古迹诗,其中有两首涉及到了禁区。其一是《蒲东寺怀古》:
小红骨贱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
诗中提到的蒲东寺,是唐代元稹的传奇《会真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人物张生和莺莺相会、相恋的地方。从诗句所写来看,所怀并非蒲东寺,而是为张生和莺莺私相传递信物的红娘。诗中“骨贱”、“勾引”,用词粗鄙。
另一首《梅花观怀古》是这么写的:
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
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
这首诗中的梅花观,是指《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因游园惊梦,梦中遇到柳梦梅,后因相思而病而死后,她的父亲为守护其墓而建的一座庙观。这两首无疑都与爱情有关,而且是自由的爱情选择,与传统的道德理念相悖,这种行为在现实中是为时人所不容的。黛玉在夜宴时曾不小心说了《西厢记》里的“艳词”,犯了大家闺戒,宝钗抓住这点教育了黛玉一番,而黛玉竟然心服口服起来。但宝琴公开写的两首诗,问题要比黛玉所写更为严重。因此,宝钗听后,假装不懂,宝钗虽也想教导她一番,反被众人批评。其中黛玉最先发起攻击,接着探春李纨等表示了支持。在别的女子就是有伤风化的事,在宝琴这里成了公然允许的行为。
宝琴一副天真无邪的女儿之态,正因为这样,没人怀疑她会有不洁的想法,更不用说行为了。她不矫揉造作,芦雪庭大家烧烤鹿肉吃,宝琴看着说怪肮脏的。湘云叫她傻子,宝钗说你林姐姐吃了不消化,不然她也爱吃呢。只这一句,宝琴也不嫌肮脏了,加入了吃的行列。芦雪庭联诗,宝琴显示了她的诗才一面,但这一章主要还是才思敏捷的史湘云占了风头。每个人似乎都沾染了或多或少人世的尘埃,她们在这处还未被污染的纯洁的女儿身上,看到了女儿纯洁的本质。
宝琴仿佛一个意念中的人物,一个虚幻的影子,她在红楼梦中其实是没有什么故事的。原本贾母说要给一个人婚配,把她拉入现实,可是却借一句已经许了人家,把这事轻轻放过。生活中有多少人是完美的呢?只有宝琴这样一个游离于世事之外的人物,连十二钗都没入。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入世,便会多少沾染些尘世的东西。黛玉追问她讲述的那个外国女子的诗稿时,她却撒了“在南京收着呢”一个小谎,又被黛玉快言利语地说出来。宝琴还没学会如何应付世上性格差异的人,宝钗两个人都批评说:“偏这颦儿惯说这些话,你就伶俐的太过了。”其实如宝钗一样实说“箱子笼子一大堆,还没理清呢,知道在那个里头呢?等过日子收拾清了找出来,大家再看罢了。”也就行了,没人非逼着真的立时拿出来。俗世中的人都是有缺点的,连黛玉宝钗这样出色的女子都是,她们被人们喜欢或者不喜欢。能让所有人都叫一声好的,只有画中人。不过,《红楼梦》是不准备把宝琴拉入凡俗的,她只能停留在那幅美艳的画里,保持着不染凡尘的清洁与娇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