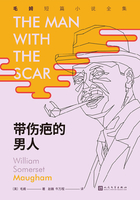旅馆有四个老板娘,都是中年女人,她们在来到大理之前彼此并不认识。其中一个老板娘姓郑,住店的客人无论长幼都叫她郑姐。郑姐年纪不到四十,湖北人,五年前离了婚,孩子判给了前夫,她自己一个人跟朋友出门散心来到大理,从此再也没离开。郑姐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起床后跟一些同样赖床的住客们一起吃早饭,然后靠在院子里的沙发上抽烟。她每天都穿不同的花裤子,都是一样地宽松,都绣着云南少数民族特色的图案。天气微凉时,她会披一条摩梭族的手织披肩在身上,像一只花蝴蝶。她无论走到哪里都只穿拖鞋,她的脚长得很美。苏凉问郑姐可不可以给她的脚拍张照片——令苏凉意想不到的是,郑姐甩掉拖鞋,直接把花裤子也脱下来,露出里面贴身的小短裤。当时院子里还有其他几位住客坐在一起乘凉聊天,郑姐当着众人的面,在院子中央优雅地转了一圈儿,欢快地对苏凉说:“连我的腿也一起拍进去吧,我的腿长得也好看!”几位住客先是愣住,随后马上异口同声地赞扬起郑姐的一双美腿。郑姐得意洋洋地说:“去年有一个画画的说想画我的脚和腿,我直接把屁股也借给他画啦!”住客们跟着郑姐一起没心没肺地笑,郑姐爽朗的笑声和肆无忌惮的眼神竟然让苏凉不好意思起来。
“你们这些搞艺术的啊!看谁都美,还从来不说人美,只说具体某个部位美——老实交代吧!你靠这一招儿骗过多少小姑娘啦?”
郑姐调侃苏凉时的笑容尽显妩媚,岁月的痕迹仿佛在她的脸上消失殆尽。苏凉猜想,这个女人在多年前离婚出走时,绝对不曾想过自己会像今天一样快乐吧。
“我喜欢这里,”苏凉抬头望着小院子上空四方形的天,“真想留下来。”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郑姐沉寂下来,点燃一支烟说,“不光是你和我,曾经有无数过往的旅客都这么想过,可是真正有几人留下来呢?绝大多数人都是来大理旅游、散心、度蜜月,忙里偷闲还没等沉下心来好好享受这里的空气和日光,就又要赶回去匆忙地过生活,一晃几十年过去,理想就永远成了理想。有时候,实现人生理想不仅要靠决心,还要狠心——大老远跑来这里过悠闲日子,父母呢?工作呢?孩子呢?谁能割舍下这些平凡人的牵绊?我当初是刚好被迫割断了这些牵绊,否则一个平常的女人怎么可能会跑来这里过日子?那还不成了疯女人!再就是需要钱,还记得当年有首老歌叫《我想去桂林》吗?”郑姐随口唱了起来,她的声音很沙哑,“‘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时间我却没有钱’——唱得多实在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当年我只有三万块钱,好在找到几个疯女人一起合伙租下这套房子,算我有福气!当年我起码明白一个道理:等到钱和时间都有了的时候,我他妈早就老啦!不过你这么年轻,选择过怎样的日子,将来后悔都来得及,如果真想,就留下来,人和水土之间也是讲缘分的。”
“那我就在这条街上再开一间旅馆,跟你抢生意。”苏凉笑着打趣。
“我才不怕你哩!”郑姐飞着眼角,自信满满地说,“就怕你待不长久!多少人都试图在这里扎根,可是没两年都走了,不是生意赔本,就是忍受不了单调,第一眼的新鲜劲儿一过,就又怀念起大城市的喧嚣繁华了,就跟爱情一样。我怕你待不了几天就会想家,想女朋友,到时落荒而逃!”郑姐笑着看苏凉。苏凉摇头说:“放心,这些牵挂我都没有了。”郑姐挑了一下眉毛,忍住没多问,只是媚笑着说:“那倒好,留下来陪姐姐我解闷儿,也好多个聊天打牌的人!”
“开旅馆太操心,”苏凉思索着说,“我想开一间酒吧。”
“洋人街上遍地都是酒吧,再说开酒吧成本高,没有经验容易赔钱,”郑姐好心劝解,“你还是干点儿别的吧。”
一个月后,苏凉在大理古镇开了一间咖啡馆,距离郑姐的旅馆不出一百米。
开店的房子是一家出租的老旧民居,单层附加阁楼,租金每年七万五,苏凉一次性签了两年。装修费花了三万,六月中旬开张,主要卖咖啡和茶,晚上八点以后也会卖啤酒和简单的调酒。苏凉既是老板,也是店员,只雇了一个当地小妹帮忙。
装修接近完毕时,装修师傅建议苏凉给后窗装一个防盗铁窗,因为古镇有段时间晚上常有小偷出没,专偷一些防盗不严的商户。苏凉听后并没表态,师傅有些羞涩地说:“我也只是提个建议,没有想坑你钱的意思,主意还得你自己拿。”苏凉觉得师傅不容易,点头答应了。防盗窗就是最简易的那种由横竖几条细钢筋焊成的铁网罩,直接罩在窗户外面,用射钉枪钉上四个角。
晴天下午,苏凉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顶着大太阳看几位工人装铁窗。工人们以为苏凉是在监工,干得异常认真,其间没有扯一句闲话。但苏凉没有在监工,他甚至没有在看面前的这个防盗窗。
苏凉想起的是二十年前的另一扇形神俱似的铁窗。
那时苏凉刚满四岁,夏日清晨,父亲苏敬钢带着他从花鸟鱼虫市场逛回来,刚刚进到自家小区院门,见到十几位邻居正围在一楼防盗窗前,热议着什么,人群中间是住在一楼的大姐,看上去心急如焚。苏敬钢牵着苏凉走上前询问,才知道当天是高考第一天,大姐已经把女儿送到考场才发现准考证落在了家中,急忙赶回家后居然发现门钥匙被反锁在家里。邻居们要打电话叫开锁的人来,大姐说来不及了,马上要开考了。夏天,铝合金拉窗没有关,透过防盗铁窗,众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串钥匙就摆在茶几上,望眼欲穿,却无能为力。大姐急得号啕大哭,不停地用双手狠狠抽自己的脸,拼命骂自己:“为啥要装这防盗窗?我他妈当初脑子叫驴踢了!为啥就今天忘带钥匙?我他妈该死!我把我女儿给坑了……”大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瘫坐在地,邻居们赶忙上前搀扶并安抚,却都苦于帮不上忙。苏敬钢独自走到防盗窗前,一只手攥住一根钢筋摇了摇,朝屋内眺望一眼,回身拉过小苏凉,蹲下身子问:“儿子,这个阿姨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你够不够勇敢,跟爸爸一起帮阿姨一个忙?”小苏凉的大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点着头,大声地说:“勇敢!”——“真是我儿子!”苏敬钢对儿子竖起大拇指,“男子汉!”
苏敬钢回到铁窗前,双手紧抓住两根相邻的竖排钢筋,双臂使劲儿一用力,手臂和肩头的青筋暴起,只见两根钢筋被一点点掰弯,缝隙越来越宽。围观众人大惊失色,全都聚拢过来给苏敬钢加油打气,大姐也激动地从地上一跃而起,瞪大眼睛在旁傻看。苏敬钢裂开嘴大喝一声,缝隙被扯成一个狭窄的洞。苏敬钢松开手,喘了口气,高举起小苏凉把他递到窄洞前:“儿子,钻进去!”四岁的小苏凉比同龄的孩子瘦弱许多,单薄的小身子轻而易举地钻过窄洞,头却被卡住,他再一使劲儿,疼得叫了出来。苏敬钢连忙张开手,继续掰两根钢筋。两个男性邻居上前帮忙推小苏凉的屁股,嗖地一下,小苏凉像条小泥鳅滑进了洞里。“从窗子跳进去!”苏敬钢在身后指挥。小苏凉跳进屋里,只听见阿姨在窗外跳着脚大叫:“钥匙在茶几上!”小苏凉遵照指挥拿起钥匙,回到窗前,踮着脚朝窗外喊:“是这个吗?”——“是!是!小祖宗快出来吧!”大姐再次喜极而泣。小苏凉个子矮小,够不到窗台,他在屋内转了一圈儿,搬来一把凳子,踩着凳子爬上了窗台。邻居们在窗外异口同声地赞叹:“这孩子真聪明!”苏敬钢眉飞色舞地说:“我苏敬钢的儿子还用说!”他两手架着小苏凉的两只胳膊在空中举着,父子俩对望着笑。大姐接过钥匙,含着泪说:“你们爷儿俩就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她话还没说完就骑上自行车飞蹬出院门。
苏凉记得那天的阳光,跟此刻的阳光一样灿烂、耀眼、炫目,普照他的童年。
苏凉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崭新的、在大太阳下闪着银光的铁窗,仿佛回到了四岁的那天,他仰起脖子仰望着父亲高大威猛的身躯、手臂上黝黑健硕的肌肉和执着刚毅的脸。
那一刻的父亲,在苏凉的心中,是英雄。
那天,父子俩带着凯旋的心回到家。小苏凉蹦跳着回到房间,抬头一望,糠皮芯儿枕头还直挺挺地悬挂在木门框上。“爸爸,我要练撞羊头!”小苏凉跳着用头撞了一下枕头。苏敬钢在身后看着儿子兴奋的样子,笑着说:“妈妈和姥姥不让练,咱就不练了!”小苏凉表情沮丧,口气遗憾地说:“你还没给我表演过撞羊头呢!到底有多厉害?”苏敬钢站着想了一会儿,说:“爸爸给你表演比撞羊头更厉害的好不好?”说罢,他将儿子拉到自己身边,抬起一只手收进腋下,猛地一出拳,沉甸甸的枕头从门框上横飞出去,在房间的上空爆裂开来,棕黑色的糠皮芯儿飞散整个屋子,像一朵绽放的礼花。小苏凉拍着手高呼,被父亲一把抱起来,他记得父亲脸上的笑容恬淡,他听见父亲在他的耳边说:“儿子,你将来一定比爸爸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