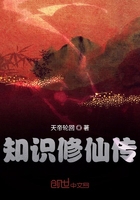苏敬钢不解地问:“你买钢琴干啥?你教的那些孩子家里不是都有钢琴吗?”“我买给自己。”“买来干啥?”“弹!”“废话!”苏敬钢积压着的一夜未眠的怨气被激起,大声地说,“你是不是还做明星梦呢?”左娜一下子被激怒:“我自己买!不用你的钱!这辈子我不能上台唱歌,还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吗?你可以去外面花天酒地,我在家给自己找点儿乐子都不行吗?”——“我花天酒地个屁!”苏敬钢瞪起眼睛说,“我干啥啦?”左娜挺直腰杆说:“你隔三差五去歌厅玩儿,以为没人知道吗?我瞧不起你!”苏敬钢后背一阵冷汗,喘了两下,胡乱挥舞着手说:“现在知道瞧不起我啦?早干啥来着!我是配不上你,你高雅,你有文化,你有追求——我他妈就是庸俗!我为啥去歌厅?因为我有一帮庸俗的朋友!你以为开出租车是啥俏活儿啊?公司里一共没几个人,现在都快走光了!别家公司给的钱多,我跟冯劲给不起那么高的工资,司机都跑了,不然用得着我这么没日没夜地熬嘛!留下的再不对他们好点儿,谁还愿意跟着我们干?以前供饭供酒不说,现在还得陪喝陪玩儿,清明节完了是劳动节,别人都放假在家歇着,司机不能,就指着这几天上街多拉几趟活儿呢!大过节的不得犒劳一下吗?人家提出来去饭店就得陪着吃,人家要去歌厅就得陪着玩,我有啥办法?”苏敬钢喊得大声,左娜却丝毫不怕,吊起嗓子跟苏敬钢对着喊:“我就每天在家里好吃懒做吗?对!就你有道理!就你有苦衷!就你够朋友!”
“少他妈讽刺我!”
苏敬钢少有地对左娜说粗话,累积在他心底的愧疚再也压制不住,随手抓起桌子上的茶壶向身后甩了出去,正砸在卧室房门的玻璃上,玻璃碴子与碎瓷片交织着散落满地,他大声吼着:“我够个屁朋友!连我兄弟死了都会记恨我!”
左娜不作声了,她被空气中爆裂的脆响吓得发抖,眼泪止不住地掉。她瘫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说:“我知道,因为大昆的死,你记恨我,可我做错了吗?如果那天晚上我放你去跟人拼命,这个家今天还在吗?我不想让我的儿子从小就没爸,也不想让我儿子的爸在监狱里待一辈子——我有错吗?”
左娜哭得两手发抖,滚烫的泪水从她刚刚扑好的粉底上划出两道泪痕。
西元1988年初,大昆刚刚能够坐上轮椅后,染上了毒瘾。
也不知道他是通过谁认识了几个混在西塔的朋友,常来他的麻将社打牌,不只是照顾生意,是因为大昆的麻将社可以赌钱。刚开业那段时间,大昆还从不从中抽水。论起这座城的市井闲杂,西塔不能不说,那里早年是朝鲜族与汉族的杂居地,朝鲜族为多。在地上,那里有全城最好的烧烤店、冷面店、韩式桑拿,但在地下,歌舞厅遍布暗娼,毒品也是从这里开始,向这座城最早期的娱乐场所扩散。后来,西塔的一条街逐渐演变为尽人皆知的红灯区——直至2004年底,这座城上任了一位新公安局长,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烧在了西塔,严打黄赌毒。传说在严打的头三个月里,按摩小姐和歌厅小姐们见形势不妙,纷纷逃回周边老家,走人前,一口气把整条街ATM机里的现金都提空了。
大昆跟两个朝鲜族混混成了朋友,他们引诱大昆吸毒,他们对大昆说,“吸粉儿”可以缓解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大昆听信了。朝鲜族混混起初是送,不久便开始卖,最后变成大昆求着他们买。
大昆吸毒的事儿,苏敬钢一直以来都不知道,大昆也没敢跟苏敬钢说。大昆吸毒上瘾以后,很快花光了积蓄,开始四处借钱。对大昆知根知底的人都听说了他是借钱去吸毒,没人再愿意借,因为人人心里都清楚那是个无底洞,借出的钱有去无回。大昆毒瘾发作时痛苦难忍,手头没钱,只好拿房子抵账。可是房子给了人,大昆就无家可归了,于是他赖了账。两个混混来收房子时,大昆把他们撵走了,等他们再回来时,已经不是两个人,而是七八个人。这些人砸了麻将社,痛揍了大昆,恐吓大昆说一个礼拜后再不交房子就废了他。砸麻将社的当晚,苏敬钢接到了大昆的电话。大昆走投无路,只能跟苏敬钢说了实话。苏敬钢又气又恨,但事已至此,只能想对策。大昆说,下一次混混们会带西塔的一位大哥来,当面要他的房,如果不给,就剁他的手。
大昆对苏敬钢说:“三儿,其实我不怕,我可以跟他们拼命,反正我这条贱命也早就不值钱了,可我现在是个废人,我站都站不起来,吸粉儿吸得手连菜刀都握不住,我他妈真窝囊!这房子是我娘住了一辈子的平房换来的,我不能给他们……”
“欠他们多少?”
“五万。”
苏敬钢怔住了,在那个年头,任凭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钱没有,房子也不想给?”
大昆在电话里“嗯”了一声。
“那就只有拼命了。”
周末的夜晚,苏敬钢趁左娜在厨房做饭的工夫,翻箱倒柜地找他当年那把尺二枪刺。左娜突然进屋,苏敬钢被堵了个正着。左娜质问:“你要干啥去?”苏敬钢含糊地说:“不干啥。”左娜逼问:“你说实话!”苏敬钢扯谎说:“去楼下挖点儿土,回来种花。”——“你撒谎!”左娜上前一把夺过枪刺,用刀尖儿戳着墙上的《约法三章》说,“第一条:夫妻双方不得跟对方隐瞒任何事情,否则——离婚!”——“别张嘴就瞎说!”苏敬钢最忌讳左娜动不动用离婚作要挟,不得已道出实情。左娜堵在房门口,手撑住门框,说:“今天你哪儿也不许去!”苏敬钢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说:“我不去大昆就得出事儿!”——“你去了你就得出事儿!”左娜大声地说,“他是我男人还是你是我男人?别人我谁都不管,我只要我的男人不能出事儿!”左娜的话有理到无可反驳。苏敬钢已经火急火燎,却还要装作平心静气地说:“我保证平平安安回来,保证我跟大昆谁都没事儿,但是今晚的事儿必须摆平。”——“你这就叫‘平平安安’回来?”左娜回手“砰”地一声把房门关上,激动地说,“苏敬钢!你答应过我结婚后再不会出去干浑事儿,再不会跟社会上那些人来往,你保证过本本分分地跟我过日子,绝对不会做违法的事儿,不会做伤害家庭的事儿!你发过的誓都是骗我的吗?你是想看着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把儿子带大吗?”
苏敬钢哑口无言,直接冲上前去开门,左娜将整个身子靠在门上,一只手死死攥住门把手,另一只手举着枪刺晃在苏敬钢面前,盯着苏敬钢的眼睛说:“除非你先扎我一刀,否则你今晚别想出这个门!”
屋里的电话响了——在苏敬钢听来,那是呼救的铃;而在左娜听来,那是催命的锣。
“大昆是我兄弟。”苏敬钢望着电话,低沉着说。
“我是你老婆,”左娜也低下了声说,“这是你的家。”
苏敬钢脸上露出愧疚的神情:“男人的事儿你不懂。”
“要兄弟,还是要这个家?”左娜冷冷地说,“今天你只能选一个。”
电话再次响起,铃声更加尖锐而急促。苏敬钢伫立不动,忽然一屁股坐在床上,看着熟睡中的小苏凉,仿佛希望儿子鼻息中轻微的鼾声可以再大一些,遮盖过空气中刺耳的电话铃。左娜走到桌前,拔了电话线。
苏敬钢回想起这些,心中的怒火也熄了。
他望着窗外晴朗的天空,有些刺眼,拉上了窗帘——苏敬钢已经习惯了在清晨入睡,太亮的阳光会令他不适应。他从床头柜的抽屉中取出一张存折,交到左娜手中,说:“这里有些钱,密码是凉凉的生日,拿去买钢琴吧。”左娜接过存折,手上有些沉重。她自己心里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左娜曾经冲破阻力,不顾非议,一门心思地嫁给苏敬钢,可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的婚姻生活会走到如此境地。左娜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不久前看过的一本外国小说中的一句话:“婚姻最可怕之处,不在于彼此耗光了金钱,或者耗光了青春,而是耗光了各自对生活的理想与激情,因为理想与激情是一切爱情的源泉。”
左娜不知道自己的婚姻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可她终于明白了,爱情与婚姻是两回事,理想与现实更是两回事,彼此间的鸿沟就好像当年左娜跟苏敬钢两家之间门前的窄道,望着近,却又深得难以跨越。
多年后,当左娜已经三十四岁,即将不再受到青春和理想的眷顾时,却恰恰有一团早已熄灭的火种在心底里死灰复燃。三十四岁的左娜深知,如果自己不把身体里的最后一丝勇气拿来为终生的理想献祭,她的余生就只能被动地迎接死亡。
左娜选择了在三十四岁离开,那是一个令她终生心痛但从未愧疚的决定。在世俗看来,左娜冲动的决定是一个女人的自私、一个母亲的背叛。但是左娜明白,任何选择都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不是物质,就是情感,人生牵挂无非此两种。至于代价,无非是忍痛割爱。左娜爱自己的家庭,也爱自己的儿子,可世俗总是将一个母亲的爱等同于牺牲,而忘记了每一个母亲最初都是一个女人。左娜忍痛割爱的最痛之处,就是选择了离开后,便再不可以回来讨扰。她跟这对父子之间,从此天各一方。
左娜愿意相信,她只是把自己再嫁给了理想,把现实许配给了苏敬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