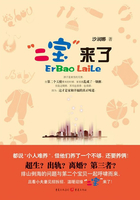西元1989年,第一机床厂的营业额每况愈下。
年轻男工人纷纷申请停薪留职,下海闯荡。苏敬钢也曾被冯劲叫去参加过几次酒局,认识了一些私营业主,大部分做生意已经发了家,他们劝苏敬钢尽快从厂里出来,跟他们一起下海经商。
“你是你们厂的销售科长,没人比你心里更清楚,这座城里当年全国闻名的几家大工厂如今有哪家还在赚钱?经济发展这么快,重工业已经没落了,全国人民都在搞合资企业、对外贸易,老外出钱我们出力,就算是赚辛苦钱也比厂里给的工资多十几倍。”冯劲不止一次苦口婆心地为苏敬钢“解放思想”,他自己早已经把物资局的铁饭碗当成闲职,“以前搞贸易那叫投机倒把,现在那叫互通有无!咱们远的不说,搞边境贸易我们有优势——俄罗斯啊!我那几个朋友拿收音机和卫生巾跟大鼻子们换机器和汽车!你敢相信吗?”——“合法吗?”苏敬钢每每都是这一句话,气得冯劲恨不得撬开自己的脑子给他看看,现在的世界已经是什么模样了。
冯劲费解地问苏敬钢:“你这是怎么了?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世上还有你苏敬钢不敢干的事儿!”苏敬钢平静地说:“不被抓当然没事儿,被抓了就有事儿,我一个人不怕,但我现在有儿子。”冯劲不在乎地说:“我也有儿子啊!”“我儿子将来是要出国留学的,”苏敬钢一提起儿子苏凉,脸上总会浮现出难以掩饰的喜悦,“我要是出事儿进去了,那我就成了我儿子的污点,别说他将来要出国留学,就是以后想找个好工作都难,老子的黑锅不能让儿子背,我劝你也别太嚣张,为你老婆孩子想想!”
冯劲不是没听过苏敬钢的劝,最初下海那两年,做的一直都是正经生意:搞过出租车公司,代理过外国营养品,还在南站开过小旅馆,组过建筑队揽过工程,可惜没有一样干得长久——直到后来,他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了深圳,一走就是十年,跟苏敬钢也断了来往。
冯劲具体做哪一行发了家,无人知晓。十年后,当冯劲回到这座城时,他已经是个千万富翁。
苏凉两三岁时,苏敬钢觉得他智力超群——可惜,只有他一人这么想。
苏敬钢从小就没有好好念过书,中学毕业后连最基本的汉语拼音都不会,自然觉得儿子苏凉两三岁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出左娜教他的成语,就算是神童。唯独令苏敬钢遗憾的是,苏凉太瘦弱了。
苏凉生下来就比普通的孩子体重轻,月科里又没有充足的奶水,能够健康长大已经算是奇迹。但是苏敬钢对儿子给予了全部的厚望,他没有气馁,他坚信通过自己的调教可以让儿子强壮起来。于是苏敬钢开始了对儿子的特训:他用钉子把一个沉重的糠皮芯儿枕头吊在卧室的房门上,让儿子每次进出时都用头狠狠撞上几下。苏敬钢煞有介事地指导苏凉说:“爸爸教你一个打架用的绝招——撞羊头!凉凉,你太瘦小,以后出门要是有比你高的大孩子欺负你,你出拳打不到他的脸,就用头撞他的肚子,发力前先退后几步,然后低头哈腰、猛劲儿向前冲——就像动物世界里演的羚羊,用犄角顶对方,只要瞄准了肚子撞,多高的个子都能被撞翻,等他倒在地上,身高优势就没了,你再骑到身上揍他的脸……”
“你把儿子都教坏啦!”左娜几次尝试阻止苏敬钢野蛮的教育方式都未果,只能埋怨,“你以为是男孩就都要像你一样啊?天性有别,懂吗?”苏敬钢理直气壮地说:“王大爷早就说过了,这孩子性格随我!”左娜被气得直翻白眼:“说性格随你,又不等于就要跟你干一样的事儿!你看咱家凉凉像是会出去跟人拳打脚踢的孩子吗?我儿子可是斯文人!”苏敬钢反驳:“男孩就该有男孩的样子!斯文有啥好?天天被人欺负的男孩,长大了也成不了大事!”
“歪理邪说!”
这种时候,唯有小苏凉像个受气包似的,夹在父母一来一去的争吵中,进进出出时还不忘朝硬邦邦的枕头撞上几下,枕头荡回来拍在他的小脑门儿上,拍得小苏凉晕晕乎乎——每每见此场景,苏敬钢和左娜都会转怒为笑。左娜对儿子的爱,较之苏敬钢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她最担心的就是小苏凉每天在大西菜行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早晚要学坏。可苏凉终归是要出去玩儿的,总不能整天把儿子锁在家里。左娜于是只好每天骑车载着苏凉去音乐学院的家属院里玩儿。在左娜眼里,那里的小孩子都是“正经”人家的孩子,苏凉跟他们一起,学到的起码不会是打打杀杀。
左娜也是由那时起,开始在音乐学院办的成人艺术班里学习钢琴,她想在学会最基本的唱教方法后,去教小孩子唱歌,赚一些外快补贴家用。九十年代初,左娜所在的第一阀门厂效益也早大不如前,厂里的同事都开始想法设法地搞副业:有豁得出面子的中年女同事在下班后去大西菜行卖烤地瓜、烤羊肉串儿,一个礼拜赚到的钱也比厂里发一个月的工资多。
左娜除了画图纸,她只会唱歌。
从广州回来后,左娜时常会怀念在全国各地的夜总会里张口就能大把赚钱的日子。但是生活毕竟回到了所谓的正轨,即便曾经在舞台上被人当作“小邓丽君”深受追捧,选择了退出,左娜也要跟平常女人一样,洗洗涮涮,买菜做饭,照顾孩子。左娜不敢说这样的日子就有多么枯燥和乏味,毕竟安稳的家庭生活还是给她带来过许多舞台上体验不到的人生乐趣,但是左娜在心底始终能感受到,有一团明媚炽热的火焰正在随着青春一同消亡。
苏凉三岁时,苏敬钢终于从厂里出来,跟冯劲一起跑了三个月出租,白班夜班轮流倒;左娜下班以后还要跑去别人家里教小孩子唱歌,她不是音乐学院出身,也没有专业认证,雇请左娜的人家多是因为左娜要的学费便宜。两人都没空照顾孩子的日夜里,张婶儿主动替他们照看起小苏凉。左娜曾经提议送苏凉去上幼儿园,可是一出口就被张婶儿回绝。张婶儿觉得上幼儿园太浪费钱,她又放心不下,生怕幼儿园的老师对外孙子百般折磨、千般虐待。左娜还是觉得,苏凉上了幼儿园可以早日学习知识,哪怕是认得几个汉字、会说几个最简单的英文单词也好,否则将来上了小学会被同龄的孩子落下。张婶儿却坚持说:“当年你哥和你不都是这么散养着长大的吗?谁也没上过幼儿园,也没见谁长大成了傻子!”左娜拗不过固执的母亲,任由张婶儿带着小苏凉过每天除了吃和睡,就是在户外玩耍的童年。
清晨,苏敬钢下了夜班回到家,左娜刚好起床,收拾着准备去上班。左娜对着镜子匆忙地化妆,对苏敬钢说:“待会儿你给儿子弄早饭,我着急出门。”苏敬钢上眼皮搭着下眼皮说:“今天上班这么早?”
“以后可能都要早,我跟主任说了下班去给小孩上课的事,主任说理解,允许我以后早点儿上班提前把活儿做完,就可以提前下班,省得我每天回家太晚不安全。”左娜说着嗅了两下鼻子,嫌弃地说:“一身烟味儿!在家不许抽了!别把儿子给呛着!”苏敬钢不快地说:“不抽烟怎么顶得住一个晚上?”左娜又说:“今天我妈要去照看一天我哥的孩子,过不来了,午饭和晚饭你给凉凉做吧。”——“我又不会做饭!”苏敬钢胸中积蓄着一股闷气。“不会学啊?”左娜也恼怒起来,忍不住大吐苦水,“我一天到晚趴在案子上画图纸,肩周炎都趴出来了,晚上还要骑车跑十里地去给人家孩子上课,回到家还得洗衣做饭,这些都是我出生就会的吗?从小到大,我啥时候自己做过饭?都是我妈做给我吃,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后学的吗?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你本来也用不着这么辛苦!”苏敬钢说,“我从厂里出来,不就是想多赚钱让你跟儿子过得自在一点儿嘛!我就弄不明白了,现在钱又不是不够你花,你还把自己累得跟驴一样辛苦为了啥?”左娜撇过头说:“我也不想可劲儿累你一个人,起码我能帮你分担一些。”
“你没说实话!”
苏敬钢盯着左娜频闪的眼睛,他太了解这个单纯得藏不住心事的女人了。
“我想买钢琴。”左娜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