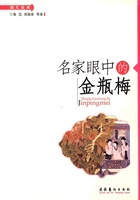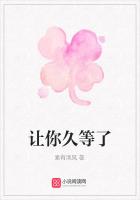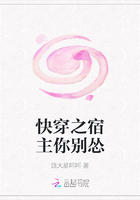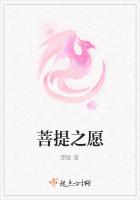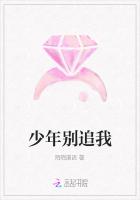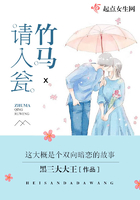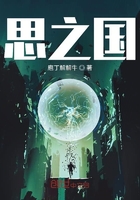我十六岁在四川省郫县第三中学初中毕业后,就没有继续读高中,而是进入了国家级重点中专之一的四川省邮电学校财会专业学习。虽然后来我通过十多年的继续学习,先后获得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但按照干部人事部门的正规要求,我的《履历表》上“全日制教育”栏目只能填上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我初中时期的学习成绩并不算差,全校排名在前三,但因为眼睛近视得厉害,即使考上大学也不能选择好的专业,再加上父母都是邮电职工,于是就叫我报考了邮电学校,读出来后即使在县邮电局就业,也算是有个牢固的“铁饭碗”。一九九一年后的三四年中,当我的大多数同学都还在高中挑灯苦读的时候,我却已经在成都狮子山下临帖刻章喝茶看闲书了。有时候回想起来,当年没有经历残酷的高考和读全日制大学或许是一种遗憾。不过,没有去读高中对自己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更重要的是,我有机会较早开始按照自己的兴趣广泛阅读,多年来一直对学习保持着兴趣。不像身边的一些虽然读了大学甚至研究生的朋友,学习的兴趣早已在高三的那些日日夜夜中消磨殆尽。这样来看我的选择,有失也有得,或许得还更多一点罢。
先说说我所学的财会专业知识。很惭愧,中专四年我花在会计专业方面的时间和精力估计不到十分之一。在邮电学校里,通信类理科专业的那些同学读得非常辛苦,而邮政和财会专业的学生就太轻松了。那几年我基本上是在每学期的最后半个月,抄笔记,背大纲,考试绝对没有问题。我庆幸自己所读的文科专业没有学业上的压力,可以有大把的时间自由支配任意挥霍。我当时想,学校里面学习的东西不过是谋生的手段,自己喜欢的书法才是值得长期付出的大工程。人生际遇很难说,但我毕业之后确实和财会专业工作无缘,说明最初的那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我进入中专以前已经在成都市书协会员龙宁老师指导下学习过多年的书法,也在一些青少年书法比赛中获奖,还作为成都学生代表参加过第三十九、四十一两届“全日本学生书道展”。一九九一年夏天,我的目标是争取在中专毕业前书法作品能两次选上省级书法展览,加入四川省书法家协会。我随身常带了不少字帖,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一册《书法丛刊》“米芾”专辑。我把这本书拆散了,把其中的一些散页随身携带,有时间就拿出来细细体味老米“八面出锋”的精妙笔法。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还没有什么电脑刻字之类的商铺,学校里迎接领导检查啊,“五四”文艺汇演啊等活动要挂出的标语横幅,就只能靠我拿着大号的毛笔“刷字”了。要写大字就得有地方,所以我进校不久就搞到了团委的一间办公室,两张办公桌拼到一起就是个大的画案,可以随时去写他个昏天黑地了。幸运的是,当时在邮电学校任党委秘书的任云老师也是一位青年书法家,我常常在晚自习后带着习作请他指教,从他那里借阅早些年的《中国书法》《书法》和《书法研究》;也常在周日骑着借来的单车,和任老师一起到美术馆看展览,到师友家切磋书艺。回头来看,九十年代初期还有着不少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大家都很真诚地谈论着艺术、文学,官方的书协还是很权威很神圣的机构,省书协会员的身份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在任云老师的指点之下,我进步很快,在一九九二年冬天,作品入选了“首届四川省书法新人新作展”。同时,我的几篇书法论文习作也在《书法导报》上发表。看来,我离自己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变化总是比计划快,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一九九三年是我的幸运年。这年寒假我在家玩得实在无聊,翻出《书法报》上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征稿启事”,在一个月内试着写了三篇论文。一篇论王铎书法,投寄“王铎书法国际研讨会”;一篇论赵孟 书法,投寄“赵孟 书法国际研讨会”;还有一篇谈书法与传统,投寄“全国第四届书法学术研讨会”。大概在四月初,我突然收到中国书协研究部主任张荣庆先生发来的加急电报,说论文入选,叫我到河南洛阳参加王铎书法国际研讨会。我打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领带坐火车到洛阳参加了这次会议。洛阳之行收获很大,不但见到了许多以前只能在报纸上读到名字的书法名家,认识了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授学者,还有机会游览了洛阳龙门石窟、关林、千唐志斋和王城公园,真有点“一日看尽洛阳花”的得意之情。九月,我又收到中国书协的会议通知,论文入选了“全国第四届书法学术研讨会”并获得三等奖,全文收入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这个结果令人惊喜。十月,我依然打着借来的领带坐火车到重庆参加了研讨会,重庆之行让我结识了当时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的邱振中教授,他在会后给了我很多帮助,指导我阅读哲学、美学和艺术史方面的书籍。十一月,我第三次收到中国书协的通知,论文入选在浙江湖州举行的“赵孟 书法国际研讨会”,并收入了由上海书店出版的论文集。我想,像我这种没有良好研究条件的野路子的书法研究者,一次入选国际研讨会是偶然,三次都入选,那肯定就是自己的实力了!呵呵。但是好像也不太对劲吧。我在短暂地被喜悦冲昏了头脑后很快清醒过来。自己能够几次入选这种大型研讨会既不是偶然,也不是自己有实力,而是当时整个书法学术研究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现代学术评判机制,整体学术水平太低,才让我占了先机有这个出道的机会而已。令人愉快的是,我这三次入选由中国书协主办的研讨会并获奖一次,已经具备加入中国书协的条件了。办理会员申请和审批花去一些时间,我在一九九四年四月加入了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在一九九六年六月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
从一九九四年春天开始,我按照邱振中老师的指点练习思辨能力和加强哲学素养,阅读西方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读波普,也读拉卡托斯、库恩和夏佩尔。好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当年已经出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黑皮书,里面有不少科学哲学译著,几块钱一本买来,慢慢读,反复看,一本《客观知识》或《证明与反驳》就可以消磨我好几个月的时间。由阅读波普延伸到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和《艺术发展史》,并参考了邱振中老师的朋友和同学范景中先生的有关论述。特别是范先生对黑格尔“时代精神”之类理论的批判,当时我读来真是有醍醐灌顶之感。在一九九四年夏天,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邮电学校图书馆里处理过期的刊物,我以一角钱一本的超低价格买来了一九八八年以来所有的《读书》《文物》《新华文摘》,书法美术类的期刊也被我全部买下。能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我经常帮图书馆写“新书预告”,得到了比别人提前选书的机会。而我的同学们喜欢的杂志,也主要是小说、散文和影视。各取所需,如此而已。
接下来,我很快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美妙的新世界,那就是《读书》杂志。八十年代的《读书》真是一部百科全书,内容极为广泛,很多都是大家写的文章,篇幅小容量大。我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辗转于离邮电学校咫尺之遥的四川师范大学里的几家旧书店、九眼桥地摊和冻青树街“淘书斋”,收齐了《读书》自创刊号以来的所有刊物,并以一周三本的速度进行通读。那真是一段美好的“读书”时光,我了解到很多从未听闻的学术话题,记住了一个又一个新鲜的人名和书名。《读书》对我来说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曾经认真读过的《书目答问》,它为我打开了许多扇新的学术之窗。在一九九四年圣诞前后,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旧梦重温及其他》投寄《读书》,刊发于一九九五年二月号。一九九五年春天,我离开成都到乐山邮电局实习前,在冻青树街“淘书斋”老蒋那里买了不少民国商务版的“万有文库”和“四部丛刊初编”零本,当时就一两元一本。也买了一些上海书店影印的民国文学书籍。我读到了章衣萍的《古庙集》,断断续续写成了《小僧衣萍是也》一文投寄《读书》,刊发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号。龚明德老师曾给我说,他当时正关心章衣萍的有关事迹,也读到了此文,但没想到作者就在成都。而我也在一九九九年前后读到龚老师《新文学散札》中有关章衣萍的数文。世界虽然很大,但爱书人并不太多。因为种种书缘与人缘,我和龚明德老师终于在二○○七年夏天“接上了头”,每周日早晨七点相约到草堂北大门外文物市场搜罗旧书。也因为龚老师的指示,我才在二○○九年的这个春天的夜晚,回忆那些中专读书的旧事和自己渐行渐远的青春岁月。撰有《读书敏求记》的钱遵王说过一句话,“墨汁因缘,艰于荣名利禄”。我想,在浮躁的时代里,能够忘掉荣名利禄,平平淡淡认认真真地读一些书,就很好了。
贺宏亮,男,一九七五年七月出生,汉族。四川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现为四川省通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