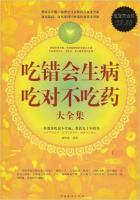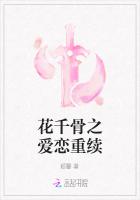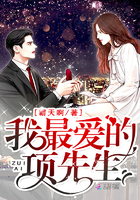我不太愿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给它的定性是两个字:灰暗。灰暗度高达百分之八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年都是转折年,很少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而这期间,我正在读中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逐步形成,尤其感觉到转折的苦痛。
苦痛的表征就是孤独。每天晚上,躺在大通铺上,旁边的同学鼾声四起,我微睁着眼睛,看窗外由明变暗,由暗变明。我不是经常失眠,只是睡不踏实,总觉得天快亮了天快亮了。黑暗、光明,光明、黑暗,缠绕着我,让我上升跌落,跌落上升。不知为什么,我那么期待天亮,那么害怕天黑。我自认为高人一等,却没出头之日(十三四岁时思考这样的问题,多少有点早熟)。天一黑下来,我就想到自己被埋没了。哲人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撬动地球。我想的是,给我一个机会,我会一飞冲天。当然,现在不这样想了,我明白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明白了自己的虚弱和无能为力。彼时的自信,皆因目光短浅,井底看天。同时,自己冒头儿很快,激发出了不属于自己的豪迈。我小学即发表作品,也算轰动一时。在学校里是知名人士。我写了诗,邮寄给《人民文学》,邮寄给《诗刊》《诗歌报》——自然,无一发表。谁理解我呢?周围的同学、老师,在我眼里都是平庸之辈,跟他们在一起,只能让我更平庸更堕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请原谅,那时我的确发自肺腑地这样认为。茫然四顾,心内凄惶,谁是我的知音?
一九八九年冬天,我和王世立创办了一份油印小报《我你他》,印好以后,我俩站在楼梯口散发。各年级的同学都奇怪地看我俩,有的接过去,有的则拒绝了。散发了有三十多份。谈不上成就感,有点满足而已。夕阳西下,我和世立围着操场边转圈边畅谈梦想。后来我们还发展了不少会员。因为我们的带动,好几个班级都有人操办文学社。我和世立把自己的小报邮寄给其他地方的文学社团,试图联络更多的同盟,结果不了了之。前两年回家,居然在抽屉里找到两份《我你他》,抚摸着泛黄的纸页,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王世立现居住在衡水,十多年后我们再见面时,他正全心把精力用在对女儿的教育上,他还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家庭教育的心得。他过得很充实。祝福他。毕竟,我们共同做了唯一一件值得回忆的事。
我读琼瑶的小说,三毛的散文,这类书读多了,真的以为可以找到知音似的。于是,青春激情萌动了。初二的时候,我就开始单恋一个女孩儿,给人家写信,写了好几封,终于回了一次,提醒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高中时,跟一个女笔友通信谈文学,后来谈情说爱。连面都没见过,居然谈到了爱,不过是一种望梅止渴的方式,但好歹也可慰藉一下孤寂的心灵。我们甚至约定了见面时间和地点。在临门一脚时,却射偏了,没有见成。其实彼此心里对见面都没底,冥冥之中并不希望变成现实。就这么拖着,直到各自都没了情绪。在此期间,我还给另外两个女孩儿写过情书,一个给我回了信,一个没回。回想起来有点后怕,幸亏我没正式谈成恋爱。一些早恋的同学,如今都被锁定在家乡那片土地上了,再没机会出来。而且,因为爱情建立的基础太过薄弱,他们的婚姻多不幸福。
对文学的期待,对爱情的憧憬,是中学时代的两大主题,但都没什么着落。当时刻骨铭心,如今却觉非常模糊,连带着自己的记忆也模糊起来,仿佛那是别人的事,跟我关系不大。
或问,这也没看出什么灰暗来呀。是的,灰暗是一种心境——那些年,我总处于挫败感之中。家境不如人,未来不如人。我知道外面有一个很精彩的世界,因为遥远,还会把它想象得更精彩。而我深陷泥淖,难以自拔,看不到希望,一切很渺茫。在以分数决定未来的环境中,我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到写作上了,学习成绩不出色。那是真正靠分数改变命运的年代。自己的敲门砖不硬,每每在梦中惊醒。即使今天,我还常常梦到被拽回学校参加考试,而那些试题我都不会做。
如果重新活一次,我绝对不要那样的中学时代。我害怕。
王国华,笔名易水寒。一九七四年生人,河北人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深圳报业集团宝安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