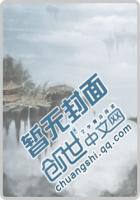我出生在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教师,母亲在一所小学一直工作到退休;父亲是当地有点影响的中学数学教师,后来做过一段时间的中学校长,桃李芬芳。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家庭大概也差不多,没有什么神秘和特殊可以炫耀。书香气息,诗礼人家,其实距离我们和那个时代都很遥远。因此,在我们这样的家庭,生活也极其普通,属于波澜不惊的那一种。唯一的是有一点书,大都是多年教学积累的参考书和历年的教科书,几乎没有像样的文学艺术类的东西,更谈不上什么珍籍善本了。我现在能够找到的那时所谓的文艺书籍,只有一本缺少了封面的《欧阳海之歌》初版本和几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学》课本——如果它们也能算作文艺书籍的话。也许是注定的缘分吧,这有限的书籍却给了我最初的精神滋养,竟然使我后来爱上了读书和藏书,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书虫。
我是一九七八年升入初中的,父母虽然都是在农村教学,但我和哥哥却都是在城里的中学读书。学校距离我住的村子很远,步行得走四五十分钟,冬天天不亮就出发,披星戴月是家常便饭,我的初中上下学全靠双腿来回跋涉。我的第一首诗歌是在《语文报》发表的,那时我已经读了高中,我曾经在诗中描写过当时上学的情景:“我起床的时候/天上还有星/长跑与早读刚刚结束/太阳又送我/走进钢笔和纸张的长吻中/当最后一束晚霞/和我的作业本一同收进书包/月亮却在我担水时/用她全部的柔情/燃亮了/我的台灯”。诗写得不好,却很浪漫,也很真实,里面凝结着浓郁的少年情怀,意气风发的精神像这些浅薄的诗句一样显而易见。那个年代刚刚恢复高考,初中的功课并不紧张,不用减负,也没有素质教育的说法,后人常把那时说成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其实,我们初中生根本觉察不出什么,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一场电影,一次春游爬山,都可能让我们激动好多天,把这难忘的快乐经历写进作文和日记里。那时的流行歌曲都是抒情的“台湾校园歌曲”,没有VCD光碟,磁带也很奢侈,只能靠半导体收音机,那时的歌星绝对不是今天的周杰伦、SHE们的对手,但我们依旧狂热地传抄在笔记本上如醉如痴。虽然也有崇拜的偶像,却没有今天粉丝们的投入,一张洗印的明星黑白照片,大概与今天琳琅满目的粘贴画是无法比较的。那时的晚自习更多是一种形式,家远的同学可以不去,也几乎没有家庭作业,因此晚上听广播就是最大的娱乐,当时的评书连播《岳飞传》《杨家将》,让我在白天上课时候也牵肠挂肚。功课的平稳,娱乐的缺乏,开始让我接近一些杂志。最初是买《大众电影》,买《萌芽》《青春》,也买《星星》诗刊,我至今还完整保存着包括复刊号在内的一九七九年全年的《大众电影》,一九七九年的《当代》创刊号我也珍藏着。通过读杂志,勾起了我的阅读的欲望,我节省下午饭钱来买书,买的第一本书是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我小心地给它包了书衣,工工整整写下了购买时间:一九八○年三月二日。我不仅为书中主人公的命运感动,我更为作家华丽的文笔倾倒,有些章节几乎可以大段背诵下来,我还精心把自己喜欢的段落抄在一个小本子上,连同其他阅读的收获,这样的笔记大概记了十几本,直到上了高中,功课紧张了才停止。二○○六年夏天,在北京大栅栏中国书店,我再次购买了《第二次握手》(重写本),比起初版本来,重写本厚重了许多,我把它从北京带回来,与一九七九年七月的初版本一起放在书架上,为的就是一种读书情结,我知道,我今后也许不会去读它了,但我会记起少年时与它亲密接触的情景,我会循着时间的记忆之链,打捞起初中的读书生活,体味逝水年华的美好。
买书的心情是慷慨的,读书的享受是快乐的。有时读得入迷了,我也会犯一些小错误,我读《青春万岁》,读《红楼梦》,就是在课堂上,忽视了老师的存在,只顾了自己的津津有味,换来的是课后的检讨和哀求归还没收的书。批评自是难免的,但作文经常被好评,当众宣读,使我风光,也使我矛盾。我的喜欢作文、喜欢阅读,大概和语文老师不断地鼓励有关。当然,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为了提高描写能力,我几乎把课本上的重要文章都进行了背诵,看到同学羡慕的目光,很是沾沾自喜,但也有被老师取笑的时候,自己偷偷涂鸦的小诗,记得有一首写溪流的,在句子中出现了浩浩荡荡一词,老师就常常拿此笑话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通感和意象,完全是凭感觉去写,用词上就生硬了,但这事对我很有触动,以后就细心起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兴旺勃发的岁月,我的初中生活也在不知不觉中丰富生动起来,那时候一大批经典和准经典图书解除了禁锢,洋溢出诱人的气息,我沉浸其中,难以自拔。随着日积月累,读书逐渐开阔,藏书也渐成气象,几乎到了不买书就手痒的程度。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已有了三百多册书,除了文学杂志,已经有了像《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十日谈》《猎人笔记》《复活》等这类的文学名著了。人的一生,与书是分不开的,与书的呼吸是连在一起的,书籍给人的帮助也是说不清的。我们现在的读书条件非常好,要读的书就像田野那样丰饶,打开一本喜欢的书来读,就像面对一个好友,伴着茶的清香和酒的醇厚,这个世界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在读书的路上,我们慢慢长大,慢慢成熟,慢慢和岁月一起老去,多么从容,多么惬意,又是多么幸福,多么快乐和满足。
袁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于山东淄博,曾在政府机关从事文秘工作,现供职于地方广电部门,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周村区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