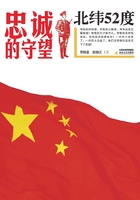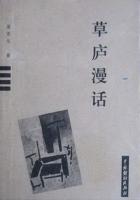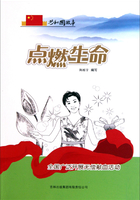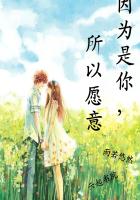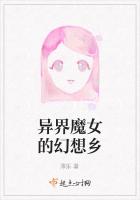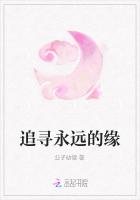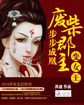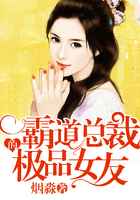师生重又相见的这一天,经过三十余年漫长期待之后,终于盼到了。我的老师从香港回到内地,来看望他始终想念的学生。当我们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师,报上自己姓名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的眼圈儿红了,他大声地重复着我们的名字,似乎要把眼前的情景,重新拉回到当年的校园。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老师三十八九岁,年轻且胸怀抱负,我们大都在十五六岁,懵懂之中初学做人。当时班里的课堂纪律混乱,老师奉命前来接班,可第一天上课,并没有出现以往的“哄堂”情况,这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这样有风度的老师,并且知道老师还是一位泰国归侨,可能就是缘于对老师爱国心的敬佩吧,初次相识,师生之间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学生时代,使我难以忘怀的老师,当属这位中学时期的班主任韩良平。虽然从小学直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有七八位之多,但是像韩老师这样印象深刻的班主任却不多。实际上,在61中学,我和韩老师也只相处了两个学年,那段时光的零星记忆,不知为什么,竟然一直在心里埋藏了三十多年。
老师是否还有当年的印象?从那时到现在,岁月倏忽,弹指间三十余年过去了,而今,老师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他坐在我们中间,一边听我们说话,一边用眼睛细细地打量着我们,似在回想坐在他身边的这些学生,是否还有当年的影子?而我们也在端详老师,当年的老师高高的身材,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梳着整洁的背头,烟瘾很大,走起路来的步幅也很大……
老师在我们的回忆中,开怀地笑着,仿佛又使我们回到互为师生时的场景,只是当年的老师是不苟言笑的,作为师长,他需要有一种威慑,而我们认可这种威严,完全是出于对老师认真执教的服膺,老师在课堂上那带有南方口音的授课声,常常使得教室里鸦雀无声。作为学生,能够对老师怀有敬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水平和为人师表的品行。
在学生的心目中,老师总是有些神秘,有关老师的个人情况,我们是后来才断断续续地听说的,知道老师毕业于河北大学,对语文教学很有经验,这些已经在课堂上得到了证实。关于老师的身世和家庭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但非常关心,多少有些耳闻,尤其是像老师这样的华侨身份。在上学途中,我们就曾经结伴到当时位于黄家花园的一家土产杂品商店,去“偷看”老师的爱人,因为我们听说这位年轻的师母也是华侨,而且很漂亮。结果也是这样,师母是位售货员,长得白皙、丰满,和老师很般配。当时站在柜台后的师母肯定不会想到,这几个心怀想法的中学生,是来验证她的相貌的。老师有两个儿子,都很聪颖,尤其对小儿子,老师相当地疼爱。
老师们虽然很努力地教课,但当时畅行“读书无用”论,甚至连期末考试都被取消了,每到新学年,学生都是自动升级。中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已经没有任何教学课程,全班学生被“放逐”到天津罐头厂学工劳动,一干就是三个月,直到学年结束。这期间,老师一直跟着我们,在生产车间,经常会看到他身穿白色围裙来回穿梭的身影。中午休息时,老师根据学校的要求,组织我们集中政治学习,具体“作业”就是批判《神童诗》,让我和另外几个语文比较好的同学,将《神童诗》分成若干部分,每人分领一段儿进行分析、批判,然后再纂成一本小册子,由老师通过学校印刷装订,发放给同学们学习。对这本有着黄色封面的薄薄的小册子,我早已经忘记了名称,但在当时,它却是我们开门办学,走向社会大课堂所取得的所谓学习成果。
由于历史的原因,老师不能尽到传授知识的责任,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我始终认为,老师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极想在教书育人方面有所建树,可是不行,空有一腔热血,而终究不能有所为。我在离校之后的许多年,心中都抹不掉老师的影子,在听说老师于一九七九年定居香港后,我的心里不禁又多了一份失落与惆怅。
对老师的思念,让我拿起笔来,以老师为原型,写了一篇散文《校园生活回忆》和一首叙事诗《第二次归来——给一位班主任》,时间分别为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九三年。文章和诗歌都是以母校为背景,描写一位人民教师,在“**********”中所经历的坎坷与磨难。但又怕给老师找麻烦,我把它们放进抽屉里,一直“埋藏”着,就像我对老师的想念,始终是深藏在心里一样。
身为教师,老师是不愿看到学生荒废学业的,他便在做人上做出表率,尽心尽力地尽到班主任之责。老师喜欢语文好的学生,班里哪个学生的文笔好,他就表扬;老师善解人意,他说有的学生上课捣乱,那并不是坏,而是调皮;老师做家访时,说得最多的,是学生的本质,是长处……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学生们或多或少地都能回忆起,老师曾经给予过的教诲和帮助,哪怕只是一桩微小的、不起眼的,甚或有的连老师自己都早已忘记的小事,学生却是一生铭记。
那年夏季,我正在家里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下午,老师忽然蹬着自行车到家里找我,通知我到学校面试,说有一家新闻单位特别适合我。这个消息令我振奋,从心里感激老师的惦记。后来得知,为争取到这个分配名额,老师极为尽心地做了推荐,他对负责分配工作的老师们说:“可以比一比嘛,我的这个学生有作品!”
这就是在学工劳动期间,每天下班回家,吃完晚饭我便埋头写作,不到两个月时间,竟然写出了几十首诗歌,并且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白纸上,自己装订成册。之后,我惴惴不安地将这本“诗集”呈送给老师,请他给予指点。就是这一情节,让老师记在了心里。
在老师的心中,诸如这样的情节很多,老师几乎记住了班里每个学生的爱好和特长,并且在关系到学生一生命运的毕业分配中,想尽办法地提供关照,想上学的去上学,想当兵的送去体检,想参加工作的尽可能选择一个好单位。现在想来,对于一个普通的班主任来说,他所能做的都做到了。
老师身在香港,一直惦念他工作过的学校和教过的学生,近几年,他常有回内地的计划,却又都因事情牵绊而搁浅。是的,老师仍然是忙碌而勤勉的,五年前,老师用泰文出版了一本介绍海南岛的专著(老师祖籍海南),这次回内地,老师又带来了新近完稿的三十万字的《美丽而神奇的泰国》一书。可见,老师在晚年的生活是充实而愉快的,虽然在香港的生活压力很大,老师作为一介书生,自然不会财运亨通,但老师没有放弃专业,仍在香港的大学里教授中文,师母也相跟着一起授课。老师说,他不给自己施加压力,能够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就很满足了。
翻阅着老师的书稿,我的心头不由得漾起一阵别样的情愫。这多年来,我在心中“囤积”的情感,该怎样向老师倾吐?我突然感到,语言在此时是多么无力,我像三十余年前一样,仍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向老师呈送上我的第一本诗集《迟献的素馨花》,但此情此景已不似当年。我能预感,这本凝聚着或曰记录了我的真情实感的诗集,老师一定会从中读出我的心声,我的向往,我在人生历程中的努力与跋涉。
师生重新相见的这一天,来得如此漫长,其间的世态炎凉、人情变化,会改变多少东西?我始终相信,师生情谊永远不会受到玷污,因为老师既给过你知识,也给过你思想,在施教与受益者之间,感恩是学生终生的情怀。
毕竟三十余年过去了,我默默地观察老师,发现老师虽然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但从背影望去,还是老了,他的体态和步幅已远不如当年,而我们也不再青春年少,在体验过懵懂、感奋和得失之后,这段师生缘已经被刻录在心底,在未来那依然漫长的岁月中,将时时发出生命之光。
宋曙光,一九五七年生,大学学历,现为天津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