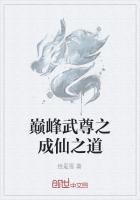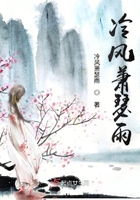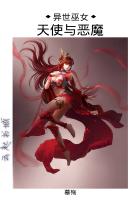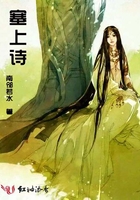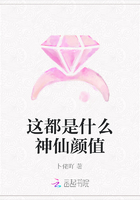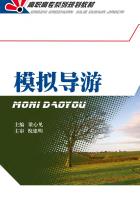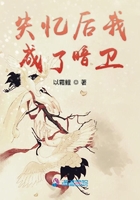我的老家在长沙市东边的乡下,距长沙大约四十五公里,系长沙和浏阳的交界处,旁边有一条公路,就叫长浏公路。我的老家大名江背,为何叫这么个名,我也一直没搞清楚。我们那地方是没有河也没有江的。与江背相邻的五美倒是有一条著名的浏阳河从其中穿过,江背的“江”是否与这一条浏阳河有关呢?不得而知。江背是在浏阳的“臂弯”里。我从长沙回老家,先得经过浏阳的永安,然后是江背,再往前,又是浏阳的跃龙了。江背中学就在长浏公路的旁边。
还得交代一下,我读小学时,进的是江背小学,当时的小学是和初中连在一起的,也是在长浏公路的旁边。小学和初中合起来称为江背学校。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用的是全国通用的正式教材。从小学一年二期开始,直到高中毕业,用的教材都是临时的,拼凑的,或者说是乌七八糟的。还是来说说我的中学吧。我的初中是在江背中学读的。我在读初中时,在距江背学校一公里处,有一所社办中学正在热火朝天地兴建之中。这一所新建的中学便是新的江背中学。我的高中就是在这所新的江背中学读的。我当时所在的班是高四班。我进高中的那一年是一九七二年。
现在想起来,这江背中学真是一个十分奇怪的学校。她最怪的地方是,不知为什么,在那么一个颇为偏远的乡村中学,竟然汇集了那么多就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非常了不得的老师。先说我的班主任老师吧,他叫曹泽杨,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一直记得他那与众不同的粉笔字,行云流水,显示出一种个性鲜明的无拘无束。他学识渊博,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能把他难倒。他会拉二胡、京胡、小提琴。他会翻空心筋斗。有一辆东风牌的货车从他的旁边过,他跟着跑几步就可以爬上去。他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而且都是学校中打得最好的。那时候的曹老师在我的心中,简直是无所不能。后来,我在长沙工作,曹老师也调到了长沙的一所重点中学,他一直都是教毕业班的。他还写过几本与长沙地域文化有关的书,即《长沙忆旧》《湘人百态》《湘城掌故》。这几本书他都是与全国著名的漫画家石卜合作的,其形式都是一文一图。在长沙的二十多年时间,我一直都与曹老师保持着密切的忘年之交。
再说刚才提到的全国著名漫画家石卜吧,他原名叫周正。在江背中学时,他是我们的英语老师。他最著名的系列组画《马大哈大叔》,曾在《中国日报》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上连载过四十多组。当时的漫画界前辈华君武、方成等老先生都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创作过系列漫画《老两口》,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连载,也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在江背中学教书时的周老师,刚从城市到农村,真是闹过不少的笑话。比如见竹子长得好,他就问,哪里有竹秧子买?又比如挖红薯,他见别人挖的比他大,便问何故?告之曰:要挖得深。于是,他就拼命往深里挖。挖到锄头都扯不出来了,他就用肩膀去扛,结果,锄头把断了。那时候,周老师是以“憨”著称的。
还有教化学的彭鸣凯老师,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词学家,湘潭大学的名教授彭靖先生。彭老师比我大不了几岁,后来我们是一同参加高考的。他曾经带我到长沙玩过,两人还一起看过电影。而且,在电影院里还偷偷地抽过烟。关于我抽烟的故事,等会再说。我记得那时我还跟着彭老师到他位于北正街的家里去过。他们家的姊妹是很多的,最小的叫八妹子。我记得,彭老师和八妹子为什么事打赌,他们背化学元素周期表,看谁背得快,两人让我大开眼界。彭鸣凯老师现在湖南教师进修学院任教,他主编的《中学生化学报》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的。
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叫黄卓杰,据说他是当时的长沙县唯一一个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他的夫人也是教数学的,典型的城市美人。还有教体育的周国光老师,一米八几的个子,天生就是搞体育的料子。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曹泽杨老师的篮球打得好之外,第二个就是周老师了。他们两个似乎是难分高下的。还有一个篮球打得好的老师姓刘,好像是叫刘世成,教我们高一个年级的语文。后来据说他调到长沙县当了管文教的副县长。还有教物理的,也姓曹,也是长沙市一所高校毕业的。还有曾在长沙市一家花鼓剧团当过演员的熊梦鹤老师,他是我们的文娱老师吧?有点记不清,反正,他是辅导过我们排练节目的。熊梦鹤老师最拿手的是打快板,我记得最清楚的段子是《新旧南门口》和《消灭“四害”打老鼠》。我后来在长沙县的“五七大学文艺分校”时一项特长是打快板,便是受他的影响。再后来我进大学,还上台表演过打快板,且获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这功劳还真要归功于熊老师。还有几位打扮入时的女老师,让那时的我对城市的文明充满了一种模糊的向往。一直到现在,我都经常和人说起,我的命真好,在那么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所在的中学居然从城里来了那么多好老师。这不是谁想遇就能遇到的。
还是说说我自己吧。我记得初中刚毕业时,我们的生产队来了一个城里伢子,他叫王中强。他是为了躲避“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而来到亲戚家的。他会画画,还会拉小提琴。他在我的面前展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于是,整整的一个暑假,我便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跑来跑去。那时候的夏天没有现在这么热,我和他在坝坎子里捉鱼,或在某一个山坡上听他拉琴。有一次,我和他在江背小镇边上的一个水碾房玩。我爬到了水碾子上。不知怎么水碾子忽然被水冲开了,水碾子由慢到快加速地转动着。我急得哇哇大叫,随时都有被摔到水坝里去的危险。后来是怎么下来的,是不是王中强关的水,也不记得了。但我不会忘记的是,那一次我差一点连命都丢了。我抽烟就是和王中强学的。那时我们还用英语的谐音美其名曰“司慕克”。顺便说一下,我与王中强在分别将近二十年后的某一天,忽然在长沙的街头相遇了。这一遇,我们的友好关系又接上了。他在一家台资的娱乐公司任职,我在一家小报当编辑,后又到一家文学杂志当主编,王中强都给过我很大的支持。当然,我也利用新闻媒体的朋友助过他一臂之力。我和王中强至今还是极好的哥们儿。
也就是因为抽烟,进高中时,学校某领导提出这样调皮的学生不敢收,曹泽杨老师说,他不怕,因为这个学生成绩好,就放在他的班上好了。进高中后,我依然恶习不改,烟照抽不误,当然是偷偷地抽。曹老师的烟经常放在书桌上,那时的烟我记得有一角三分钱一包的“红橘”,我们称之为“南瓜砣”。还有两角钱一包的“岳麓山”,二角六分钱一包的“黄金叶”,最好的是“大前门”,三角钱一包。曹老师的书桌上一般是没抽完的“南瓜砣”。曹老师的烟我是偷过不少的。周正老师的烟我也偷过,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家做藕煤,我和两位同学发现周老师的上衣口袋里有烟,就装作关心的样子,说天太热了,要他把衣服脱下,我们帮他送到寝室里去。周老师觉得这些学生真不错,知道体贴人,于是二话没说就把上衣脱了下来,后果可想而知。好多年后,周老师也调到了长沙一所中学,说起这件事来,他还佯装着愤愤地骂人。到彭鸣凯老师的寝室里去玩,我的胆子就要大得多,因为他宠着我。有时,我和他两个人共着一支烟抽。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的抽烟史》,我大约抽了有七年的时间。进大学的第一年,我就把烟戒了。而且,戒得好像还很轻松,这说明我那时的烟瘾并不是特别地重,很多的时候是想抖一种男人的派头。
在中学时,我还是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先是校队的,后来又是区队的,受过一段时间正规训练。我到县里参加过比赛,拿没拿过名次,不记得了。现在偶尔打打乒乓球,拍子一拿,好像就能找到当年读中学时的感觉。朋友们一见,都说,看得出,曾经是受过训练的。读中学时,还有什么值得说说的呢?我们那时候读书是连单车都没有的,全靠两条腿跑来跑去。每天放学回家,要么到生产队去做一气工。在生产队做事叫出工,一天分为四气,每气近两小时。要么就去寻猪草。总而言之,放学回家是要做事的。暑假呢,雷打不动地参加生产队的“双抢”,抢收抢种。那时的“双抢”没有一个多月是怎么也搞不完的。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晚上天黑了还不能回家。我那时挑得起一百多斤的稻子,工间歇气时,就坐在家里的门槛上吃米汤泡饭,好大一碗,什么菜都不要。有一次“双抢”,我在田里踩打稻机,踩着踩着,发了痧,晕倒在田里了,是被人抬回家的。
读中学时,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戴军帽,而且抢军帽都成了一种时尚。我曾经想方设法从我们队上的复员军人三哥处死皮赖脸地要到过一顶,如获至宝,一直戴了好多年。我至今还留着一张当年戴军帽的照片。我在读中学时,仿佛是没有初恋故事的。朦朦胧胧喜欢一个女孩子的事是有过的,可那是单相思,对方是不知道的。
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现在想起中学时代的事来,还真是有了一种遥远又遥远的伤感。此时,窗外的斜阳正扬着告别白天的手,因此,心中也就涌动着莫名的惆怅。
彭国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原《创作》杂志主编。现为长沙市文联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