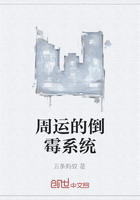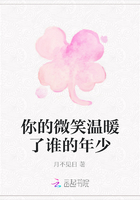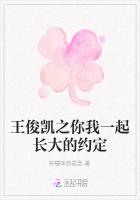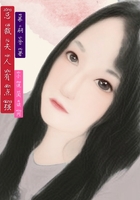在我将满八十岁的时候,忆及中学时代,就不能不想到一位语文老师陆承勉先生。那时候,学校里的习惯是称老师为“先生”的。我说我不能不“想到”,用词不太准确。我是止不住地回忆他,感念他。我还禁不住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一个我极少用的词——“亲爱的”。因为陆老师是我在语文方面的启蒙老师。后来,我进入山西社科所和山西作家协会从事编辑工作以前,先做过十年中学语文教师。其实我高中尚未毕业,能承担这样的工作,都是陆老师给我打下的一点底子。说来惭愧,我当教师的那十年,也就是由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二年间,语文教师的素质已不算很理想了。我记得那时学校安排工作,有几个什么都不会干的人,什么也教不了,最后领导说:“那就教语文。”我就是这样的人。因为那些年学校迅速增加,又“跃进”,需要人太多,要求不能太严。那时真是无所谓什么教师素质的。可是我当学生的时候,教师素质可不是这样的。
我说的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间的事。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年代。而那时我正在徐州,那可是淮海大战的中心。那里真可以说是战云密布。但也不要以为在徐州就是炮火连天。不是。我后来才慢慢明白,什么叫作“战略要地”。徐州就是一个战略要地,但仗都在徐州百里以外的地方打,打完了,该胜的胜,该逃的逃。在徐州市内,只听到炮声的闷响,看到国民党部队的伤兵。我们学校里也驻过一阵兵,时间不长;在后操场里架过炮,但没有开过炮。那时候学校的师资极好。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有许多由后方来的教师、学者、大学生,想往京、津、济南、青岛或东北一带去,走到徐州,铁路断了,连去济南也不通车。他们只好在徐州找个教书的活儿,先过下去。那时候,我们的江苏省立徐州中学,真是人才济济。
陆承勉老师在那里立住脚,受到欢迎,也不易。他可真算是一位好的语文教师,是素质高的语文教师。从高一到高二,我的语文都由陆承勉先生教。陆老师毕业于大后方的武汉大学中文系。也许当年他的老同学还能记起他。他的语文功底很好,当然他也称不上专家。他的语文功底的强项在古典,在知识。回想起来,他的写作能力可能并不强。比如,在学校里的语文老师里和英语老师里,当时和以后,在报刊上发表过散文、小说、翻译作品的就有几位,而陆老师却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这是自然的。但总体的学问却不能少,而应比较全面。陆老师给我们讲过拜伦的长诗《去国行》,那是苏曼殊译的,据说经章太炎润色过,声情俱茂,极其感人。那是一篇“补充教材”,油印的;我不记得为什么要补这么一篇,也许是他喜欢吧。他一面读苏曼殊译诗,一面还把拜伦的原文也抄写在黑板上,我们跟着抄。所以我现在除背译文外,还能背出原文的头两句。我前些日子与老同学联系,谈及此,他说他也能背下几句原文。陆老师的神态也如在目前。他的英语发音很生硬,但也还能应付。我以为这也是语文功底的一部分。
那时正在淮海大战的前夕,徐州可以说是兵荒马乱。学校里架起大炮,沿校墙的大树都被锯断。说来也巧,那时的课文里就有鲍照的《芜城赋》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序》。这都是记战乱中的荒凉。我记得陆老师有腔有调的朗读,加上深沉又苍凉的讲解,真也有些令人心碎呢。我们几个走读学生,在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就都试着背课文。这两篇都是名文大作,用的典故也多。现在,其中的典故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还能片断背下它的某些句子,像“日暮途穷,人间何世”,像“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我读到过学者刘绍铭的《文字岂是东西》,谈当前的中国语文教育。作者在海外当教授多年。他说:“提高学子语文水准,除了复古,别无他法。”那讲的也许过了一点,而且是针对大学生讲的。中学生未必要如此,但中学教师实在是可以如此的。我偶翻中学生的语文课本,发现现在的课文也真是这样的了。
我说过,我没见陆老师发表过文章。但是按当时的说法,他的“笔下”,也还是蛮漂亮的。那时学生作文要用毛笔抄写,老师也要用毛笔蘸红墨水批改。他的书法挺老到,平常不批作文,临到作文课前一二日,再熬一个通宵批改。他批得认真,且有感情,也见文采。他欣赏我的作文,这对我很有促进作用。我记得有一次用文言作文,他在我的作文后面批了长长一段,其中有一句云“文言亦复跌宕,真长才也”,我到现在也不知什么叫“长才”,但我很得意,竟然一直记了七十多年。可见一位好老师的评语,真能叫学生记一辈子。当然这种评语,老师要用心写,而且有能力写好。他善用“之乎者也”,铿锵有力。那可不是人人能写得出的。他的强项在古典。但他自己并不是酸老夫子。他网球打得很好,下过工夫的。他对当代话剧也有兴趣。当时校里演话剧(张骏祥著《万世师表》),他就有兴趣来当导演,因为我也演了一个角色,所以与他有些课外的交流。《万世师表》是写抗战中一所大学的迁校,写教授和学生的。按年龄,他该是那里面的学生一代。他导演,我就感到他的体验是很真的。戏剧是文学的一种,这也可以表现出一位教师的整体素质。
那时候的教师是那样穷,几乎无法养活全家。陆老师的孩子多,夫人没有工作,日子很艰难。这位先生是守着孔夫子的“君子固穷”的原则,不作“穷斯滥矣”的下三烂。我们以前批判过这种知识分子的“假清高”,其实,在穷困中,那点清高并不假,实在是可贵的。这是题外的话。他只在他自己的学生和文学辞章的天地里生活,这份清高在当时没有多少。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寒假前,班里有人集同学的捐助,给陆老师买一袋白面送去。原担心他不收,但他收下了,也许因为那是弟子们的心意。不知他当时心里滋味如何。他爱喝点烧酒。酒后偶有的一点狂态,就是在夜晚高声读什么古文古诗之类,同院邻居都能听到。我是听他们说的。这好像是所谓“喝烧酒,读离骚,方是真名士”的体现。总之,他是文人也。学生们在这方面也明白着呢。有时,见他两眼充满血丝,学生们知道,不是昨夜未眠,就是喝烧酒多了一点。那年头,他能没有郁闷和痛苦?
陆老师是我终身难忘的语文老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回徐州时,还多次拜访过他。他还是老样子,见到老学生十分亲切,问长问短,还开几句玩笑。有时他眼里还有红丝,不知是否还熬夜读书,或者还喝几盅烧酒。陆老师并没有活到我现在的年纪。陆老师如活到现在,也该有一百岁了。现在,他只是活在我的心中。不是活在我一个人的心中,而是活在我们一班学生、几届学生的心中。
李国涛,一九三○年十一月生,江苏徐州人。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徐州中学。一九五○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学教师、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学术通讯》编辑、《汾水》编辑部副主任、《山西文学》杂志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