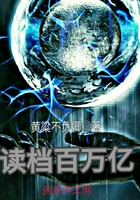一叶秋:
那时少年愁
剑语问公侯
梨花灯影乱
刀马逍遥游
半壶红尘酿
三两疏离酒
一念辞家日
醉梦已千秋
从来没有哪片天,像今日一般压抑;从来没有哪条河,像这段江水一般赤红;也从来没有哪个镇,像江流集一般悲凉。
鸣鸿山崖上巨大的石佛手掐般若印,双目半阖,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也不知是因为佛麻木了,还是不忍再看那屠宰场一眼。
数以万计的血肉之躯倒在这里,却没有一具动弹一下。无边尸骸间偶然跃动的生命却是寥寥几只食腐鸦。望不到边际的尸身不过是又一个寒秋之日的修饰,漫山遍野的红叶与猩红相映透着别样的凄美,构成这副画卷的代价却如此惨重。
过不了多久,那些循迹而来的野犬也回到了。方才震天的杀喊声几欲惊退雷神,这些可怜的禽兽一个个早被吓破了胆,许久不敢靠近。唯有那些饿昏了头的鸦才敢在这时落下来饕餮一番。
嘉陵江水面上突然起了几道涟漪,一场不期而至的雨开始冲刷江流集。不一会儿,嘉陵江水更红了。
一只饥饿的黄毛野狗拖着湿漉漉的、如柴的身子从山林里现出了本尊。就算是被杀掉,老子也得吃口肉。它的脑子里都是肉,也不知是不是幻觉,就连它满眼看到的竟都是***山遍野,江流浮尸,那是一辈子都吃不完的肉!
黄毛狗看看周围,它那可怜的黑白视界里会动的生物中自己就是块头最大了,那流淌的河水和几只傻鸟根本不能对自己构成任何威胁——没有谁会打扰它的用餐!它开始晕乎乎地往前走,爪子踩着的都是肉。
这一块?太脏。那一坨?太油。
黄毛狗踩着尸体走了好远,也许有上百丈那么远。他现在站在江流集……曾经江流集的镇中心。这里的肉最多,血也最浓,有铁壳蓝皮的肉,有铁壳黄皮的肉……最后黄毛狗挑了一块藤壳红皮温乎乎还冒着热气的肉。
它先嗅了半天,又用爪子扒拉了半天,确定这是它见过最好的肉了,便朝那柔软的肚子下嘴。它准备先把那碍事的红色布皮给撕掉,然后咬破肚子掏出内脏……没有什么比新鲜的内脏更加美味的了……
可是那身藤壳又坚又韧,怎么都去不掉。黄毛狗撕扯了好久,终于放弃了肚子。它又转向大腿,大腿肉的口感虽不及内脏,但也十分美味。
黄毛狗张开了嘴,还没来得及要下去就感到一阵腥臭的热流充满了自己的口腔,这味道它曾经十分熟悉,但近些日子已经很久没有尝到过了——那是热血的味道。
它自己的血的味道。
士兵从死去的野狗嘴里拔出匕首,踉跄着爬了起来。他没有举目四望,也没有回味战争的残酷,更没有追忆逝去的战友,却只是盯着那只野狗的尸体看,仿佛周围倒下的袍泽都是畜生的尸体,只有那只野狗才是他的同类一般。
浓郁的腥气与腐臭终于让士兵有了反应,他冲地面一阵呕吐,开战前所吃的压缩军粮混着奇怪的东西从他嘴里争先恐后地涌出来。
“吃!吃不下硬塞也得装进肚子里!一会儿吐干粮比吐胆汁强!”士兵回忆起开战前长官逼大伙儿吃东西时喊的话。
结果只有我一个人吐出来了。士兵这样想着,不无讽刺地笑了笑,真是多余。
他看到那摊呕吐物中看到了半只人类的耳朵。
就算是加餐了。
瞬间排空了胃袋里存储的能量,他的消化系统开始抗议地抽搐。
士兵没有任何感觉,尸体也好,呕吐也好,寒冷也好,饥饿也好,身上插着的七支断箭也好,什么感觉都没有。
他任由一切负面状态摧残着自己的身体。就算他想做什么,也没有精力了。透支的体力与失血夺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反抗能力,就连杀一条狗都要装死偷袭才能得手。
吐完之后,他便拖着野狗的尸体,艰难地在无数横尸间穿行。老远看去,他就想一只浑身浴血的恶鬼拖着自己的猎物,在炼狱中游荡。
突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绝对不该出现在这修罗场中的声音。这声音是如此真实又是如此充满希望,任何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都无法无视这样的声音。
那是幼童的啼哭声。
士兵灰白的瞳孔深处突然绽放出来一丝光彩,被年轻生命点亮的光彩越来越炽烈,像是火种一样,瞬间点亮了他的整个世界。
一定要找到那孩子,一定要活下去!这是士兵心里此刻最强烈的念头。
哭声似乎非常遥远,但士兵还是在江流集中找了间半残的木屋,他确信源头就在那里。
木屋被焚毁了一半,坍塌了一半,只剩几面断墙撑着烧成焦炭的横梁。令人惊奇的是,这样的一间屋子竟还有门,只不过那门才被士兵轻轻碰了一下便长叹一声仰天倒下了。
这倒出乎士兵的意料,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几乎就在门倒下的瞬间,一束冷光射来。身为百战精兵,他太熟悉那冷光了,那夺命的金属光泽和他遗失的战刀一样,无情、锋利、毫不犹豫。
“等一下!”士兵听到一声宛如九天玄女道喝的声音响起。
太晚了,冷光穿透了士兵的喉咙,就像他用匕首刺杀野狗一样,干脆利落不留任何余地。士兵不怪谁,在这种地方,谁留余地,谁就得死。
意识模糊得如此迅速,他勉强辨别出一个女人的身影朝自己扑来,他还嗅到一阵清淡的馥郁,这味道与刺鼻的血腥味形成的强烈反差深刻地烙印在了士兵的灵魂深处。
“别再杀人了!”女人叫喊着。
士兵昏了过去,昏迷中,士兵有着很奇怪的感觉。
谁在动我?士兵对于自己死后也不得安生感到非常愤怒却也无可奈何,毕竟这不是自己的地盘。
为什么我还有意识?我现在是孤魂野鬼么?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死去的长官,还有被一刀剁掉头颅的铁爪吴。岑将军变成鬼会是什么样子,哦,他掉进嘉陵江,就算变成鬼也是水鬼,估计是见不到了……为什么这么吵?战争不是结束了么,怎么还有打斗声?难不成地府也在打仗?那自己岂不是又要变成鬼兵,死也不得安息。
士兵听到剑的呼啸,听到脚步的嘈杂,听到缥缈悠远的笙歌……还有人类中剑时的闷哼。
……
士兵又一次醒来时,雨已经停了,幼童的哭声也停了,残破的木屋中血腥味弥漫。风流动着,透过破屋顶洒下的月光映着未及消散的血雾显得格外邪异。房间里除了死不瞑目的野狗外,又多了两具陌生人的尸体。这两具尸体绝对不是参加江流集战役的士兵,他们一身黑色短打,临死还握着造型狰狞形似日月轮的兵器。
士兵当趟子手时走过几年江湖,却没见过使这种兵器的,也不知这两人是什么来头。
管他们是谁,他们就算是黑白无常也跟自己没关系。
这个时候士兵发现自己身上的伤已经被人仔细地包扎过了,仔细得让人只能想到女人的手法,而且是个非常温柔贤惠的女人。正是这个女人,让士兵深刻体会到了活着与死了的区别,那就是痛觉。士兵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没死成。
身体的剧痛、肌肉的酸痛,与之相比饥渴的感觉简直可以无视了。
“真他妈疼啊!”他尖叫着,像野兽的嚎叫。
毕竟是个男子汉,只要还活着,怎么都好。士兵低头,发现那野狗的尸体还在,他便操着匕首,非常熟练地把狗剥皮、开膛,然后烤来吃了。虽然旁边就是两具尸体,虽然简陋的小屋怎么都挡不住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但这是士兵这辈子吃过最满足的一顿饭。
士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活着的幸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活着的痛苦。
他不知道江流集一战具体死了多少人,反正他这一方基本上都死光了,他认识的人里除了“兔腿儿”,应该没谁幸免。按照上头的说法,根本是一场必胜的仗,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但士兵并没有什么怨恨,相信别的活下来的人也不会有什么不满,愤世嫉俗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能在这样的时代里活下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而且本来就是我们发动的战争,幸存是上天垂青,死了也怨不得谁。士兵这样想着,于是活得心安理得。
木屋外突然传来了陌生的声音,似乎像是某种巨型蚯蚓在尸体间蠕动。士兵抽出匕首架在身前,因为满足而涣散的目光也变得如手中的匕首般凌厉,那动作迅捷得根本不像是个刚从濒死状态被救回来的重伤员。
“放松,放松,战争已经结束了。”推门进来的是一个半死的和尚,这样的称呼很奇怪,但这个家伙确实只剩下一半还活着。确切地说,这家伙的下半身已经不见了,他用裤子简单包住了自己的伤口,拿护胸当做滑板垫在身下,用双臂拖着残躯艰难地爬进了木屋。
“嗯,战争已经结束了。”士兵注意到半死和尚的僧衣外头套着敌方势力的服饰。
“冒昧打扰,但和尚实在是太饿了。临死之前,可以给和尚吃点肉么?”半死之人说得非常真挚,一点也没有因为自己快死了而显得焦略或恐惧,就像一个没吃午饭的人在说“今天晚饭早点吃吧”一样。
“哦,不用客气,肉还有不少。”
“感激不尽。”半死之人说着,用手撑着身体来到了士兵身边。士兵微笑着递给他一只狗腿,他的眼角瞥到了半死和尚的腹部:“我说,老弟啊,你的肠子露出来了,不要紧么?”
“是嘛?让施主见笑了。”半死和尚低头看了看,有些促狭地笑了笑,用一只沾满血污和泥土的手将那一截露出来的肠子塞回肚子,然后又撕下袖口包扎了两圈,这才抓住狗腿啃了起来。
“贫僧皮原野。”半死和尚冲士兵路痴一笑,那表情灿烂得根本看不出来他只剩下半边身子了,但他的眼里却没有任何光彩,死一般的灰暗。
“景老猫。”士兵回道。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猫老大’,失敬失敬。”皮原野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异,“没想到为了对付我们洪荒谷里的闲云野鹤,天道盟真是叫来了一群不得了的家伙啊。”
“墨池寺的诡术铁算,如雷贯耳。”景老猫苦笑,用手敲着皮原野肩头的“校尉”军衔道,“连你这等人物都只得校尉之衔,洪荒谷海纳四方大能无愧其名,这一仗输得不冤。”
“景施主太瞧得起和尚了,很多事你我都意想不到。江流集一战只是天道盟自己导的一出戏,我们才能惨胜而归啊。”
景老猫皱了皱眉头,诡术铁算武功虽不算登峰造极,在江湖中却也算个人物,即便是在洪荒谷这种强绝的势力中混个中高层应该不难,他说这番话,显然别有所指:“此话怎讲?”
“施主可知,天道盟是谁组织的?”
“逐鹿·九命妖,姚天下。”五年前惊魂楼楼主姚天下在中华大会上登高一呼,号召中原武林组件联军讨伐洪荒谷中的异族,这是江湖人尽皆知的事情。
“那天道盟的盟主又是谁?”
“点星剑法唯一传人,北野真人。”死劫中逃出生天,景老猫的心情非常好,他不介意跟这个诡术铁算多聊一会儿。
“楼主大人功参造化,大费周章组建天道盟,自己却不当盟主……”反正自己已是将死之人,在确认自己生命无几的时候,皮原野觉得把这种足以震动江湖的隐秘说说也无所谓。
那些家伙连墨池寺都坑了进去,那就索性把真相都给抖出来。这猫老大在剑南道也算是个人物,如果能借他之口给那些黑手找点麻烦,也不错。
“打住!”景老猫突然叫停。
“嗯?”
“我对上面的那些事不感兴趣,咱们换个话题吧。”景老猫咧嘴冲皮原野笑道,“你老家是哪的?”
皮原野有些愕然地看着景,过了一阵子,他才释然笑道:“倒是和尚着了相了。”
“早就听说墨池寺的牧空大师十四岁智取松峰寨,十七岁横扫灰岩庄,二十七岁进入洪荒谷诨名皮原野,三十五岁便修成禅宗七十二般绝技中的两种江湖人称诡术铁算……如今年过半百,大师想过家么?”
“想啊,当然想了,特别是现在,做梦都想回江南老家。”皮原野像是忽然顿悟了一般,死气沉沉的目光一下子亮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景老猫觉得眼前这个手拿狗骨头的和尚是个半活的和尚,而不是个半死的和尚。“最是忘不了,跟师傅离开家时踏着青石板,看到的那一桥烟雨。”
景老猫看着皮原野,笑道:“大师,我若能带你回家,能否答应我三件事?”
皮原野苦笑:“我一个将死之人,能答应你什么事?”
“我说带你回去,当然不是带你的骨灰回去。大好的江南,抱一盒子骨灰乱跑多煞风情?”景老猫笑得非常自信,皮原野觉得自己越来越看不懂这个猫老大了。
“你能救我!?”皮原野瞪大了眼睛。
“我没那么大本事,但我知道这江流集中有一个人可以。”
“这一战……”
“不打紧,连我都没死,那个家伙肯定死不了。”景老猫非常自信,就算全天下的人都死了,兔腿儿也绝对不会死。“那个家伙没学他师傅武功的一成,但保命的手段却学了十二成!”
“难道是舞空之术?”
“这世上有什么比医术更能保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