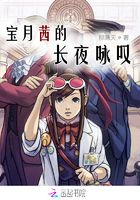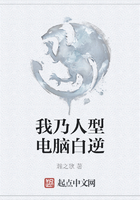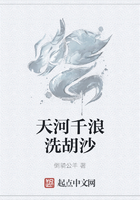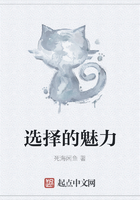治学严谨堪为师范
中国近代风云人物梁启超,其前半生一直置身于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但到了晚年,则致力于著述及讲学。20世纪20年代,即在南京留下踪迹。
东南大学,延揽名家讲课
南京的东南大学原是清末兴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民国后,为进一步振兴教育事业,1921年7月改办为“东南大学”。当时中国只有两所国立大学:一所是蔡元培为校长的国立北京大学,再一个就是号称“东南最高学府”的东南大学。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主张“自由讲学”。延揽了国内外许多名流学者,不分党派,利用这个最高学府讲坛,充分发表个人的政治主张,让学生也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1992年(夏天,学校董事会决定仿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办了暑期学校。担任暑期学校课程的教师,除本校权威教授外,郭秉文还罗致了海内外知名之士:美国杜威博士讲授《实验教育哲学》;美国吴卫士博士讲授《昆虫学》;美国孟禄博士讲授《教育学》;德国杜里舒博士讲授《生机哲学》;胡适博士讲授《实用主义》;梁启超教授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江亢虎博士讲授《劳动问题》;张东荪教授讲授《新闻学大意》,还有本校常务校董和工科教授杨杏佛的《政治改造思想》等,此外还延聘了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讲了一次《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世人所必需》的讲座。
治学严谨,梁启超堪为师范
为此,暑期学校为讲师们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大会一结束,学生们挤在食堂,禁不住纷纷对大师们的仪表品头论足,特别是杜威、胡适,有人大失所望地说:“想不到杜威不过是个瘦老头。”有人说胡适不像个学者,“倒像花牌楼(今太平南路一段)的商人”。
但大家对梁启超却普遍印象较好,首先是他的谦虚态度,不似胡适等人讲话目空一切。在学生们眼中,梁启超是位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的学者。梁启超此时暂住在成贤街校舍中,每逢到了星期天,不少青年都喜欢去拜访他。大家发现,他不仅为人谦诚,而且治学勤恳,星期天也有工作计划,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右手写文章,左手扇不停挥,有时一面写,一面又在答复同学提出的问题。当写完一张时,便吩咐他的助手拿到另一间房屋去打字,一篇打字机印稿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上了。此外,他每天还要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而且摘录下必要的资料。在与学生们交谈中,他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这句话来勉励他们。在勤恳治学方面,梁启动的确做到了以身作则。
由于大师们各有千秋的讲学,很快发展到学员们自下而上的自由评论。对于学员们对教授们提出的疑问,东南大学的杨杏佛教授都有问必答地作出了相应的答解。而梁启超对此则多方回避,甚至表示矜持。以“我不能赞成一词”来作应付,从而又引起许多学员在“学者态度”上的争论。有人主张真理愈辩愈明,应大力提倡杨杏佛教授的学者态度;有人则认为多言多败,应永远保持虚衷自守。对政治“三缄其口”的戒律。这些话很快传到了梁启超耳里,他很敏感,立时郑重地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而是反对批评的不自由,我的态度同杏佛并无两样……我也说过同大家一起进行改错。”经他这么一表态,学员们关于学者态度的争论就此涣然冰释了。
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期间,还参加了东南大学文、史两系全体师生在鸡鸣寺举行的一次联欢会,当时正是盛暑时节。鸡鸣寺当家的老和尚见到梁启超到来,十分高兴地捧出文房用具索求墨宝,梁启超略为沉吟片刻,便奋笔写下了陆游的诗句:“江山重叠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从中不难看出这位昔日政坛骄子对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幻仍怀有不满情绪。作品完成时,喜得这位老衲连说:“小寺一定要把任公的墨宝藏之名山,垂之千古。”联欢会上,一位学员趁梁启超高兴之际,向他提问:“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启超听了顿时庄重起来:“我认为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二千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会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趣味人生,梁启超活得坦荡
这一年(1922)的夏天,梁启超还为东南大学暑期班学员作了一次颇有趣味的专题讲座——《为学的趣味》,表达了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引起了学员们的极大兴趣。他认为,人生最合理的生活应该是“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什么叫趣味呢?梁启超解释说:“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他认为除此之外,像赌钱、吃酒、做官之类的事在做时或许有趣,但并非能以趣味终。输了钱如何?吃酒吃病了如何?没有官做了又如何?因此,他提倡做学问,认为“学问的本质能趣味始,以趣味终……”他自认为:“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致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噜,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到趣味。”这种积极的人生观无疑成为梁启超一生勤奋地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动力。
五四史学精神的领航
现代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一方面指政治与经济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文化现代化。文化,中国狭义所指是“经史子集”,故如学界共识,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无法绕开史学现代化这个重要课题。通常,人们习惯将“五四”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起始,其实20世纪最初10年十分要紧,譬如新史学理论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前奏。
一、解“史”如解“尸”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运动的倡导者。他在《新史学》中对中国 旧史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他看来,中国旧史学推其大端,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非史也”,只不过是中国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产生这样弊端,是因为过去的史家总抱着如此的想法:天下者乃君主一人之天下。故此为史也。只是论述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失之。梁启超说明,国家与朝廷不是一回事。要正确认识什么是国家,国家是君主与国民合而所成之物。单为君主作史而舍民众,是乃非完整的史学,或根本不为“史”。
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史学乃君主与“个人”之史。中国历史成为君主的家谱与彰显“个人”功德的“墓志铭”。中国历史不否认个人的作用,但也绝不可忽视民众的作用。他将民众说成是“群”。中国“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其文化根源就在这里。
其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记录陈迹,乃是为今务服务。记陈迹而不求于今务的实际效用,其记录乃是无用之记录。事实正是,记录与分析过去,如同诊病,中国民族于近代已有沉病在身。“史”犹如“尸”,解“史”如解“尸”。解“史”可知中国历代王朝症状,据之又可知近代社会不振之病因,继而投以药石。进而言之,今天是过去的继续,洞悉今天,即可对历史作更深刻的探究,舍今而研史,也无法对史作正确的判断,将无新意,无发见,无创获。
其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举例说若人有四肢、身体,有手足、脏器与皮毛。中国过去的史学研究外部事变,如研究人体之皮毛。然而,精神与哲学是中国之史的内在驱动,表现了中国的理想与追求。中国历史过程,是时间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人精神发展与演化的过程。研究“历史”而不去研究中国“精神”,则使所记录的人物如蜡人院的蜡象,全无生气。如此,中国人读史,只对皇帝治术有加,而于民智启发,究有何用?
二、“进化论”与“心力论”
在对中国旧史学作了有力批判以后,梁启超继而提出“新史学”的创言,首先,新史学求其“新”,要“述进化之现象”。关于宇宙之演化方式,学者所论大体有二:如“循环之状”,如“进化状”。梁启超倾向于“进化论”。人类历史之演进日日“进化”,“往而不返”,“进而无极”。凡述进化者为“真史”,否则不然。历史由人群所造,叙述进化之历史也就是叙述人群进化之历史。 梁启超注意用因果律解释历史,并试图将历史学提升到“科学”层面。他说,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以前只有自然科学可以说得上是“科学”,所以治科学是离不开因果律的。
百科启蒙第一人
不论从他对众多历史人物、历史事变的影响,还是那些人、那些事对后来的影响,以及近年学界乃至全社会对他日益频繁和深入的“重新发现”来看,把梁启超列为20世纪中国第一人,理由是充分的。
梁启超10岁中秀才,16岁中举,翌年结识康有为,被康宣讲的西学知识和变法之论所震慑,遂拜为师,告别旧学,走上经世致用、维新救国之途。甲午年(1894)赴京会试期间,助康发动“公车上书”。不久去上海主《时务报》笔政,从此名声鹊起。又应邀出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和谭嗣同等培养了一批维新志士。1898年百日维新时,他年仅25岁(康40岁,谭33岁),参与宣传策划和联络组织,执笔起草变法文件,史称“康梁变法”。戊戌政变后,他原“抱定一死的决心”,只因谭嗣同郑重托命及日本公使林权助力劝,才逃离虎口。
初亡命日本,梁启超相继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介绍西方思想和科学知识,以独创的“新民体”开白话文先河。1900年作《少年中国说》,两年后作《新民说》。后者以“培育中华新公民”为旨,主张吸收西方文明以更新传统。又鼓吹“破坏主义”,若非康有为制止,梁差点儿跟孙中山搞成联合。1903年考察美洲后,他相信共和革命不合国情,转主立宪,提出“保皇即革命”,图谋助光绪皇帝复位。不久跟革命党有一场著名论战。以往史书断言,此后他转向反动,政治作为再无可称道。殊不知,如近年学者指出:“革命派中不少人正是借助梁启超的‘启蒙’,才学到了一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一些革命派人士所写的文章,包括脍炙人口的邹容的《革命军》,甚至大段大段地抄录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文章。”就在那前后,梁与康在学术、政治上分歧日深。他鼓吹立宪,遭到清廷、康氏保皇党及革命党三面夹击,却获普遍响应,直至清廷被迫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事前,奉旨操办大臣赴日考察,曾私下请教他这个通辑要犯;梁为其代拟奏折、草案等,逾20万言。史家称: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而十多年后,李大钊、毛泽东分别在北京、长沙建立学会,仍以“少年中国”、“新民”命名,足见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