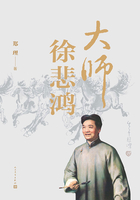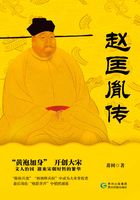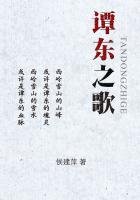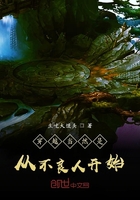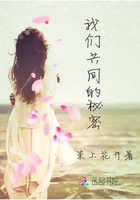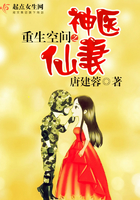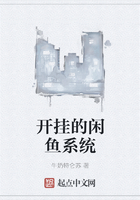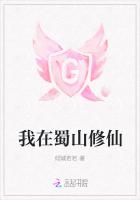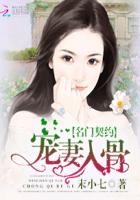人权平等性的实现需要有一个不断斗争不断充实的过程。强调通过运动程序逐步实现人权的平等性,这是梁启超人权思想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女权运动程序而言,实际上涉及三个阶段上的不同内容的平等权。“一是教育上平等权,二是职业上平等权,三是政治上平等权”。从程序上看,这三种意义上的平等权的实现具有先后顺序,应该依次推进。梁启超的主张是:“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在人权运动程序论方面,梁启超的“学第一”的主张体现出对人权主体性和解放性的重视。人权是主体自我意识到的权利。人权意识的发达与否直接同主体的觉悟程度相关。人权运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是主体的自觉自动,是主体争取自我解放的斗争。人权的主体性和解放性决定人权运动的自动性。梁启超非常明确地强调人权运动必须是自动的:“美国放奴运动,不是黑奴自己要解放自己,乃是一部分有博爱心的白人要解放他们,这便是他动,不是自动。不自由动得来的解放,虽解放了也没有什么价值。不惟哪此,凡运动是多数人协作的事,不是少数人包办的事,所以要多数共同的自动。”人虽然都具有主体性,因而人权运动作为自觉自动的运动成为可能,但由于智识程度不同,故自觉自动的程度也就有所不同。“不从智识基础上求权利,权利断断乎得不到,侥幸得到,也断断乎保不住。”注重人权的智识基础,这一点也是梁启超人权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人权平等性的认识同人的智识程度密切相关。人的知识程度越高,其觉悟程度也就越高,从而人权意识也就越强。因此,“开民智”和不断增强“智识基础”应该成为实现人权斗争的最基本的环节。
就重视人权的知识基础而言,梁启超的新民说同严复的“三民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无论在理论形式上还是在具体主张上都大致相同,它们都将开民智作为求权利的动力源泉。但是,就人权的平等性同民智的关系而言,梁启超和严复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却有很大的不同。严复将平等理解为人类理想状态的力智德的平等,且认为“民主之所以为民主者,以平等”严复说:顾平等必有所以为平者,非可强而平之也,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使是三者平,则郅治之民主至矣。”。将力智德的平等作为民主政治的标识和根基,进而将民主政治的目标推向遥无期限的未来,这是严复过程分离论错误得以形式的原由。尽管梁启超也曾有过类似的过程分离论的认识错误,但梁启超追求的不是可期不可得的力智德的平等。梁启超注重的是法律上的平等。这种平等一方面表现为国民在立法上得以平等地表达意思,另一方面国民在立法上不被划分为不平等的阶级。前者具有积极的主动意识;后者具有消极的被动的意味。当他讲求立法权的性质和意义时,才思横溢,博涉广论,情理充分。当他论及等级制度四民问题时,便简单认为中国自战国时期废除“世卿之制”后,“四民平等”问题便大致解决。这说明梁启超注重的是立法上的阶级平等。他希望通过在智识基 础上求权利,达到不仅废除立法上的阶级不平等现象,而且根除立法上的各类特权,包括政党特权,教会特权、男子特权、君主特权、贵族特权等。他将体现此类特权的立法一概斥之为“恶法”就表明他所讲求的平等重在法律上的平等权。严复虽然也讲法律平等权,但在观念深处更着重事实平等,以致其民主概念也是卢梭式的直接民主。梁启超虽然也反对事实不平等,但在观念深处更着重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因此也更强调选举权和参政权。
平等固然是民主的基石。但作为民主权利的平等权更应该是法律上的平等权。人生而平等是人格尊严的平等,这种平等在法律上应表现为平等地享有人所应有的权利。在这方面,梁启超的思想比严复的思想更符合实际。严复将治制之极盛的民主解释成人人自为自治的小国寡民式的直接民主,由此必然不会详究选举权和选举程序之类的间接民主制所不可或缺的环节。梁启超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陷得较深,因而更倾向于符合儒家理想的间接民主制度,更注重选举权和选举程序的研究。
选举权是国民平等地表达意志和参与政治所必不可缺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梁启超对选举权的研究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是独具特色的,且相当深入系统。他从宪政的角度对选举权制度作了划分:“人民选举议员之权,名日选举权。选举权之广狭,各国不同。可分为普通选举与制限选举之两种。普通选举者,谓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也。制限选举者,谓以法律提定若干条件,必合于此条,或不及于此条件,乃得有选举权也。”梁启超对选举权的划分,显然受到日本宪法学者的影响,直接采用“制限选举”的概念。但他在概念的表述方面和术语使用方面又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实际上普通选举在任何国家也不能彻底实现。选举权在任何国家都会受到一定限制,只不过受限制的标准和程度不同而已。他主张将“普通选举”一词改为“普通制限选举”,而将“制限选举”一词改为“特别制限选举”。前者指选举权受到年龄、性别等限制;后者指选举权受到财产或教育程度的限制。
关于外国法律规定的选举权资格限制在中国的条件下哪些可以实行的问题,梁启超认为根据当时国情大致可以采用的有:国藉限制、属性限制、住所限制、公权行使限制和职业限制。他坚决反对对选举权实行阶级限制和财产限制。至于教育程度限制,他主张在当时教育未普及的情况下还是应该适当采用。他关于选举权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甚至比当时西方某些国家法律规定具有更多的民主色彩。
在普通选举方面,梁启超不论述了平等选举和等级选举。他讲的平等选举指一人一权,举国同等。等级选举指限于某种类的人有不同于民的优越权。其方法有两种:一是复数投票制度;二是分级投票制度。复数投票制度指将有选举权的公民根据其纳税总额分为不同等级,各等级选举议员人数不等。对于等级选举制,梁启超基本上持反对态度。但考虑到权利的智识基础和提高知识群体参政程度,他主张当时中国凡有科弟官职及学堂毕业文凭者,得有投两票之权。
至于选举,梁启超认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各有利弊。直接选举的优点在于:第一,在直接选举中,被选举人为选举人直接信任,可以代表选举人意志。在间接选举中,被选举人虽为第二级选举人所信任,未必为原选举人所信任,因而多数人民意志不能直接反映在国会中。第二,直接选举,则选举人直接感受到选举的利害关系,对选举必然热心。间接选举,由于原选举人的意思不能直接反映在国会中而往往缺乏热心。第三,直接选举手续简单,不像间接选举手续复杂,使国家人民增加劳费。第四,间接选举的结果,基本已由原选举人选举时已决定,因为第二级选举人受命于选举人的投票,从这一点看,第二级选举人成为赘疣。间接选举的优点在梁启超看来主要在于:第一,原选举人较之第二级选举人在知识能力上为低,不易鉴别被选举人的才干,所以使用间接选举方法易得人材。在教育未普及的国家,间接选举的这一优点更为突出。第二,原选举人只熟悉周围的人们,在其邻里乡党以外所知甚少。用间接选举方法,第二级选举较易了解议员候选人。第三,用间接选举方法,第二级选举人受原选举人委托,对于选举更为慎重,并以公心行之。由于直接选择与间接选举各有利弊,梁启超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上院采取间接选举制。至于下院,他主张逐步实行直接选举制。
在选举制度方面,梁启超还论述了选区的划分方法、中选计算方法、选举人名薄的制作、投票方法、选举机关构成等问题。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非常强调对选举权的法律保障。为此,他主张实行开票公开制度、处罚不法行为制度和选举诉讼及中选诉讼制度等。为了增进国民的选举权意识,梁启超不建议待立宪思想逐渐普及后,可以推行强制选举法,使人们意识到选举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
对抗可能出现的专制行为。
梁启超抵抗权思想的彻底性还表现在他既反对恶法优于无法论,也反对恶法亦法论。他批判中国古代慎到“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的观点,指出法若不善,不足以为治。“法而不善,则不肖者私便而束手焉。无论得人不得人,皆不足以为治。”恶法优于无法论者通常满足于表面的稳定秩序而不惜以牺牲人民的权益为代价。其根本立场是站在专制权势一边为专制主义制造舆论。这种人的论调当然会受到为自由人权奋斗的梁启超的批驳。至于那种纯实证主义的恶法亦法论,同样不符合法的概念,为梁启超所不屑一驳。他指出:“乱国之立法,以个人或极少数人之福利为目的,目的不正,是法愈多而愈以速乱亡。“对于违背法的宗旨的专制主义法律,梁启超来采取法非法论的立场而根本不予承认。非但如此,他还号召人们拒绝服从恶法,行使抵抗权利。他主张的法治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概念相念,即法治必以良法善法为前提。但梁启超的法治论更接近现代抵抗权论的水平,充满人权主义的抵抗精神”。
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深入论证了人权的对应性或抵抗性,号召人民为维护人权而奋起斗争,而且他一生坚持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抵抗权主张。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从流亡日本到创办《新民从报》,从发动护国战争到反对张勋复辟,梁启超始终以无所胃惧英勇不屈的抵抗精神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