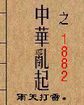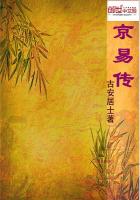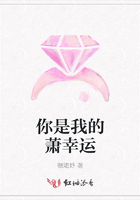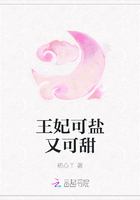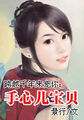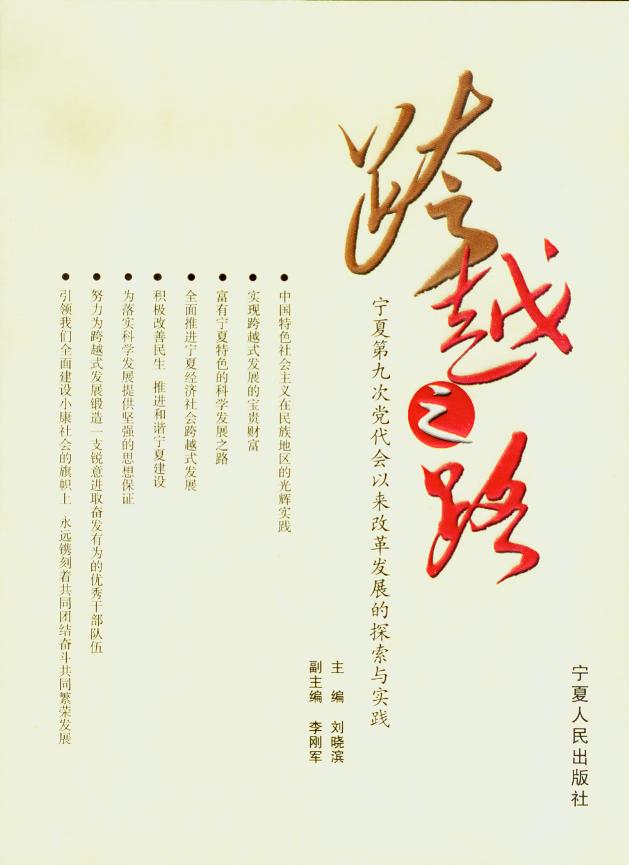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汉族。浙江绍兴人,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5年春,柔石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当时鲁迅先生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一周一次。因为有很多外系的学生也来听鲁迅先生的课,去迟了,往往只能站在教室外的过道里听。所以,每逢鲁迅先生讲课,柔石必早早赶到教室。鲁迅先生讲课广征博引,语言幽默生动,语调平缓有力,常引得堂内发出笑声。鲁迅先生带有浓重绍兴口音的普通话,与柔石家乡的宁波话有许多近似之处,他听来感到特别亲切,并详细地作下笔记,不放过先生的每句话。
1928年9月,柔石在王方仁、崔真吾带领下拜见了当时住在上海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的鲁迅先生。而这一会面可说是柔石这一生的转折点。
柔石向鲁迅倾诉了自己对文艺的深深喜爱,以及创作《旧时代之死》的思想动机,并将他随身带的书稿,恭恭敬敬地呈给鲁迅观看。鲁迅应允定当仔细阅读这部书稿。
景云里23号临近宝山路,非常嘈杂。当时恰好同弄的18号空出,鲁迅便把它租下,并邀请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三弟(周建人)一同居住。当时柔石、王方仁和崔真吾三人也无固定住所,鲁迅就介绍他们租下了刚刚搬出的23号。此后,柔石与鲁迅、周建人两位长者朝夕相处,几人时而议论社会现状,时而交谈文化心得,柔石因此受益匪浅。
鲁迅悉心审阅了《旧时代之死》的书稿,赞之为“优秀之作”。他把柔石介绍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让他们出版这本书。同一天,他又读了柔石的小说稿《人鬼与他的妻的故事》,看见稿上署着“柔石”两字,疑问地凝视了一下。柔石当即解释说,这笔名取自家乡方祠前一道小桥上题刻着的“金桥柔石”四个字。他儿时搞不清这四字的含义,现在感到为人处世,应该刚柔相济。鲁迅会心地微笑着问:《易经》有“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老子》又有“守柔曰强”之说,你知道么?鲁迅觉得这小说写得不差,决定放在他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第一卷第五、六期连载发表。柔石自学校毕业后,除了自费出版短篇小说集《疯人》外,在像样的杂志上公开发表作品,这还是第一次。
当时,王方仁与柔石、崔真吾都无固定的经济收入。1928年10月的一天,王方仁提出合伙办刊物和出版图书的建议,说景云里居住着众多文化名人,他哥哥的教育用品社可帮助先垫付印刷的油墨、纸张,还可帮助代售。崔真吾与柔石很感兴趣,就去与鲁迅先生商量。鲁迅早于1925年在北京时,就曾扶助韦素园兄弟与李霁野、曹靖华等几位青年创办《莽原》周刊和未名社,所以对此事也表示支持。几经商议,大家决定创建一个文艺社团,出版一种刊物,每人的股金为50元。当时柔石交不出钱,还是鲁迅帮他垫付。为使启动资金能够更加充足,鲁迅还介绍许广平也参加了一股。这样鲁迅用自己的稿费,实际负担了全社五分之三的资金。鲁迅想起《文选·陆机<文赋>》中“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话,提出把这个文艺社团命名为朝花社,拟办的刊物也就名为《朝花》周刊。
《朝花》周刊第一期于1928年12月6日面世。这虽然只是一个16开8版的小刊物,鲁迅却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精心选用了英国阿瑟·拉克哈姆的一幅画来饰刊头,又为刊名“朝花”书写了美术字。他手把手地指导柔石说:办刊物既要求文章内容扎实,版面设计、编排形式也要生动活泼,不能搞得密密麻麻,给人压抑感。他还主张版面可以选登一幅以木刻为主的外国美术作品,这在当时国内文艺刊物可说是个创举。柔石在鲁迅的指导下初做编务,还常常到文具社、印刷所跑制图、校字之类的杂务,热情很高。
早在学生时代,柔石就爱好美术。如今看到鲁迅亲手书写了雅致的美术字“朝花”二字,并找来恰当的名画作饰题,一种同调共鸣的惊喜感油然产生。他想方设法搜集整理国外有关木刻的资料,一心做好鲁迅的助手。《朝花》周刊第八期于1929年1月24日出版,柔石与鲁迅合编的《艺苑朝华》第一辑《近代木刻选集》和第二辑《谷虹儿画选》,也以朝花社的名义于26日印成。这两个集子的出版,开创了我国介绍国外进步木刻艺术的先河。
一次,柔石听鲁迅介绍说,英国著名木刻家吉宾斯对于黑白的观念常有意味深长的独创。为求印刷效果的逼真,他径自去信向吉宾斯求商。结果吉宾斯夫人来了复信,并附寄三幅黑白木刻拓片。柔石高兴地把拓片和信件都交给了鲁迅。鲁迅为之妥善保存。这宗珍贵的历史文物,见证了鲁迅与柔石倡导中国木刻运动的劳绩。
朝花社这套《艺苑朝华》文艺丛刊,按当时的计划,一共要出12辑,即还要出《新俄画选》、《法国插图选集》、《英国插图选集》、《近代木刻选集》等。可惜柔石不懂经营,王方仁那个开教育用品社的哥哥,给朝花社供应的纸张,多是从拍卖行里兜来的次货,油墨也是廉价的,用来印制木刻图版,影响了质量和销路。他为朝花社代售书刊,还常常借故不付书款。朝花社经济上遭受极大损失,柔石只得用自己的一点稿费去抵债。鲁迅曾愤慨地说:“我这回总算大上了当”,最后他“以百廿元赔朝花社亏空”。1930年1月朝花社“社事告终”。然而柔石所展现的人格魅力,赢得了鲁迅的称赞与信任。他对柔石的评价是:“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柔石自得到鲁迅的关爱后,更加“忠心于文艺”。1929年是柔石著译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他创作了《二月》等中短篇小说20篇、散文随笔3篇、独幕剧2部、诗歌3首、翻译作品17篇,共约三十余万字。1930年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希望》,并发表了短篇新作《为奴隶的母亲》。
1930年5月,经冯雪峰、黄理文介绍,柔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29岁。
1929年10月初,共产党员、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冯乃超会见了柔石,说起自己过去由于对鲁迅“缺乏了解,以至错误地批评了他”的负疚之情,表示很想去见鲁迅,但又心怯。柔石告诉冯乃超:鲁迅不是这样的人。柔石热情地带冯乃超去见鲁迅,鲁迅满面笑容地接待了他,彼此取得了谅解。这次会见消除了进步文艺团体之间的隔膜,为筹备成立“左联”铺平了道路。
这以后,柔石更加倾心尽力,和冯雪峰一起照料鲁迅的生活与安全事宜。冯雪峰曾说:“我那时感觉到,鲁迅把柔石简直当作家人似的,就是偶尔看电影、游公园,或参观画展、出席会议,也总是邀柔石一同参加。”鲁迅到内山书店看望内山完造,经常与柔石同行。平时,柔石常到鲁迅房中,征询有些什么要代办的事,帮助处理一些诸如寄信、寄书、汇款、取款,以及给青年作者退稿或赠书等杂务。两人之间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载及近百次。以致后来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深情地说,柔石是他在上海“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办点私事的人”。还说:“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
1931年1月17日,柔石参加完左联执委会后,下午在东方旅社,和李云卿、林育南、冯铿、殷夫等一同被捕。在龙华监狱,他被钉上重达18斤的“半步镣”,但仍设法通过送饭的狱卒,带出一封转交给冯雪峰的信,信中三次提到的“大先生”即指鲁迅,要他注意安全。
2月7日,柔石和23位战友被国民党杀害。鲁迅闻知柔石牺牲,彻夜不寐,悲愤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惯于长夜过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