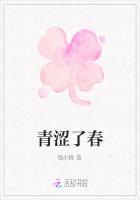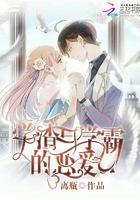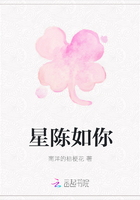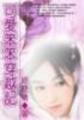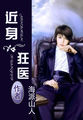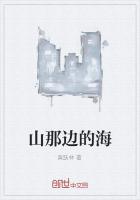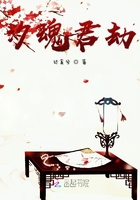县城小小的班车站售票厅里,此时只有吕聪一家人排队买票,手里大包小裹,几乎全是送给老人的食品和营养品,另外还有给吕聪的舅舅舅妈拿的几样东西。
吕聪和舅舅舅妈也同姥爷一样不熟,但吕聪喜欢姥爷那明朗的笑容和舅妈那质朴勤劳的品质,却不喜欢舅舅那张阴沉又胡子拉碴的脸。吕聪听妈妈说过,她们几兄妹小的时候,属她舅舅脑子最笨,学习成绩最差,所以早早就辍学,回家娶妻生子种地了。每次无意中说到这,吕聪妈妈的一张圆润、油光满面的脸上总是隐隐约约带着自豪、庆幸的表情,自豪的是自己学习成绩好从农村考了出来,从此吃上了公家饭,住上了城里的楼房,算是家里几个孩子中过得最好最有出息的;庆幸的是,没有像其他三个脑瓜聪明但由于各种原因早早就嫁人的姐姐一样,如今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穿着老土,整天围着锅台转;由于是老小,父母一直供她读书。
吕聪怎么能理解妈妈的这种心情呢?毕竟她没有生长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没有身边围绕、陪伴着几个各种各样的兄弟姐妹共同成长的经历。
班车从县城班车站出发,又途经环城路,出了县城去往姥爷家的是一条还称得上平坦、宽阔又笔直的柏油公路。路两旁没有多少人家,大都是荒芜的田地和已经结冰的河流。吕聪已经没有心情和精力欣赏风景了,坐在车座上昏昏欲睡,头随着车身的晃动而左右摇晃。
这一次他们一家人并着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吕聪还是坐在最里边靠窗的位置,那是她永久不变最喜欢的角落。
他们一下车便看见吕聪的姥爷开着一辆三轮车停在道边村口,是来接他们的。
吕聪走上前,不好意思地微笑着,小声说了句"姥爷好!〃
她姥爷笑着点头,没说话。
他们从打开着的车后边的门上了车,坐到车里两排的座位上。
她妈妈就像刚回家的孩子一样,一路上和自己的爸爸有说有笑,那口气十分自然。沉默的只有吕聪和她爸爸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着。只有老人向他们问上几句话时,才应答两句。
三轮车带着巨大吵闹的声响飞速穿行在乡间白色的小道上,道路两边紧挨着枯萎的树木,伸长的树枝有时会剐蹭到车棚子边上,发出一种响亮的响声。
最后驶过一座小桥,再路过几家门口,便到了地方。
吕聪安静地跟着爸妈跨进院门,院子里被打扫得十分干净。正中央是新装修的正房,左右两边是厢房。
显然,姥爷家的房子更宽阔明亮,更高大。吕聪不禁觉得有些心里不是滋味,要是爷爷奶奶家的房子也这么样就好了。
吕聪听说大舅过完年后就立即动身外出打工去了,此时不在家,心里竟然暗暗地感到高兴。
舅妈好像比上次见面时更胖了,圆滚滚的脸庞油光满面,鼓囊囊的肚瓜像怀了孩子,吕聪突然想起妈妈说过,舅妈吃饭向来是无肉不欢的。不过还是那么热情、质朴,用一口纯粹的当地乡音对吕聪一家人嘘寒问暖,对吕聪尤其关心,用一双眯缝小眼不住地上下打量着吕聪,眼神里有一种亲切又明亮的光芒。吕聪一感到这道光芒在自己的周身游走扫荡,脸便顿时发起烧,感觉滚烫滚烫的,绯红的云彩笼罩在圆圆的脸面上,红彤彤得活像熟透的红苹果。
一进屋,吕聪坐在炕前的沙发上,沙发前的大电视机打开着,吕聪看了屏幕一眼,见在播放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心里暗自嘀咕,真是无聊,没完没了地重播!
她的爸妈和姥爷、舅母刚开始并排坐在炕沿边拉家常,随后没多久都脱了鞋上炕,在炕里边靠着窗台坐着。吕聪妈妈和自己年迈的唯一的父亲紧挨着坐在中间,聊得热火朝天,说话声几乎掩盖了电视机发出的声音。两边分别坐着吕聪爸爸和她的舅妈,都边看电视边时不时地在那对父女之间插几句话。
吕聪对他们的谈话没有兴趣,拿起横放在茶几中央的遥控器,不停地换着台。
"聪聪,你坐那儿不冷吗?快上炕来呀,这暖和。〃是她舅妈在温柔地招呼她。
吕聪听见声音,不耐烦地回过头,冲着舅妈微微一笑,摇摇头,过了一会儿说:"我不冷,在这挺好的。〃心里暗自嘀咕一句:"不好我也会跟你说的。〃便又转回过头看电视了。
吕聪听见背后爸爸那低沉、缓慢的说话声:"不用管她,她在那儿没事的,她也喜欢一个人看电视。〃
"哦,这样啊。〃她舅妈仿佛恍然大悟似的回答。
来之前他们打算好了,在这住一宿,第二天下午坐火车回县城,车票已经买提前买好了。
很快夜色降临,吃完晚饭后吕聪继续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时她已经找到了自己喜欢看的节目。听着炕上热闹的说话声,渐渐地,吕聪不感到不自在了,心里也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的感觉。
那天晚上,吕聪最后结束了奔波劳累的一天、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朦胧睡去时想着:"来这也挺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