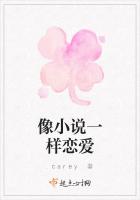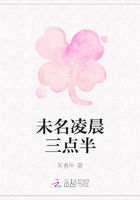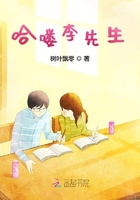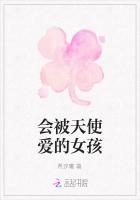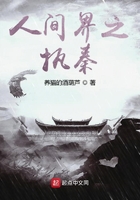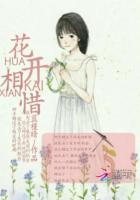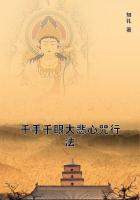班车就在吕聪紧张兮兮地注视下平安地驶过整个盘山地段,最终把它的四个车轮轻快地落脚到了平直的路面上,继续前行。
吕聪怀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心情放眼四周,突然发现窗外道路边的田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由于人迹罕至又未遭受汽车轱辘无情地碾压而有幸保持着初落时的圣洁。她的眼前一亮,心也瞬间变得明亮起来,随着班车的飞驰而荡漾。很快,班车驶进了一个小村庄,雪不见了——退场了,接连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个小巧质朴又大同小异的农家院。
即使车速很快使得吕聪不能仔细看个清楚明白,但只一晃而过,也能大致了解农家院的样子和其间的种种东西。那院子正中央坐落的窗户紧闭的平房让吕聪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浪漫遐想之中。
吕聪的爸爸妈妈是在班车已经驶进县城郊区时醒来的,一睁开惺忪睡眼他们眼前的道路是柳河,道路两旁的枯树干飞快倒退,吕聪还是那个身子完全轻松地靠着椅背的姿势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只是头不再向着窗外,而是对着正前方。
吕聪妈妈懒洋洋地打个哈欠,看看戴在腕上的手表,时针和分针已经快要重合在中午十二点的位置,还有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她心里计划着,一会儿班车驶进车站下车后,他们先到左近的拉面馆,接着回家把手里拿着的从吕聪爷爷奶奶家带来的东西该放茶几上的放在茶几上,该装进抽屉里的装进抽屉里,把一些垃圾没用的则一起扔进那间没人住的小卧室床边地下的空箱子里,等着哪天收破烂的吆喝着来到家门口时把它们卖了换些零钱。最后,他们在家里略微休息几分钟、梳洗梳洗以后,又要接着出门了,到班车站售票大厅里角落处的小卖铺买几样她姥爷爱吃的点心和糖果,就又要脚步匆匆地踏上另一班去往另一方向的旅程了。不过,这一段路程不必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只要半个小时左右便可到达目的地。吕聪对此时常想,要是爷爷奶奶家也这么近,该多好呀!
可是事实总是这样不尽如人意,仿佛偏要故意跟人作对似的。
班车像一个久经沙场、凯旋而归的将军,翻山越岭历经种种艰辛和磨难,终于回到了这座安宁、平静的小城母亲的怀抱。
吕聪的目光又专注地看着窗外。她坐的是汽车靠右边的单人座位,离中间的车门很近,又能很方便地很完整地看到柳河岸边一路的风景。
岸边修建了一道白色堤坝,其距离公路之间的地段都铺上了一块块白色砖瓦,偶有起伏的地势,其上则人工修建了有利于人们行走的台阶。
这时,那上边有走着几个三五成群地散步的人,吕聪看不太清他们的面貌和衣着,远远地看去,似乎是几个上了年纪却精神抖擞的老头老太太,因为吕聪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他们头上花白的头发。吕聪心想,等我到了他们那么大的年纪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呢?
班车到达最后一站——汽车站,也是它的归宿之地的时候,已经是一身轻了,完成了它承载着形形色色、来自各地的乘客到他们想去的地方的任务。
当然,大部分乘客都在之前在各自的目的地下了车,还有个别的例外。吕聪的家就位于汽车站附近,他们必须得在这里下车。他们算是最忠实的乘客吧,最起码亲眼目睹了汽车到达终点的时刻。
一切都按照吕聪妈妈原先计划好一步步去做。
他们又光顾那家一出车站门口左转就能看到的拉面馆。吕聪最爱吃这的拉面。
面馆老板是一个热情的中年男子,又高又壮,滚圆的大脑袋上没有多少头发。那在吕聪一家人听来十分陌生又奇怪的说话口音无疑地显示着他不是本地人。
他们一起跨进店门,小小的店面里挨着墙摆着两排供四人同桌用餐的桌子。其中已经有两个桌子满满地坐了人。只剩下一张最里边、挨着柜台桌子还没人坐。于是吕聪和爸爸妈妈顺理成章地走过去坐在了那。
他们虽然来过不止一次,但老板每天要面对的客人那么多,早就不记得他们谁是谁了。
吕聪却记得面馆老板的样子。他们要了三碗面,两大碗一小碗,老板站在他们桌前听完吩咐后便连忙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店门口,命令在那负责煮面的店员又要加三碗的量了,麻利地给我快点干活!
那个年轻店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长得瘦瘦高高的,头上戴着一顶和他身材十分相配的细高的厨师帽,更显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他低着头乖乖地听从老板的吩咐,手里边忙着抻面头边连连地点着。
老板吩咐完后悠闲地走开,也许是趁着中午日头足去哪儿散步晒太阳去了吧。
有几个在吕聪他们之前到的客人等得不耐烦,直着脖子嚷着催促那个店员。那个店员明显地加快了速度,匆忙把他们那桌的面都盛好,放在一个大托盘里端上桌去。
吕聪他们一家人耐心地等着,又过了几分钟,他们的也被端上桌了。
吕聪看着冒着热气和散发着香喷喷味道的三碗面端到自己面前,已经馋涎欲滴,简直没有什么能比这一刻感觉到的更让人幸福了。
那一根根筋道、滑溜又整齐的面条被一口口送进嘴里的时候,吕聪很自然地想起了"大饱口福〃这个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