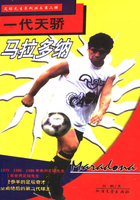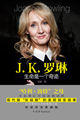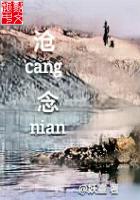邵总编过来告诉她,说她姐姐静宜来电话让她去一下。来到静宜的住所,陈香梅便兴冲冲地告诉姐姐说:“静宜,我今天见到他啦。”
“谁?”静宜睁着圆圆的大眼问。
“陈纳德将军。”
“啊!他人很好,是不是?”静宜漫不经心地答应着。这时,陈香梅察觉出气氛有点不对头。
静宜的宿舍似乎很乱。衣橱敞开着,地毯上放着两只皮箱,一只橄榄木做的褐色军用箱,像是在收拾行装。“告诉你吧,爹地来信也希望你到加州去,你考虑过这件事吗?”静宜右手举着一只浅蓝色的信封说。
陈香梅接过信,仔细读了起来。
父亲在信中几乎是在下“最后通牒”,如果她执意不去美国,父亲将会断绝对她的任何经济援助。
陈香梅果断地摇了摇头说;
“我想过去美国这件事,但是我现在不想去,我愿意留在这里,为战争稍作贡献。”
静宜没有开口。陈香梅接着说:
“再说,我到底学的是新闻,也被训练成一个女记者。同时很幸运获得一份很好的工作,并被派到一个很吸引人的部门——陈纳德将军和第14航空队。如果为了在美国那个不可预知的前途,而骤离此地,对我而言,乃是一桩愚蠢的事,因为在那儿的新闻界中,我需要与当地的美国人竞争。”静宜轻轻叹了一口气,说:
“我了解,我一点也不责备你。我也希望你不要怨我。人,常常要作出妥协和让步,我不想太伤爹地的心。唉,因为你一定不会走,所以我一定得走,懂吗?”姊妹俩说到离别伤心处,不禁潸然泪下。
“陈纳德的确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安娜。”
静宜试图改换话题。她接着说:
“因为有他,整个团体变得生气勃勃了。他的性格,他的精力和勇气,决定了一切。我非常钦慕第14航空队的每一个队员,而陈纳德却是一朵火花,一份感召。”
“正是如此,我也被他震住了,险些写不出一个字!”陈香梅抑制不住地插了一句。
“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爱上他了。”静宜狐疑地看着她说。
陈香梅两颊绯红,喃喃说道:
“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不知道……”
冬去春来。
陈香梅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出席社交活动。她在这些非正式的场合,同陈纳德将军有了更多的接触,彼此间有了更多的了解。
陈香梅在《一千个春天》里写道:
这些简短的谈话,在一种社交的气氛中,常使将军表现得更为轻松。为适应这种场合,我们并不局限于谈论本行,而是一般性的事物。他的学识、理解及智慧给予我深刻的印象,我一直珍惜我们的接触。但从1944年至1945年,我与陈纳德将军从无“约会”一类的事。
4月的一天。倾盆大雨。也许是天意,中午时分,陈纳德收到了陈应荣从美国寄给他的一封信。
原来,陈应荣在信中恳请陈纳德,说服他的女儿陈香梅去美国。
信的结尾写道:
“说来惭愧,对生性倔强的小女,为父的是一筹莫展了。我从静宜处得知,她崇敬您,而且一定会听您的。在此,让我先谢谢您。”
陈纳德看完最后一个字,他笑了。
难道陈香梅真的会听他的?
他有些冲动。
立即接通昆明分社的电话,邵总编告诉他,陈香梅外出采访了。
他忙问去哪采访了。
邵总编说,这时间大概采访完了,上老城墙根排档茶铺吃过桥米线呢,记者的中饭多是这样打发的。
他放下电话,连忙吩咐司机,开车去老城墙根寻找陈小姐。
雨不停地在下。此刻他的心却怦怦乱跳。他又燃着了一支“骆驼牌”香烟。
“将军,您找我?”陈香梅已冲进了办公室,不安地问。陈纳德怔了一下,指指桌上的信,说:
“喏,你父亲给我来了信,你先看看,坐呀!”陈香梅急忙抓起信就读。原来却是老调重弹!她凝视着窗外。
窗外是一片茫茫烟雨。
良久,她转过身来。
一只猎犬跟随陈纳德的身后,摇晃而行。
“乔,这是安娜。”陈纳德俯视着他的小猎犬。这只狡黠可爱的小动物,走到陈香梅的跟前,带有近似人的表情,抬头望着她,同时用一种试探性的友情,摆动着它的小尾巴。
“陈香梅小姐,你如果不想去美国,就不要去,”将军对她说。“你已不是小孩了,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啰,我的境况跟你一样,家里人都希望我回美国,可是,自己的事自己抉择,我不违心。我想,我懂得你。”将军继续说道。陈香梅突然扑簌簌落下两行眼泪。
她边啜泣边说:
“可是……父亲不懂得我……更不懂得母亲……母亲去世的情景……我永远无法忘记……”
将军微微弯下腰聆听着,时而点点头,说:
“我也一样。5岁时,我的生母吐血而殁,呵,我忘不了那悲惨而鲜明的一幕。15岁时,我的继母又弃我而去,她是那样地健康、开朗,可是疾病也夺走了她。安娜,我历经了两次丧母的苦痛,人生,有时是怨不得谁的……”“你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将军改换了话题,问陈香梅。“屈指算算,整整六年半呢,从1936年到香港,1942年逃离香港止。”她答道。
“我自从1937年来华后,曾多次到过香港,嗳,为什么我在香港总没遇到你?”他说。
“也许遇到过,可我们相见不相识。”她笑着答道。
窗外的雨还在下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