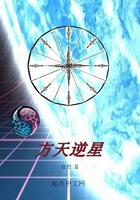梅娘是二〇一三年五月七日上午去世的,享年九十二岁。二〇一二年,我和妻子最后一次去她家拜访,和她及女儿柳青,一起切磋过自传怎么整理,当时她精神很好。直到去世前,她还能出国旅行。但到了春光明媚的季节,她却走了。听说她走得很安详。这是唯一让人宽慰的地方。她的一生实在太坎坷了!
梅娘本名孙嘉瑞,所以我称她孙老师。她一九二〇年生于海参崴。早年留学日本,四十年代初就登上文坛,成为知名的女作家。我认识她在九十年代中期,她已经七十五岁了。当时,我的妻子正在进行关于****的系列采访,鄢烈山建议采访梅娘。于是,我陪妻子一起去采访,妻子的文章不久在《书屋》发表,以后,我们和孙老师就成了忘年交。
采访中,我最突出的感受是那个时代对她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她的丈夫柳龙光本是共产党方面的人,牺牲于一九四九年初,但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农业电影制片厂当编辑,却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政治运动一来就是斗争对象:一九五二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被批判,一九五五年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一九五七年没有什么言论,被打成****,而且受到最严厉的“一类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出了劳教所,只好给人当保姆为生,其间三个孩子先后病死了两个。
就在这样艰难的处境里,她仍然保持着高贵的精神,和同为****的遇崇基、王秋林一家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他们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留学生,六十年代都住在东四北大街一带。同是****对象,就成了东四派出所政治学习班的“同学”。下课的时候,梅娘路过遇家,他们的儿子遇罗克总要想法弄一点熏干熬白菜之类的小吃请她品尝,和她讨论各种问题,还曾向她请教屈原楚辞。当时,遇崇基和梅娘两家生活都非常拮据。梅娘靠绣花维持生活,遇崇基得到陈毅批准,翻译了一本日本围棋著作,得了一点稿费,买了一点大米,就让遇罗克送一小包给梅娘分享。雪中送炭,梅娘十分感动。一九六五年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遇罗克写了一篇批驳******的长文,投寄《红旗》杂志、《北京日报》,都吃了闭门羹。于是找到梅娘,问她是否可以推荐给认识的《文汇报》编辑。他们并不知道******文章的背景,但直觉感到来头不小,于是梅娘说,推荐可以,但发表后很危险。遇罗克表示,最不好的后果都想到了。于是,梅娘把这篇题为《人民需要海瑞——与******同志商榷》的一万五千字长文介绍给《文汇报》,该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以《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为题,摘发了三千字。遇罗克当天很兴奋,说:“我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当然,梅娘的担心很快成为现实,这篇文章果然成了遇罗克更大噩运的开端。梅娘还是遇罗克《出身论》的早期读者。当时,梅娘被居委会指派写黑板报,粉笔就收在居委会门洞旁的牛奶箱里。遇崇基知道梅娘的信件都要被审查,于是通过奶箱,把儿子的一份《出身论》传递给梅娘。梅娘回忆当时“深夜,捧读《出身论》,读得热血沸腾,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赖以维生的绣花架子都碰翻了”。后来,我向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提议,写一本回忆录,二〇〇二年,遇罗文的《我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一次披露了两家人的友谊。在出版社举办的恳谈会上,梅娘到场祝贺。她看见已是中年的遇家的小儿子遇罗勉正在照相,激动地说,看见你,就想起老遇,你真像你的父亲。
得梅娘援手登上文坛的不止于此。一九七三年,史铁生刚刚瘫痪,在绝望中摸索文学创作之路,也得到过还在当保姆的她和女儿柳青的鼓励和帮助。
我认识孙老师的时候,虽然她的****问题已经改正十几年了,但后遗症还在影响着她的生活。当时,单位给她分配的住房很小,厕所只有一个平方米,人进去刚能转身,淋浴器下面就是蹲坑,她腿脚不灵,已不能站稳,但又装不成坐便器。农业电影制片厂盖了几栋新宿舍楼,她向厂里要求换房子。单位答复,不能调整,理由是进新楼必须有高级职称。她七十年代末改正后,没赶上评高级职称就退休了。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史里有论述她的章节,中国现代文学馆里有介绍她的栏目,把她当作研究课题的学者,可以评教授、副教授,但她在本单位就是不能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为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给农业部长写信,农业部长又和农影厂领导打招呼,中国作家协会又派一名书记处书记专门到厂里交涉,希望落实梅娘的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哪知就是办不成。厂里比她小二三十岁的人,或按领导职务,或按高级职称,都搬进了新楼。和她住在同一个旧楼里的是工龄不长的小青年,搞装修把暖气弄坏了,锁上门回了老家。就这样,老太太只好在冰冷的旧楼里,守着电暖气过春节。后来几经周折,单位才给她在旧楼里补了一个小单元,使住宿条件有所改善。
孙老师虽然遇到这么多不快,还是想热心帮助别人。当时,我的内弟在温哥华,工作不顺心,婚姻也解体了,孙老师听说后,就说女儿家也在温哥华,自己有时也去温哥华探亲,愿意和我的内弟相识。于是,她和我的内弟也成了朋友,在温哥华,又是帮他介绍工作,又是为他张罗对象,虽然没有成功,但那种古道热肠,十分感人。
孙老师的写作生涯,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记得常大林主编《博览群书》的时候,第一次收到孙老师的文章,大为惊叹:世上竟然有这样未经污染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