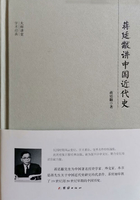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很爱看电影,可惜“文革”十年,根本没有什么电影可看。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母亲比较欣赏的片子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后来还有一部节奏比较欢快点的《摘苹果的时候》。在70年代中后期,北京开始有了黑白电视,那时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是家里最奢侈也是最昂贵的家用电器。我父母两个知识分子,手头并不宽裕,想买一台电视又觉太贵,那时一块钱能买很多东西,上百元的电视对普通家庭来说实在是个天文数字,于是,我母亲决定请朋友帮忙“攒”一台。
我母亲所在的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随便到街上去打瓶酱油,碰到的人你都可以同他谈“显像管”和“高频头”。有一段时间,我家充满了一股松香和电烙铁的味儿,墙上挂有一张绘制精美的电路图。我从小就懂得把那些二极管和三极管以及用铜丝绕成的大小线圈按照电路图焊在一起,显像管上就会跳出扭动的人影来。
那一年,我6岁,妹妹4岁,我和妹妹身上穿的新裙子是妈妈亲手缝制的。两个女孩从小到大,妈妈不知为我们缝了多少件衣服。
这是我18岁考上大学时,全家人的合影,弟弟那时只有8岁。
我父亲——一位内科医生,在组装电视的热潮中也被感染成了一位电子爱好者,到现在还喜欢在家中拉起蛛网一般的联线,给家中的众多的家用电器布置起一块布局合理、使用方便的综合电路板。我家当时那台“组装电视”是十二英寸的,居然比市面上出售的普通九英寸电视还要大好几英寸,这太让人兴奋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台电视是用三合板做的机壳,钉住三合板的钉子凸现在外面,显得有点难看,我父亲就到商店买来一罐油漆,用小刷子蘸着在电视机的木壳上精心涂抹,后来这台组装电视就不单单是电视了,还有了一点点艺术品的味道,那巧克力色的机壳和散发出来的淡淡油漆味儿,始终留在我记忆里,挥之不去。
组装出来的电视性能不稳定,经常发生“行扭”的毛病,有时一个笔直的人站在屏幕中央,在我家电视里却“滋扭滋扭”跳着摇摆舞。那时电视只有一个台,我们经常从“你好”看到“再见”,乐此不疲,觉得电视节目真是好看。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我家已有了三台不同时期的彩电,再加上原来那几台黑白的,真可以算得上是一座“电视博物馆”。三台大小不一尺寸不同的彩色电视机在客厅里一字排开,我母亲手拿遥控器噼里啪啦跳着调台,却似乎怎么也找不到可心的频道了。
第26节 书这种东西
我有个熟人买了整整一架子书,遮天蔽日,几乎占了大半个屋子,而且全都是精装书,平装的书他一律不要。我觉得很怪,就去问他:“平装的也有不少好书呢,你怎么——”
他回答我说:“你以为我真有工夫读这些书呢?这些书买来不过是些摆设,充充门面罢了,透着咱也有文化。”书就成了这样一种装腔作势的东西。后来我还听说有整柜子的书随书柜出售的,这样就省得房间的主人一本本上书店去挑了。我认为书像其他私人物品一样,不宜展览给别人看。图书的拥有量并不是学问的见证。好书都要藏起来看的,没谁敲锣打鼓招集起一帮人来,然后再开始读书。那是请客吃饭不是读书爱书。总喜欢热热闹闹的人是没心情一个人坐下来品一本书的。读书的心境与品茶颇为类似,是属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本好书从书店里买了来,放在擦得干干净净的案头上,总好像在勾人心头的痒痒肉。即使当时没有时间细读,也总想先忙中偷闲翻上两页,看他个只言片语。好小说断章取义从中间看两眼也能看得进去,这就是语言本身的魅力。而那些立意很好、语言却干巴巴的小说,冷不丁从哪儿一读感觉就很难受。有人写小说纯粹是在写“新闻报告”。这类书并不是因为多么深刻而使人看不进去,只是因为它太难看了。一个要演技没演技、要长相没长相的丑女在台上扭来扭去,观众当然有权唾弃她。读书也是这样,写得太差的书,干脆一眼也不要看,省得污染眼睛。
要找那些和自己精神上能够相通的书去读,读的时候才能体会精神上类似于飞翔的感觉。只有书才能带我们到达平常到不了的地方,平俗的书读来只是自添烦恼。我身边很有几本像伙伴那样关系亲密的书,每天一睁眼我要看到它们,这些书并不是装潢顶顶漂亮的书,也都不是精装版,我不看重那些,我喜欢一本书是爱屋及乌的。读书是在与人格上令你钦佩的人交谈,读书是最自由的一种会话,没谁能钻到你内心去,只有书籍能够做到。
那些买来书装饰墙壁的人家,是很难明白书的妙处的。书里的话印在纸上,并不像电脑里的信息那样过眼烟云。书是值得反复体味、细细追究、一句一句掰开了揉碎了看的。小说更是话里有话、音里有音的东西,并不是只看故事,单纯看故事的读者可以去看电视连续剧。
在我个人看来,一个人藏书不宜过多、过杂,这就好像交友,泛泛的皮毛之交,这种朋友不如不交。书太多、太杂、太新、太昂贵,反倒成了一个人精神上的负担而不是财富了。
第27节 流行带穗的东西
流行开来,一开始是袖口和下摆带穗的毛衣,随后又有了带穗的裙子和小包,什么东西一旦有了穗就变得特别时髦。我有一条下摆带有毛茸茸穗子的裙,颜色是稻草黄,穿上怎么看怎么像跳草裙舞的女人,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条裙子。
过年时,我穿的是一件非常独特的毛衣,他们告诉我,那叫“圣诞装”,因为领口和袖口都各有一圈雪绒绒的羽毛,穿上后整个就像一个雪人。
有时候,衣服就像会说话一样在表达心情。我从来不相信别人说的流行,什么春夏时装流行预测之类,似乎都是纸上谈兵。
有些东西永远穿行于流行之外,比如说,一条裤形适合自己的牛仔裤,一双黑色露小腿的长靴,一双红毛线手套。我永远记得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半生缘》,那里面就有一双红手套。
流行让人觉得永远有东西要去买,流行让人觉得不满足。我一生最大的两个嗜好就是买衣服和书,虽然我是一个职业小说家,但我买书却不是为了工作,纯属乐趣,买书时的心情和买喜欢的衣服一样。
这是我当兵时的“新兵照”,80年代的军校女学员都特别爱照相,照的大部分是黑白照片。
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她总是买不到合适的衣服,买回来的衣服总是后悔,穿一次就再也不穿了,或者干脆一次也没穿过就想送人。我想这是心情问题,当时买下这件衣服时的心情,度过那一个时间的点,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倒有些像写小说,那时的心情才能写下那样的文字。写小说就像开着一辆轰轰向前走的列车,沿路经过的风景,一边走一边把它们甩在后面。如果你要说把某处的风景重来一遍,那找起来可就难了。一朵花无法重复开放,艺术也是无法重复第二遍的。
流行就是对生活有兴趣的人不断花样翻新。流行就是女人和女人达成共识,在一段时间内,都想穿紧身的上衣和修长的裤子,或者,反过来,穿宽大的上衣和细腿裤。现在正流行前者,所以就觉得大衣小裤是很难看的,可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种打扮是很流行的,所谓“休闲装”,就是宽大衣服的代名词,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那么难看的打扮,居然能流行。
第28节 阅读之美
卧室里有一盏带着长长流苏灯罩的床头灯,即使在白天,如果我躺在床上看书,我会拉上窗帘,开这盏灯,细雨一样的流苏就像灯的睫毛一般,垂顺而又飘然。我喜欢开着灯的上午,寂静慵懒的时光,我靠在枕上阅读。
有很多书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读到的。那些诗歌刊物,大小不一的开本,或粗糙或精美的印刷,生动爽利的文字,很是吸引人。还有村上春树的小说,也很适合躺着阅读。
我很想与读者分享阅读之美,阅读是一种境界,是寻求自己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方法。清晨或者下午五点,迷乱的泡沫正在上升的时候,放一杯清水在床边,直口杯,没有一点装饰,灯光照在单纯的杯口,闪烁着迷人的光亮。
这时,你已站在一个通道的入口,忘掉那些烦心的电话,要发还没发的电子邮件,邮政信函,未过目的合同,大会发言,小会提纲,统统忘掉它们吧。翻动书页,会带来哗啦哗啦的响声,流苏灯罩,发出静谧的令人难以想像的光芒。阅读的快感在你翻开书页那一瞬间就开始启动了。
我是一个很怕换地方的人,因此每次旅行我都要带上同样一本书,这是一本法国人写的书,无论我走到哪儿,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椰子树》,看到它的第一行“在我们故乡每一棵树都像人一样直立,岸然不动……”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变得出奇的宁静。其实,旅行就是从一个酒店的标准间到另一个酒店的标准间,身体的移动会使人难以适应,陌生的气味,陌生的人和酒,陌生的人脸。
我不喜欢旅行主要是害怕夜晚睡在陌生的房间,有书为伴,陌生的房间就不再陌生,在不一样的灯光下阅读同样一本书,感觉并未走远。
我曾在旅行车上朗诵那本书的序,其中“今夜,直到清晨,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中国同眠的时刻了,在我们的身后,事物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离去而停止存在”是我喜欢的句子。车身晃动,抚摸这样的句子使我感到安心。
阅读可以随时随地进入,在候车室,在朋友的房间,在电视演播厅的一角,在酒吧的窗子旁边,在人多的地方,在人少的地方。吵闹与安静,慌乱与安闲,爱着与失恋,有朋友或者没朋友,有工作或者没工作,事情进展得顺利或者不顺利,心情好极了或者心情糟透了,种种状况下都可以开始阅读。
阅读有时就像飞一样,可以带你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我的长发常常被人称赞,他们说长发飘飘是一种美,其实,我一直梳长发的原因是没时间上理发店,我是一个写得很慢的作家,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写作上了。